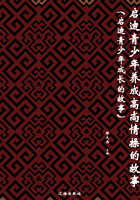多年前,我在一本诗集里看了这么一首诗《孤独》。
我本是不喜欢诗的,理由就是一个,看不懂,不知道作者在说啥。但看了这首诗我哭了,它打动了我。我哭后,还爱上了这写诗的人,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他,便开始追随,最终嫁了他。
诗是这样写的:
蹒跚去走
就一个人不要月不要星
不要萤虫似怜悯又似嘲讽的灯
不要光亮照出我的影
陌路上相逢一笑 足够了
别进屋
别摆下两只杯盏
别上床枕一个枕头
我与这首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我说这事,不是想公布我的恋爱史,虽然客观上起到了这作用,但它决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想证明,语言是有用的,有用到,它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
今天午休时,我翻看《老子快读》一书,台湾人写的,书写得不是怎么好,有些粗糙,但作者在这本书里讲了这样一件事让我有了兴趣,并有了今天的话题。
书中说,苏轼在《日喻》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天生的瞎子没有见过太阳,就问人家太阳是什么样子。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形状就跟铜盘一样。他敲敲铜盘而晓得了它的声音。后来有一天,他听到铜钟之声,就认为那是太阳的声音。又有人告诉他,太阳的光就跟蜡烛的光一样,他摸摸蜡烛了解了它的形状。后来,有一天,他摸到一根短笛,就认为那是太阳。”苏轼这个故事,说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太阳是圆形的,人人可以看得到,但经过用语言解说给没有见过的人听,结果却由铜盘错成钟,又由蜡烛错成笛子。可见,语言又是多么的无用,它竟把圆的说成是长的了。
昨天,我看罗西的博客,他写了一篇文章《久不见牡丹,于丹就成了牡丹》,用准确而生动的语言,对于丹倍加赞赏。我读后感觉很好,罗西的字里行间根本没有什么对于丹献媚、讨好的语言啊。但却有网友评论说,罗西在拍于丹的“屁屁”。
于丹出名后,对于丹的声音一直有两种:欣赏与指责!我也想写一篇小文,《于丹该死还是该活?》
这又是语言的用处。
还有一个小故事,说是一个丈夫与妻子不在一地工作,两人平时沟通就用短信,既省钱又有情趣,一次,丈夫睡着了,没有给妻子及时回信,妻子生气,短信怒斥。丈夫赶紧解释,让妻子消气,他回信道:“刚才睡了一小姐,没有听到短信声音,千万不要生气!”由于丈夫着急回信,竟把睡一小时的“时”字,错按成“姐”字,这可是捅了马蜂窝,妻子立即打过来电话咒骂,害得丈夫足足解释了两个多小时。
这又是语言的无奈之处。
语言,终究是有用还是无用?
我说语言是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