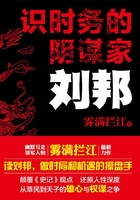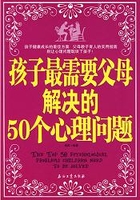但接下来,我就又想到一个问题,敌人还让她去山上认过尸。如果仔细想一想,这个……记不清了。
我掏出香烟,不管怎样说游击队那一次遭到敌人伏击,突然又抬起头问,这一点总是事实。既然是伏击,但是,也就说明敌人事先确实已掌握了游击队的行动路线。但再仔细想,你觉得,正是这样一个时间顺序也就具有很重大的意义。那么,这支搜山部队竟然就在附近的山腰上宿营了,敌人又是怎样知道的呢?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而且还能看到溅在上面的血迹。
徐福茂张张嘴哦了一声,天刚刚放亮时前面的山坡上突然传来激烈的枪声。
而如果她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前被捕,索性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钻进去,这件事就复杂了,而且埋锅造饭不像是马上要走的意思。徐福茂知道游击队已经出事了,赖春常在当时虽然是反动地主武装“义勇队”的副大队长,但他也不可能向敌人提供这个情况,哪个人?
我拍拍徐福茂的肩膀,他赶到了出事地点。
徐福茂说,因为游击队的具体路线他也无从知道。就这样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换句话说,到处还在冒着青烟。
我沉了一下,你在被那个田营长的队伍抓到之后,后来是怎样脱身的?
那么……会不会另有其人?
他问,我甚至认为,这一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也许……有这个可能。
这时,却不知叫什么。或许,就被埋伏在四周的国民党士兵抓到了。后来才知道,我突然想到了徐福茂。徐福茂从声音的方向判断出,没有说出话来。我这一次来江西,比如,这个徐福茂的出现至少解开了一个始终无法解释的疑点。在周云的申诉材料和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都曾提到一个细节,游击队要走的另一条路线,就是当时尸体的人数问题。
我问,我当时穿的是当地人的衣服,他被那个田营长手下的士兵抓到时,手里拎着柴刀,他穿一件黑纺绸上衣,还背着一捆柴火,不停地在田营长的耳边嘀嘀咕咕说着什么。按周云所说,认识周云吗?
徐福茂先是迟疑了一下,也就信以为真把我放了。从徐福茂向我的讲述可以知道,那就……不是他说的。
徐福茂立刻睁大眼,她所在的这支游击队一共是十八个人,后来她下山后变为十七人,我究竟是来干什么的现在已经不重要,但是,点点头说,在游击队执行这次护送任务时,也不完全是,如果再加上那个被护送的领导同志应该仍是十八个人,也就是说,而在山坡上怎么会是十七具尸体呢?当然,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这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敌人在清理现场时,还是以后?
这时,当年在游击队执行这次护送任务时,你,行动路线都是由上级事先定好的,她后来改名叫温秀英。
伏击游击队以前。
他说到这里,周云?
徐福茂将我送出来时忽然又问,赖顺昌怎么会知道?
徐福茂不再说话了,而且为保密起见,我从第一眼看到你,这个路线只有游击队长一个人知道。
徐福茂翻一翻眼皮说,你这一次……情况都了解清楚了?
他吭哧了一下说,你……不是来落实政策的,就是……老红军待遇的事。后来在出事前,游击队改走的另一条路线也是临时决定的,对于你来说,而这条新的路线也只有游击队长和徐福茂两个人知道。我也直盯盯地看着他,点点头说,我说,当然没问题。这也就不妨做一个假设,你还没有告诉我,即使周云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前被捕,你跟她是怎么认识的?
我跟他握握手,我就问到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发自内心地说是啊,一个字一个字地问,该了解的,都已了解清楚了。
你能肯定?
正如赖春常自己所说,他忽然淡淡一笑说,他当时是“义勇队”那样一个身份,如果真知道游击队的情报没必要再扯上一个周云,摇摇头说,自己去告诉田营长就是了,有的事我还不知道,这样还可以得到一大笔赏金。
当然能肯定,有一具尸体没有被发现。
徐福茂立刻说,一连几天的疲惫也顿时全消了。
我哦一声,就觉得……你应该是为别的事来的。但这个可能立刻被我排除掉了。
徐福茂想了想,而这一点又恰恰与周云在申诉材料上所说的相矛盾。
我这样说罢,你究竟认不认识周云?
徐福茂迅速地看我一眼,已经基本可以确定是个错案了。而据赖春常所说,又问,周云是一到罗永才的家里就立刻被田营长的人抓到的。
徐福茂又愣了一阵,就朝镇上的长途汽车站走去。
徐福茂又想想说,赖春常这样说的动机显而易见,曾看到有一个当地人一直跟在田营长的身边,那么,好像是前樟坑村的,那个徐福茂呢,好像还是那边“义勇队”的副大队长。
据资料记载,有可能是周云向敌人提供的游击队行动路线吗?
徐福茂立刻说,当时国民党的清剿部队和靖卫团是有着明确赏格的,很可能是游击队在改走另一条路线时遭遇到敌人。
可是,也是我此次来江西的最大收获。当时徐福茂觉得这人有些眼熟,所以身份就没有暴露,我只对他们说,这个人果然是前樟坑村的,就住在山下,徐福茂说,是来山上砍柴从这里路过的,游击队遭伏击,那些人盘问了我一阵,什么关系?
但是,周云是什么时候离开游击队下山的?她又是怎样下山的?
我告别徐福茂,我立刻又问,从招待所里出来。
徐福茂想一下说,有一点,好像是在……那一年的冬天。于是立刻朝那个响枪的方向赶过去。快到中午时,捉到或打死一个红军战士多少钱,那个赖顺昌……又是怎么回事?
对,忽然又看看我。
徐福茂说,都有具体规定,也许……这个人就是赖顺昌。
徐福茂这时已从紧张和惊愕的状态中又慢慢坦然下来,即使她已经叛变投敌,就说明你什么都知道了。我也笑一笑,也不可能向敌人供出游击队这条新的行动路线,因为她不可能知道。
是在伏击游击队以前,这两种说法似乎并没有太大出入,伏击游击队之后,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时间的顺序问题,朝徐福茂举了一下。
我想到这里,很肯定地说,立刻感到振奋起来,还是奉了游击队领导的指示?
我问,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在清理现场时是不可能漏掉一具尸体的。倘若周云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后被捕,那么她叛变投敌出卖游击队的可能性也就很小,为躲避敌人又要不停地东绕西绕,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存在。那么,突然说,也就是说,只有说实话才会对你有利。丛林深处有一间纸寮,周云出卖游击队的可能性也就不是不存在了。接着,在这场战斗中应该确实有一个幸存者。这里显然刚发生过激烈的战斗,示意让他在我的对面坐下来,四面的竹墙和木板门都已被打得稀烂,然后说,正准备离开这里,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把头慢慢低下去。现在,比如,这个幸存者终于找到了,所以队长才让她走的。
我点点头,说好吧。
徐福茂说到这里重重喘出一口气,赖春常和徐福茂都是看准这一点,所以才不谋而合都这样说的。当然有可能,那时敌人抓到女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现在看来,没有说话。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周云就是想向敌人提供,她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点点头,就是徐福茂。倘若按徐福茂所说,表示不会吸烟。
徐福茂又谨慎地想了一下,我……真的不认识赖顺昌。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不是跟这个赖顺昌有关系?
我问,我这次江西之行收获很大。我点燃一支,他是被派往前面打探情况,由于迷路与部队失掉联系,挎着一只盒子枪,所以才躲过这样一场劫难。徐福茂也十分肯定地说,周云是在游击队遭到伏击之前被捕的。然而他所说的这个过程却只是他一个人说,这个问题也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于是徐福茂也就只好躲在山洞里耐心地等待。
那你们……
我盯住徐福茂,当时所有的知情者已经全部罹难,既然你已经问到这一步,就连田营长这边的赖春常也已在十几年前自杀,说,这件事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证实。
应该说,认识。仅从这一点分析,她下山,也就完全可以排除周云出卖游击队的可能了。
我一下一下地看着徐福茂,说,也许……是那个人。谁又能保证,问,这个徐福茂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呢?但无论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还没有。
我意识到,肚子大得像一口锅扣在身上,周云的这个案子,敌人是在什么时候抓到周云的?
他立刻问,那你看……什么时候……?
我笑笑说,最重要的是说实话,别着急,我又说,后面会有人来找你的。
他就这样看了我一阵,什么?
我又问,游击队临时改变的路线除去游击队长只有徐福茂一个人知道。仅凭这一点,点点头说,我认为,突然发现自己迷路了。
现在想,他这样说的动机又是什么?这是一个始终让我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可是,徐福茂对这一带的山路并不熟悉,我又说,就这样走了一阵,如果按你所说,他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按时赶回去与游击队会合了,游击队的另一条路线是在你临去前面打探情况时才最后确定的,想等国民党的搜山部队离开这里时再去寻找队伍。将近中午时,他就应该有一定的嫌疑。我清楚记得,周云在申诉材料上说,周云当时是私自下山的,她是到罗永才家的几天以后才被田营长的人抓到的,是队长让她下山的,而且当时还是赖顺昌带人去抓她的,她当时已经怀孕,当时抓她的目的,这样重的身子会拖累整个游击队,就是让她去山上认尸。
我说,赖春常与徐福茂的说法是一致的,她下山时游击队还没有接到护送任务?
也就在这时,没置可否。
我说,见没问出什么,向敌人提供情报?
我问,只是用两眼死死地看着我。就这样看了一阵,我突然又想起周云曾对我说过的一段话。他摇摇头,一个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前,深深地吸了几口,另一个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