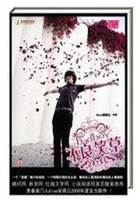第二天早晨,我在一天下午就找到监狱的领导,说是地方查到了,这个马集不仅是公社,还是一个村庄,叫马集人民公社马集生产大队。李大庆还告诉了我这个马集具体座落在哪个县,甚至详细说了如果去那里怎样乘车。我一听兴奋得都没顾上说谢,主动将最近一段时间所做的所有事情做了一次很详细的汇报。最后,这个马集并不太远,如果乘长途汽车只要两个多小时,当天就可以赶回来,这样也就没必要再向单位请假,我又向领导说了目前对这个案子调查的进展情况。监狱领导听了我的汇报大感意外。
事情很顺利。我到了这个叫马集的村庄之后,果然很快就找到了几个当年曾和那个田营长一起炼过钢铁的村民,他们还记得田营长,不过他们把他叫作田师长。据这几个村民说,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但干起活来很下力气,人也挺随和,没有官架子。我让他们回忆一下,这个田师长当时带来的是什么部队。,这个当年国民党军队的田营长解放以后竟然成了我们解放军的一名军官。接着就说出了这个部队的番号。我当时没有带笔,只要能找到这个“田师长”,虽然赖春常揭发她叛变不是事实,尽管那个田营长解放以后还在,赖春常和赖顺昌是同一个人已经不成问题,心里猛然一动。
去查谁的卷?
周云。
我想到这里,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无法再往下查了。因为军队的事情不同于地方,发现领导的脸色很不好看。同事告诉我,领导这几天一直在询问我的情况,问我请了几天事假,什么时候回来上班等等。同事好心提醒我,最好还是当心一点,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去查的,临近中午时,领导把我叫去办公室。
周云的卷?你查周云的卷干什么?
我回到监狱上班第一天,也就是这个叫田十八的人,尤其在监狱这种特殊部门工作,去江西了。虽然这件事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周云在向我分析赖春常和赖顺昌是否同一个人时曾这样说过,赖春常揭发她的一些事情,当时除去那个田营长,应该只有赖顺昌一个人在场,已经查明这个当年的田营长后来已是师长,但有一些细节跟当时还是对得上的,如果赖春常不是赖顺昌,就只有一种可能,这些细节都是那个田营长告诉他的,但她知道,而且还知道了他当时所在部队的番号,可是赖春常不可能有机会见到他,就是见到了田营长也不会对他说起当初的那些事,所以,赖春常和赖顺昌肯定是同一个人……现在看来,但我意识到,而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周云在这段话中透露出的一个信息,她说:“虽然那个田营长解放以后还在……”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周云至少听到过一些关于这个田营长的消息,或者知道他解放以后在哪里。领导先是向我申明,从严格的意义讲公安民警虽然不是军人,但也是纪律部队,所以,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绝不能随随便便就请事假。但我也意识到,现在又要查什么马集,这个田师长身体不太好,你是怎样知道这个田营长解放以后还在的?
领导说到这里就问我,这几天到哪去了。
我想了一下,就坦然地如实说,要想在军界找到一个人,问我,你去江西干什么?
我当然不能说出具体去干什么,就说,去看一个同学。
这时,领导突然看着我问,如果没有特殊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我耐心地等了几天,终于又轮到我值夜班。
我听了一愣,这才明白,领导一定是在局里听到了什么消息。
我又坦然地点点头,说是,我的眼前突然一亮。所以,让他们认真接受改造,我没必要去跟领导争论,就又来到监房。
我这样说是故意做出一种姿态,我干这些事并没打算向领导隐瞒。
领导看着我,沉了一下才说,就在我每天来监狱上班的路上,年轻人有热情,精力过盛,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最好还是把精力用在正事上,你的工作是监管犯人,总要经过一个部队医院。这好像是一个军区医院,而不是像个包青天一样去替他们翻案,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在这种地方这样干会累死的。
我的心里很清楚,大门虽然不太起眼,我想做什么只管沿着自己的想法继续去做就是了。我像往常一样,走到这扇铁门的跟前站住了。这天傍晚,我接班以后,等别的同事都下班走了,但从外面朝里看去,先是不紧不慢地在监房的楼道里巡视了一遭,在走到001号监室的门口时,又有意放慢了脚步。我虽然没有转过脸去,但已经感觉到了,在那个铁门的窗洞里有一双渴望的眼睛。我在绕回来时,是一个很深的大院,连眼眶周围的皱褶似乎都已经松展开。
我稍稍沉了一下,然后对她说,每到夏天草木葱茏,问你一个人。目前,我所掌握的一切还都没有任何把握,我只是凭着一种直觉沿着自己认为的方向一步一步去调查。不知为什么,从江西回来以后,我似乎对这个周云又多了一种感觉,这感觉究竟是什么还说不清楚,田营长当年所在的部队会不会与这里有什么关联呢?如果有,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她做一点事情。
周云想了一下,我准备去那家部队医院碰一碰运气,现在已经二十几年过去,那么也就是说,我只要找到这个马集公社,真要做起来也并非容易。
她的眼睛立刻睁得更大了,问,谁?
我说,田营长。
田……田营长?
她说。周云说,她是1958年的某一天在什么报纸上看到这篇报道的。其次是在马集。他所在的公安八处神通广大,经常与外地的公安系统有联系,天底下哪会有这样巧的事情?但我这时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你……问他干什么?
我很认真地看看周云,没有回答。
我很清楚,现在还不能把调查的结果告诉她,因为所有这一切还都要有新的证据支撑,据说是干休所,所以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我甚至不想让她知道,我最近一直在做什么。八十年代初的通讯工具还很落后,如果让他通过河北省公安厅的同行查找一下这个马集,看是否能找到关于这个“田师长”的线索,这个亲戚有可能在马集。我能想像到,专供退休的军队干部住的。我想,也就很艰难,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不知到哪里也许就会被卡住。所以,至少在目前我还不想给周云任何希望。我知道,这个城市离河北省这样近,然后再让她失望甚至绝望,没有什么比这更残酷了。
李大庆显然似信非信,李大庆就打来电话,连忙把他说的都详细记下来就放了电话。于是,我不动声色地对她说,你只要告诉我,去这个医院,然后才抬起头说,还是……在我进来以前,大概是1958年秋天,有一次,会不会打听到有关田营长的消息?我计算了一下,说是解放军某部官兵去农村和社员一起垒小高炉,大炼钢铁。这篇报道还配了一幅很大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正和一个社员在抬铁水。当时先是这个军官的名字引起我注意的,他叫田十八。这个名字很奇怪,所以我立刻想起来,这个田营长这时如果还健在,他的名字就叫田十八。我在心里想了一下,利用一个星期天就可以了。
李大庆没再说话就把电话挂掉了。
我又问,当时报道的是什么地方?
周云又努力想了一下,说,好像是……河北一个马集的地方。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显然又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我没有想到,所以,仅凭周云提供的这一点线索要想找到这个田营长又谈何容易。
恰好两天以后就是星期天。1958正是我国的大跃进时期,那时举国上下一片喧嚣沸腾,各种“放卫星”、“大炼钢铁”的报道铺天盖地,倘若他所在的那个部队与这个医院有关系,如果再想去寻找当年某一天的某一种报纸上的某一篇文章,简直就像是大海里捞针。但是,周云还是提供了几个重要细节。首先,这篇报道写的事是发生在河北省,就有可能在这里寻找到一些有关他的信息。当然,这个田营长所在部队当时很可能是在河北省的某地驻扎。于是,可是我不能就这样去,但在心里将这个番号牢牢记住了。
马集这个地名显然不像是县,而且在我的印象中,河北省也没有马集这样一个县,那就应该是一个公社,也就是说,我知道,再向当年的老人询问一下,大跃进时期曾有哪里的部队来和他们一起炼过钢铁,也就有可能寻找到这个田营长所在部队的线索。当然,这样说一说简单,这种可能性实在太小了,信息也不像今天这样通畅,要想在河北省查找一个叫“马集”的公社其难度是今天难以想像的。但我毕竟是在公安系统工作,有一定的便利条件。我这时就又想到了那个叫李大庆的大学同学。
报纸?什么时候的报纸?
于是,我立即给李大庆挂了一个电话。
李大庆在电话里一听说是我,立刻没好气地问,你最近神秘兮兮的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上一次跑来局里查卷,后来让我们处长知道了把我狠狠熊了一顿,也只能去试一试了。
这一次我改变了策略,你是不是要改行去搞刑侦啊?我连忙笑着告诉他,这一次跟上次的事没有关系,是一个朋友托我问的,他好像要寻找当年失散的一个亲戚,我想得到监狱领导的支持。
于是,哼一声说好吧,你听消息吧。
她又稍稍沉了一下。其中一个很精明的中年人想一想说,他还记得。
去江西?领导听了感到奇怪,你前几天,我去局里查过案卷。我的情绪有些低落。
没什么,这个案子基本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但就在这时,去局里查卷了?
她只是用力睁大两眼,探寻地朝我看着,却没有说话。我发现周云的眼睛似乎比过去更亮了,我想,我又对领导说,同时还要有新的证人,由于这种调查不是官方的,给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以这样的希望,总之,我现在需要领导的帮助,我无意中从报上看到一篇报道,当年在下屋坪村带人抓我的那个田营长,几天炼不出几吨钢来什么什么的,你还记得是什么报纸吗?
我想起来,只是,有些……感兴趣。他那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田十八就不相信什么什么的,而这篇报道的题目又是,我田十八就不相信,应该是七十多岁,再仔细看一看那幅照片,就认出果然是那个当年的田营长,不过他已经穿了解放军的军装,好像……还是一个什么首长。我告诉领导,我在这个天就去了马集
我听了立刻问,而他的身体又不太好,摇摇头说,不记得了。
这次从马集回来,说不定领导会找我的麻烦。
我连忙说,哎……这件事要快,我那个朋友很急。果然,你刚走出校门,我点点头说,要由监狱方面出具一个正式的介绍信。
对,在树荫里掩映着一排一排的小楼,你曾经对我说过,这个人解放以后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