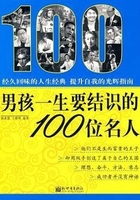皇太后那双眼睛可是深沉清亮得紧,她知道对付自己的儿子,要用什么方法!
郎东昱在悄悄的磨牙,萧少岸,槿草书,你们俩等着瞧!
“母后,你与易初莲花有什么关系?”
郎东昱目光炯炯,有如烈日。
转移话题成功,母后的脸起了一层惊疑的褶皱。
不过只是转瞬即逝。
“易初莲花?真是个好名字啊!”
皇太后为阮宁波掖了掖被角,捶了锤刚才因用力而有些发酸的肩膀,道:“有一种干净的意境,如雾气升腾,若云雾缭绕,不过不是楚国最大的商行吗?据说掌柜的叫张易初,因楚国的国花是莲花,所以取了这个名字,商行什么都卖,娘早年游历江湖时曾于此商行偶得一本秘笈,怎么,皇儿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
郎东昱深沉狡黠的眸子转了几转,母后的说辞几乎让他找不出任何破绽,也罢,这不是目前他要关注的问题。
“只是今日皇儿偶遇一个叫初醒的女子,她问起儿臣如何知道玉骨冰肌?”郎东昱貌似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立即又道:“母后,当年送去吴国的质子七年前就离开吴国了!”
“母后?”郎东昱再叫了一声失神的皇太后。
“啊?”皇太后李姝仪从沉思中转醒,“皇儿,准备迎战楚国了?”
“母后怎知?”
太后舒缓的轻笑一下,“皇儿既然提到送去吴国的质子,那必然是想借用吴国的力量来牵制楚国。不过只怕没那么容易啊!金楚之战,注定是你死我亡的血肉之搏!母后随先皇征战多年,才有了今日这番景象,母后绝对容忍不了有谁来破坏!有谁叫板,本宫必定让他血债血偿!”
皇太后李姝仪苍老的手指握成拳,怒砸在跪坐的褥被之上。
“槿草书虽狂傲不羁,但骁勇善战;萧少岸老谋深算,但过于谨慎。皇上对二人当是知人善任,至于吴国方面,派使者求援,牵制楚国兵力。”
得了皇太后的准战,又于朝堂之上紧急商议了对楚作战事宜,于是……
于金樽皇朝通元二年,金楚之战正式拉开序幕。
而此时,楚国已经大举进犯金樽皇朝边境,庐州失陷,定远相继失陷,楚军驻扎在梁园,作势一举南下!
使者出使吴国,虽然吴国答应派兵援助,却只是在边境线上按兵不动。
“报……”
“报……”
一声接一声的边关急报,一个接一个或骑或奔的身影,甩在身后的马匹嘶叫着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而人继续急速奔向皇宫的深处,御书房。
“报,边关急报!边关急报!”士兵上气不接下气的奔进御书房,扑身下跪。
“讲!”郎东昱脸色阴沉的坐在一摞的奏折中间,隐于一片阴影之中。
“回禀皇上,边关急报,楚国大军已经到达金水江,不出几日,便将过岸,直捣罗州城,逼近京城!”
士兵说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知道了,下去吧!高得全,赏!”
郎东昱说完,便又窝进蜡烛的阴影里,从小酒坛子以手指捏出几片牛肉,嚼了几嚼,却没有往日的神采,酒浸牛肉也失了韧而辣的味道,形同嚼蜡,今天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了!
萧少岸的担心成真了,郎东昱思付感叹,难道金樽皇朝注定是要消陨在他的手里?
有些苍白的指节抚上额,慢慢穿进发,的深处,揪紧,握拳。
“萧大人,你以为如何啊?”抬起头,郎东昱瞥了一眼萧少岸。尽管灰暗低迷,但是郎东昱说出的话仍然满是气势。
“这是臣最怕的结果,还是来了!”萧少岸有些暗哑低沉的开口。
“但……”萧少岸登时一个转折,“不过也并不是没有活路,酒妃阮宁波给为臣提了个醒,为今之计,是以险,以智,为皇朝争取时间!”
“哦……萧爱卿何时又见得了阮妃娘娘,这句话又是何解?”郎东昱稍微坐起身子,萧少岸是金点子,每每绝处总能逢生,不知这次又是何种计谋!只是这是阮宁波说给萧少岸的,一时之间,他很是气闷。
阮宁波已经在床榻上躺了三天了,他没顾上看她,只是让大树和小草(那高个子宫女和小个子宫女)悉心照料着,母后说了一个月不配解药,还当真是这样,可他哪有心情去临幸那些嫔妃,国都快破了,弄出个皇子来祭别人的军旗啊!
“回皇上,见阮妃是皇太后娘娘的意思,臣不敢有违,其实也不算是计谋,只是阮妃所说,兵不厌诈,我们可以假装投诚,议和,哪怕只能争取一点点时间,也是对皇朝有力的!金水河,是决计不能让楚国军队渡过的!”
萧少岸一身黑衣,浑身散发出一种地狱般的气息,但只是片刻,便隐退在每个毛孔之中。
“议和?拿什么议?即使你想议和,楚国会答应吗?”郎东昱烦躁的将桌子上的一堆奏折推到地上!纷乱的散了一地!
“楚国未战前,曾经口出妄言,说势必要掠尽金朝的土地,享尽金朝的美女,喝尽金朝的美酒,踏破金朝的酒坛……”
“好了,够了,不要说了!楚国当真是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哪!”郎东昱的拳头挥砸在檀木红桌之上,细碎的木屑刺的手上一片鲜红。“萧少岸,你去,去跟槿草书说,朕拨了京城禁卫军过去,尽数让他指挥,此战只许胜,不许败,死拼着,也得把楚国大军给我拦到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