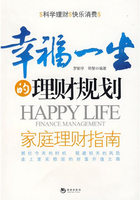小柔看看柳小姐身上的衣服,脸上臭臭的神情,又看看远去的少爷,一撇嘴,这莲子羹,她喝了,不热了!
湖边,望心亭,约在这里喝酒还真可笑!望心,心在哪?阮宁波兀自倒了一杯,浅尝一口,眼中是幽幽的笑,放下杯子,左手支头,垂首,右手端起不满盏的酒,移到摇曳的蜡烛旁边,绕着灯芯,倒下,晶莹顺着蜡烛流下,急速,却也慢慢凝固,那是酒,是烛油,还是泪?
笑,幽幽的笑,眼神穿越头顶的黑暗望着天空的几颗繁星,突然觉得,很冷……“你来了!”阮宁波没有回头,对着身后的脚步说!
宋工柳本想伸出的手,压抑下,在对面落坐,灼灼的望着阮宁波的眼睛!
阮宁波不看他,纤指摸向酒壶,欲斟。
宋工柳的手覆上她的手,“我来!”声音是霸道的毋庸置疑。说着从怀里掏出两个杯子,一模一样,只是上面一只是枯枝繁花,一支是一地落花。
那只枯枝繁花的杯子,白瓷杯被放置在阮宁波面前,白壁上那花,红得耀眼。
阮宁波拿起把玩,“荷花玉兰吗?似乎送错了人啊?”她问的幽然,眼神却调笑凌厉。
宋工柳沉默,看了她一眼,斟满一杯,“不是荷花玉兰,这是木棉,与你神似的木棉!”
这就是木棉?阮宁波心中暗付,只读过舒婷的《致橡树》,对那木棉的认知只限于……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而如今,一身红衣的她,隐没在这样的黑暗里,有这么一个曾经给予她温暖的人,对她说,你是木棉一样的女子!
她的反应,是一杯一杯的喝酒,一仰而尽,那凉意顺滑而下,冷了脖颈,又灼了肌肤!
而宋工柳也是一杯一杯的喝,那杯子,不小,他们,是豪饮。
不知道喝了多久,宋工柳舔舔唇,目光如血,这酒似乎比酒窖那次更烈!他感觉到浑身发热。
猛的按下宁波举杯的手,“不要喝了!”却一把被使劲甩开。
“我是无量酒后,我是千杯不醉的彼岸!让我喝!让我喝!”
抢夺着,宋工柳忽的站起,横过石圆桌的一侧把阮宁波抱过来,放置在腿上!
而宁波的手伸向了桌上的另一坛未启封的酒,宋工柳一把拉过,窝在胸前,声音满是哀痛:“求求你,不要再喝了,你气我什么,可以打我骂我,不要伤害自己!”
“我为什么要留着那坛酒,我要喝了,喝了,没有什么好留恋的,温暖哪里没有,阮宁波真是个懦夫!”她剧烈挣扎着,显然已经醉掉了,脸色晶莹的红,鼻息间是醉酒的香,高声的嚷叫慢慢变成低语:“最后再抱一抱我吧,我、好、冷!”
原来她要走!宋工柳摇摇脑袋,竭力控制自己的毛手,一下子清醒了不少,却登时更加郁闷起来。
看着怀中的人,他眼中闪着从未有的决绝,狠厉,单手掂起桌上的酒,猛灌,接下来他要做的事,需要胆量!
因为是她,所以他需要足够的力量来模糊自己的意志,那就是酒。
酒在坛子里撞击,流入他的喉咙,或喷溅在自己的下巴,胡茬上一片晶莹。
虽然他的意识渐渐的恍惚,但是那酒的滋味,却是从来没有体味过的,那是一种很悲哀的心情,却又很酸涩,任那酒在喉里流淌,他仿佛看见了一种割舍,一种决绝,和一丝叹息!
怦的一声,宋工柳一拳砸在那坛子上,朱红色的坛身应声而裂,然后,他胳膊一抡,碎片纷落入湖中!
阮宁波的酒从来没有名字,只是,这一个,有名字,两个字,却沉入了水中!
看着怀中的女子,头上惯绑的墨黑色丝带早已磨蹭的不知踪影,一头黑发披散在他的膝上!萤萤烛光下瓷白细嫩的脸庞,默默垂着的睫毛,因为酒的点燃而艳若樱桃的唇,象是口渴似的在微微张合,他的心中翻江倒海的,是欲念!
酒,有时不是好东西!
他的手伸过,抚上那樱唇,辗转,然后俯身,以自己的温热贴上那温热,有种感觉就象是儿时拿舌舔的那豆腐脑,那样的滑嫩,似乎比那更滑嫩,他上了瘾。
然后,忘记了场合,忘记了力道,只觉得,心中一把燃烧的火,他要找个出口!
“喔……什么东西?干什么?”阮宁波猛然惊醒。
衣袍被扯开,身子靠上冰凉的石板,衣衫尽去的凉意使得阮宁波忽的睁开眼,清冷但妖娆的望着,眼前近乎疯狂的男人。
“你—想干什么?”她的语气不稳,不是怕,是醉!
宋工柳已经昏了神志,只挤出一句话:“我要留下你,不管你醒来会怎么看待我,我要留下你,一定要留下你!留下你,留下你,有你在的日子我体会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我不想放弃,不想……你知道吗?”
有些狂乱的重复着,最后几个字几乎是吼出来的,然后在阮宁波的呆愣中,宋工柳俯身。
阮宁波无力的一闭眼,醉掉的意识里是她的冷嘲,真可笑,他们竟然是两个互相取暖的人……任双手伸开搭在石桌的两旁,她清冷的眼看一眼这个男人,他以为要了身体,他就能留下她吗?
那皇帝怎么可能想不到这层,所以她在等,等着有人喊停,可是没有!那就给他吧,原来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欢愉,她是飘在云端,却不欣喜,因为她知道了,他们只是雪地的两个人,贪恋彼此的温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