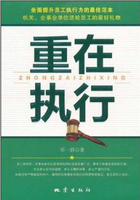娘说:“你们马家这弟兄俩——没一个好东西!”
“老五叔牵着牛往地里走,文盛蹲在厢房屋檐下啃包谷棒子,我把包单扎在腰里,打算下地去摘棉花。一转身,看见大门外走进来两个穿军装的人。我盯着他们看了一阵,他嘴角咧了一下,我认出了他,我举起手把额上的头发撩了撩,张着嘴半天没说话。他往前走了一步说,兰姐,我复员了。
“我对着他打量了一番,看清了他胸前没戴徽章,腰里没扎皮带。站在他身边的女兵和他一样没戴徽章,怀里抱着孩子。这浑货,他结婚了。瞧这副德行,不光把我忘了,把春如姑娘也给忘了!
“我鼻子里哼了一下,不冷不热地说,几时回来的呀?
“前天回到县城。有半个月假,回来看看你们。他伸手把女人往前拉了一下,这是刘英。——这是兰姐。
“我转过身说,文盛,你哥、你嫂子回来了。
“文盛站起来,张着嘴瞪着眼看他们。昌把提包放下,招着手说,盛,过来,过来。
“盛走过来,昌弯腰去拉提包拉链。女人在背后说,进屋再说呗。
“我挥了一下手,盛,让你哥嫂进屋去。
“盛住在西屋,一间房单独开门。一张床,一把破椅子,地上扔着他的臭鞋。他们进屋后扭头四下看,找不到坐的地方。我从院里拉了两把椅子给他,站在门口没进去。女人抱着孩子发愣,这个浑货脸上有点不自在。我说,要不,到我屋里坐吧。他赶忙点头说,行,刘英,咱们到兰姐屋里去。
“我伸出手,想把女人怀里的孩子接过来,孩子认生,瞪眼看着我,哇一声哭了。女人拍着她说,妞妞不哭,妞妞不哭。
“不管大人怎样,这女孩儿挺招人爱的,眼泪豆儿挂在脸蛋上,水汪汪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看我,看一阵又哭起来。我说,好了好了,大姨不看你了,大姨这张脸不好看。起名字了没有?
“她叫卓娅。
“这名字挺洋气的,不知道有什么讲究没有?
“这是一个前苏联女英雄的名字。
“咦,那好,长大了也当英雄。
“我把他们让进堂屋,堂屋的摆设还是爷爷在世时的样子,只是把后墙上的天爷换成了毛主席像,板壁上的四季屏改成了年画。这个浑货一进屋就走到神案边,伸长脖子看毛主席像旁边贴的喜报。仔细看了一阵,转过身对女人说,瞧,这儿贴着我的立功喜报呢。
“这是县里送来的,文盛屋里没地方贴,就拿来贴这儿了。
“他脸上有了笑容,比在文盛屋里开心多了。他把提包打开,拉出一条围巾。女人把它拿到我面前,指着上面的花格子说,这是文昌到前苏联去参加十月革命观礼,在莫斯科给你买的。
“围巾方方正正,展开像个大包单。中间印一座带尖塔的洋楼,楼顶上亮着一颗红星。四边缀穗子,质料挺厚实。
“他从提包里翻出两件衣服,文盛,过来,看这件褂子合不合身?然后扭头四处寻看,长安呢?咋没见长安呢?
“长安上学去了。
“长安都上学了?
“你六岁就上学了,长安八岁了,还不该上学?
“他愣了一下,长安都八岁了?在哪儿上学?兴隆铺初小?
“咱们兴隆铺学校现在是完小,能从一年级一直读到六年级小学毕业。
“没等我把茶烧开,他就急着想到学校去看孩子。
“刘英说,过会儿就放学了,有那么着急?”
兴隆铺小学在镇东头,从我家到学校要穿过整个镇子。这儿从前是祖师庙,兴隆铺每年立春都在这儿搞春祭。一个大院子,一座大殿,我们的教室在大殿旁边的草房里,坐在教室里能看见学生在操场上下操。
父亲到学校来看我,我正在上唱游课。女生们在丢手绢,我和二毛他们玩编箩头。“编,编,编箩头,箩头盛土不会漏。”正玩得起劲,老师叫我说,马长安,你娘来了。我转过身看见娘站在操场边,她身边站着一个穿军装的人。
父亲给我的第一印象鲜明地留在我脑海里,此后每当看见父亲晚年的形象,我都无法想象那就是当年的他。站在兴隆铺小学校园里的父亲,身材挺拔,面目清朗,眼睛里像有一股磁力,我第一眼看见他就被他吸引,他说话时我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他。下午的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眼睛里闪动着微笑,嘴角向两腮绽开,给人一种既威严又温暖的感觉。
他弯下腰,盯着我的脸,好像要把我的每个毛孔都看清楚似的。他想拉我的手,我没让他拉,当着老师和同学,我有点不好意思。
娘把手里的帕子提起来说,“饿不饿,乖,这儿有煎饼,你吃吧。”我把头扭过去,生气地说,我正上课呢。娘笑了。
父亲替我请了假,我提前放学跟他一起回家。走到学校大门外,他伸手拉着我,嘴角挂着笑,把我看了又看。他的手很大,把我的手攥得很结实。我走在他旁边,闻着他身上散发出的烟草味和军装气味,心里暖洋洋的,脸上直发烧。
跨进院子,我愣住了。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女孩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出现在我面前。八岁的我,面对这个陌生女人,心中泛起一种警惕。这女人眼睛很大,颧骨凸出,脸上带着笑,打量我的眼神让我不安。从父亲的神态和话语里我猜出了她是谁,一种被出卖、被欺骗的感觉代替了从学校一路走来的温暖。当她从提包里拿出礼物时,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父亲说,这是你阿姨在北京给你买的衣服和球鞋,不知道合不合适。
娘把衣服抖开让我穿,裤子短,褂子小,罩在身上像蚰子翅膀。那女人歪头打量着说,瞧,我说吧,买小了。娘笑着说,勉强能穿。那女人把球鞋塞进我手里,顺手拉过一张椅子。我没说话,也不看她的脸。我坐在椅子里不情愿地脱掉布鞋,把一只脚往新球鞋里插,穿到一半,就把脚褪出来。
她弯腰看着我的脚说,咋样?穿不进?
娘把鞋拿起来在手里握弄,安,找个鞋拔来,看能不能进去?我翻一下眼睛说,穿不上就是穿不上嘛——
父亲遗憾地说,没想到长安这么大了。
他俩失望的样子让我暗自得意,我根本不想要那女人的礼物。我轻快地跑出屋说,娘,煎饼呢,我饿了。
“他们本来应该住在盛屋里。我跟这个浑货已经离婚,用不着再管他。可文盛没立伙,他和五叔一直跟着我吃饭,叫这个浑货到哪儿去?
“卓娅睡着了,刘英把孩子放在我床上,和我一起收拾屋子。我把西间打扫干净,把床上的被褥换上新的,铺上他们从提包里拿出的床单,挂上门帘,安顿他们三口人休息,然后到厨房去做饭。”
我走进屋,站在床边看床上的女孩。她身上盖着一方小毛毯,嫩乎乎的小脸儿搁在枕头上,睫毛盖着熟睡的眼睛,小嘴唇翘起,散发出甜甜的奶腥味。这个不知从哪儿来的小东西睡在我床上,占着我娘的位置。那女人抱她、哄她、亲她,那样子让我生气。我伸手在她脸蛋上揍了一巴掌,她立刻哇哇哭起来,泪水溢满眼眶。
那女人从西屋跑过来,嘴里叫着妞妞,小卓娅!
我背手站在那儿,一声不吭地看她把女孩抱起来。
你醒了?乖,妈在这儿,妈在这儿。她伸出巴掌给她擦眼泪,女孩的脸有点红,她在她脸上看了一阵,然后像玩布娃娃一样掂起她的腿,给她换尿布。
那女人走后,我看着小女孩躺过的地方,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晚上睡在那儿,一股气味不断往我鼻子里扑。
卓娅?这名字真可笑。我嘟嘟囔囔说,我得叫她妹妹,是吗?
娘说,是。
从哪儿出来个妹妹?
娘在我头上拍了一下,人家过几天就走了,你想叫也叫不上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来了,往厨房抱柴,坐在灶前拉着风箱做饭。
“盛在地里干了一阵活,回来蹲在厨房门口说,太阳这么高了俩人还撅着屁股不起床,你凭啥伺候他?还给他们煮咸鸭蛋吃?
“盛,你不兴这样说,那是你哥、你嫂。不管怎么的,不能叫你哥在女人面前丢面子。
“我认得她是谁?一口洋腔洋调,听着叫人身上发麻。
“你这个盛啊——人家是跟那浑货过日子,回来看你,算是一份人情。
“盛还想说什么,看见昌从堂屋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说,盛,吃过饭咱俩去爷爷坟上看看吧?——这浑货真长大了,还能想到上坟祭祖,也算难为他了。
“盛不肯去,他说,我还得干活呢,想看你自己去。我说,吃饭吧,吃过饭我带你去。
“我陪他去给爷爷上坟,那女人在床上搂着小妞睡大觉。
“让她睡吧,昨晚卓娅闹了半夜,她没睡好。
“我往篮子里装了十个馍,到前街买了一捆烧纸,一挂鞭炮,还准备了一壶酒。
“他说,弄这干啥?去看看就行了。我没好气地说,你是干部,怕烧纸。我是乡下妇女,我不怕。爷爷去世你不在跟前,现在千里迢迢回来看他,难道连张纸也不烧?爷可没少为你操心,没少疼你!
“看见老爷子的坟,我心里止不住一阵酸痛。我把供品摆好,点了纸,洒了三杯酒。昌把鞭炮挂在小树上点着。在噼噼啪啪的响声里,他站在坟前鞠躬,我跪下给老爷子磕头。一跪下,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我呜呜咽咽地说,爷,你朝思暮想的文昌回来了。他给你带了一个外地媳妇,还给你带了一个重孙女。
“这个浑货傻愣愣地看着我,他不知道我为啥哭得这么痛,他不知道我心里有多少苦楚。坟头上的纸冒着青烟,转眼变成细灰,随风飞起来,呛到喉咙里。我迎着风呱呱咳嗽,他弯下腰拉着我的胳膊说,兰姐,起来吧。我扭一下身子,把他的手甩开,从地上站起来,掏出帕子擦眼睛。
“我知道这几年你在家受了不少苦。以后我回县里工作了,有啥困难你跟我说。
“我用不着你可怜!没有你,我把长安也养这么大,没灾没病,没磕着没碰着,健健康康的,谁见谁爱。回到县里,你当你的干部,我当我的农民,从前不求你,往后也不会求你。
“他把供品收起来,放进篮子,对我傻笑了一下,兰姐,你在家劳苦功高,我知道。
“你知道?军属牌挂在门上没半月,你的离婚信就来了,马文昌,你的良心叫狗吃了!你知道啥?
“本来我想再说他几句,看见坟园旁边地里有一群人,听见鞭炮响,停下手里活儿向这边张望。有人大声喊,嘿——那不是马文昌吗?啥时候回来的呀——
“他皱起眉头向地里望着说,那是谁?
“那不是马锁吗?你小学的同学。现在是土改积极分子,正领着工作组丈量土地呢。
“咱村的土地改革完成了?
“我扭头看着他,吃了几天公家饭,听你说话都带着干部味了。
“回家了嘛,能不关心家乡的事儿?
“土改完了,现在正在复查。
“文昌朝那群人走过去,我挽着篮子往镇里走。”
八月的乡野,高粱、谷子都已成熟,棉花绽开了花蕾,阳光迷离,风带着成熟的庄稼的气息。大路上的辙印弯向村庄的树影里。娘挽着篮子朝村庄走,父亲站在路埂上。见到小时候的同学,他心情开朗,满脸喜气。他掏出香烟让大伙抽,和他们亲热地交谈。
马锁把父亲递的烟接过去,夹在耳朵上。他和父亲开玩笑,问他从哪儿拐了个外地妞?当父亲问起家乡的土地改革进行得如何时,马锁的眼睛看着我娘的背影,马文昌,你真有福气,这女人跟你离了婚还对你们马家那么忠心耿耿。
父亲随着他的目光转回头去看我娘。怎么了?锁哥。
不是这女人,你家划定了地主。
父亲吃惊地说,我家没划地主?
群众评议的时候,兰姑娘拿出一份契约,说你家河滩里的二十五亩地早已卖给了老憨段根柱。
有这回事吗?
瞧,你是马家长子,都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
这些年我一直在外头,家里的事我没问过。
你还是回家谢谢这女人吧。
“这浑货跟从前大不一样了,见了乡下人比见了亲人还热乎,站在那儿没完没了地跟他们聊,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从寨外回到家,见到我,他的脸沉下来,黑乌乌的像要下雨。
“我说,咋?咱爷下葬七八年了,又不是今天才出殡,你吊着脸干啥?
“我问你,咱家为啥没划地主?
“你问土改工作队去,我又不是工作队。
“河滩里的地啥时候卖给段姨夫了?
“有契约嘛,看看就知道了。
“这个不讲理的开始发火,你这是转移土地,逃避革命!知道吗?
“我一个妇道人家,你们那些政策我不懂。我只知道我们文盛没享过一天福,他不应该当地主分子挨斗争。我也怕马家当了地主,连累我的长安。
“你不但转移土地,破坏土改,还害了段姨夫一家。
“那块地段姨夫种了那么多年,给他不比给别人强?
“你把一个雇农弄成了富裕中农,这是拉佃户下水,知道吗?
“笑死人了马文昌!我一个乡下妇女,跟我讲这些,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