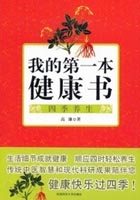“老憨姨夫把老爷子带到他家后院,把盖在红薯窖上的磨扇搬开,趴在井口说,昌——你爷来了。
“红薯井里传出他的声音,不是跟你说了,别跟他们说?
“民团到处抓你,你想连累你段姨夫?
“我明天就走。
“你走不了,昌。你要不听话,明天我送你进民团。
“送就送吧,随你的便。
“爷爷气得大口大口喘气。我什么话也没说,攀着井壁蹬着脚窝走下去。
“我抓住他,推着他的屁股把他往井口推。碰到他受伤的胳膊他喊叫了一声。我说,你不是登报要跟我离婚吗?为啥不敢回家当面说清楚?犯了事,躲在别人家,算啥男子汉大丈夫?
“他不动弹,也不说话。
“你不上去,我就和你一块待在这儿!看你明天走不走得了!
“段姨夫趴在井口说,昌,还是回家看看吧。事情到了这一步,明天你一走,不定啥时候才能回来,你爷这么大年纪,身体又不好,谁知啥时候才能再见啊?”
“爷爷带他从后沟走寨墙豁口进村,从后门回家。
“一进院门,爷爷吩咐我把前门、后门锁好,交代盛和老五叔不要对外人讲。
“我到灶屋去给他摊了几个煎饼,做了一碗汤,然后又烧了一锅热水。
“爷爷抬头看看他,站起来把房门插上。
“把灯端过来。
“我端着灯,昌跟在身后,三个人一起走进爷爷的卧室。
“老爷子弯下腰把他床前的踏脚板挪开,踏板下是方砖铺的地面。他拿笤帚把砖缝间的灰土扫去,掀开一块砖,用力往上一扳,下面露出一个方方正正的地洞。
“把腿伸进去,踏着台阶往下走,到平处再转身向上,头顶是一块木板。往上一推,出了洞口,走进一间房子里。
“这是个半坡厦屋,一面墙是爷爷卧室的后墙,另一面是侧屋的山墙。屋子不大,门前有一个窄窄的小院,被一堵短墙封死,从外边一点也看不出来。我在马家住了十几年都不知道爷爷卧房后面有这个暗室。
“我把铲子、扫帚拿过来,铲除屋檐外的杂草,把屋里的尘土打扫干净,床和桌子收拾好,铺上稿荐、被褥。
“收拾妥当之后,我说,马文昌,你写休书吧。
“他闭着嘴傻愣愣地看着我。
“不是想离婚吗?你给我写个休书,我立马就走。我到你们马家十几年,做了哪些错事?哪点对不起你?是打公骂婆,虐待老人?欺兄害弟,扰家不贤?还是偷鸡摸狗,不守妇道?写吧。写清楚。
“他垂着头一声不吭坐在床边。
“写呀!把我到你们马家这些年的过错都写出来!……
“眼泪骨碌碌往下滚。我掏出帕子,擤鼻涕,抹眼泪,可就是不当着他的面哭。
“你个没良心的,你为啥不写!
“这个不讲理的明知理亏又不肯低头,他把脖子扭过来说,我没说你有啥错。
“既然没错,你凭啥跟我离婚?你说!
“爷爷从卧房里走过来,兰妞,天晚了,明天再跟这狼羔子算账!
“我把热水给他提到暗房里。他胳膊不能动,还倔强地不肯脱衣服让我给他擦澡。我说,行,你自己洗吧,你不休我,以后别指望我伺候你!
“他褪衣服的模样儿很艰难,身上还有几处红肿。
“我回到堂屋,把酒坛打开,倒了半碗酒,在灯焰上点着黄表纸,放进酒碗。酒在碗里哗哗燃,扑出蓝莹莹的火苗。我用手蘸着燃烧的酒往他伤处拍,他嘴里一阵一阵吸溜,那样子叫我想起他小时候的模样。这个不讲理的,他只有受了伤,害了病,让我摆弄着,才会像个孩子一样温驯。”
“隔一天,民团的人又来了,为首的还是那个姓吴的区队长。他逼着爷爷要人,说有人看见马文昌回家了。
“爷爷说,前天你们不是搜过了?不相信再搜一遍!
“姓吴的说,我看还是委屈你跟我走一趟吧。
“我爷这么大年纪,他也没犯法,你凭啥抓他?
“那群人瞪着眼不讲道理。他们拿着枪。枪在谁手里谁就有理。
“我扑过去说,把我抓走好了,为啥欺负一个老年人?
“两个拿枪的人推开我,把爷爷带走了。”
那是一个深秋的上午。收割过的田野裸露出褐色的土地,村子上空的树木摇着快要落尽的黄叶。一阵锣声在兴隆铺街上响起,寨子里的人纷纷从家里走出来。他们看见一行人。敲锣的走在前头,几个人抬着一张方桌跟在后面,桌上蹲着一个老人,后边是一群背枪的团丁。他们本来是要太祖父跪在桌上的,老爷子宁死不肯,他们只好让他蹲着。这支队伍没打什么旗帜,也没扯标语,只是让王保长一路走一路敲锣喊叫,警告大家,谁看见共党分子知情不报,谁家人投了共产党,就得像这老头儿一样游街示众。
太祖父低垂着眼睛,两腿不停颤抖。他咬紧牙关,把心里的痛苦压迫在牙床上,腮帮绷紧,鼓出两道咬肌。为了使身子不至于佝下去,老人两手抱在胸前,抵着自己的胸口。
这位大清朝的最后一代秀才,为我们马家人游街示众开了先河。他为后辈人做出了榜样。他既没晕倒,也没坐下。队伍往前走时他蹲下,队伍停下来他就站着。那副模样活像一只猴子。他在秋风中坚持游完了兴隆铺的四街六路,还游了吊庄,大李庄,辛黄庄,三河码头。说起这段往事,娘的脸上总会重现当年的庄严,使我至今还能深切感受到家族受辱带来的激励。
“天色过午,老爷子被放回来。他是自己走回来的。脸色不好看,腿脚还平稳,走进大门的时候好像还没什么事儿。
“看他抬脚有点艰难,我紧跟着他。一进堂屋,他两腿像不当家似的直打摽。我赶忙走过去扶着他。他身子坠在我臂弯里,我使劲拉住,他才没跌倒。
“我勉强把他扶到床上。他一躺下就昏过去了。
“我到西街把戴先生请过来,给老爷子扎了一针,又拔了两个火罐。听到爷爷哼了一声,我悬着的心才放下一点。
“戴先生给他抚了脉,掰开牙关看看舌苔,然后开一服汤药。我到药铺去把药抓回来,煎好,给老爷子灌下去。
“天快黑时,他睁开眼睛咳嗽了一阵。
“我用新谷子小米给他熬了一碗稀饭,调了一碟小菜,扶他坐起来吃。
“他用筷子在碗里拨弄着,有气无力地说,昌呢?他吃了吗?我说,他吃过了。屋里人杂,不敢放他出来。老爷子垂下头慢慢喝汤。
“其实那个不讲理的昨天夜里已经偷跑了。老爷子受了这么大辱,躺在床上,我不敢对他说。
“爷被民团的人带走以后,我到厨房去做饭。我把饭盛在瓦罐里,坐上一个大碗,碗里放上辣椒、韭花、黑馍,把它交给盛,叫他到地里去给老五叔送饭。把盛打发走,我给昌舀了一罐饭,放上炒鸡蛋,花卷馍。我把堂屋门插好,掀开地道走下去。到了暗房,推开出口一看,屋里没人。我当时愣在那儿了,这个浪荡鬼,他跑哪儿去了?四边都封死了,他能插翅飞了不成?
“我在小院里仔细察看,看见屋檐下有块接脚石好像动过。走过去一看,石板挪开处露着洞口。想不到暗室小院还有一个出口。和上房屋的地道一样,下去后是一溜台阶。地道很长,走到尽头,坡顶是出口。用手一推,看见亮光。钻出去,是马家的坟地。不知马家哪一代人修建了这处暗室地道,让这个机灵鬼找到了出口。
“半夜过后,听见爷爷在上房屋里咿咿唔唔说话。我把灯点着,端在手里走进去。老人家像发高烧似的昏昏迷迷,喊着昌的名字。
“我把灯放在桌上,倒了一碗水,递到他面前。我说,爷,你喝点水吧。他迷迷糊糊说,昌呢?叫他过来。我说,天这么晚,人都睡下了,别惊动吧。
“老爷子喘着气说,兰妞啊,你到马家十几年,受了不少苦。爷对不住你,对不住你爹妈。
“爷,你喝口水吧,别胡思乱想。
“上辈子欠了狼羔子的债,阎王爷托生了这个败家子,冤家……对头……他翘起头喝了一口水,气喘得更厉害。我怕是不行了……兰妞。
“爷,你再喝点镇心丹好不好?好好睡一觉,明天就好了。
“这狼羔子不是人,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还有盛,这弟兄俩……哪个能叫我放心哪?兰妞,咱马家……真该败了吗?
“他说话的气力越来越弱,话头儿越来越零乱,脸上泛出一层明晃晃的颜色。我心里好害怕。我到牛屋去把老五叔叫起来。
“老爷子气色不对,快套车送他进城吧。
“老五叔忙着牵牛套车,我把盛叫醒。盛,你到吊庄去一趟,把段姨夫找来,对他说咱爷病重,叫他过来帮帮忙。
“盛揉着眼不想去。我知道盛胆小。
“我给你点个灯笼。啊。我把你的泥叫鸡找出来。你打着灯笼,吹着叫鸡,吹响点。”
月亮正在落下去,霜露把太祖父身上的被子打湿了。牛车在通往县城的大路上摇晃,太祖父的身子随着车身颠动。大路上的辙印很深,铁轮车发出咯咯噔噔的声音。在黑沉沉的田野上,老五爷吆牲口的声音传得很远,时不时夹杂着清脆的鞭响。
娘靠在车帮上,蜷腿坐在太祖父身边。隔一会儿伸手到被子下去摸摸他的额头,张开手试着他鼻子上的气息。
天快亮的时候,娘说,老五叔,你停一下。
老五爷拉长声音吆了一声“吁——”两头牛慢慢站下,老五爷从车辕上跳下地。
“你来看看……”
老五爷把太祖父身上的被子掀开,低下头仔细看了一阵,轻声喊,“二叔——二叔——”太祖父没有反应。晨光照着一张静止不动的脸,眉棱、眼睛、鼻子、颧骨全都如枯菜叶一样失去了光泽。
“我俯下身冲着他的脸喊,爷——爷——喊了一阵不见动静。老五叔赶快吆牲口往回转。兰妮,你可不要哭!野地里风大,喝了风病倒了,谁给你爷爷料理后事?
“老爷子的身体越来越僵硬,回到家没法给他换衣服。我只得临时缝了一件青布大褂,勉强给他罩上。
“那会儿我心里想,爷爷把钱放哪儿了?昨天夜里老五叔套好车,把爷爷抬到车上之后,我在桌子、柜子、枕头、褥子底下找过一遍,只在床头下找到几张小票子。这些年兵荒马乱,老爷子对家里的钱财特别精心,我知道他藏放的肯定有银元,可不知道埋在哪儿了。
“把爷爷停放在堂屋里,在他头边设了祭案,摆上供香,放上老盆,让盛披麻戴孝跪下守灵。我偷偷拿上镢头溜进后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