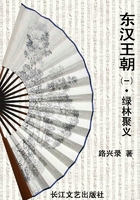娘说:“你出生那天有只黄鹭在树上叫:不苦不苦!”
“天不明我就起来了。老爷子想吃新高粱面,我收拾了一筐高粱,一箩小麦,让老五叔到磨房里,把它掺匀了倒在磨顶上。往磨屋走的时候眼皮子一个劲儿跳,我掐了一片黍秆皮儿贴在眼泡上。心里想,眼皮跳,要出啥事儿?
“老五叔把驴套好,给它戴上蒙眼罩,吆了一声呔!在它背上拍了一掌。文盛拿上小簸箕,跟在驴后绕着磨盘收粮食。他把收起的粮食倒在箩里。别看盛脑子不好使,读书不行,干活他还真给我帮了不少忙。我起多早他起多早,跟着干活,不打瞌睡。
“我坐在脚打箩的墩子上踩着箩锥筛面,老五叔蹲在磨房门口抽烟。我说,你不是还得犁地吗?你走吧,这儿有我们俩就行了。
“谁知这头驴精得很,老五叔一走,它就开始偷懒。先是放慢蹄子走走站站,后来干脆站下不动。我在它屁股上拍一下,它没精打采走一圈,再拍,它就死皮赖脸站在那儿。我没什么手劲,拍不疼它,倒把自己巴掌拍疼了。盛拉出一根棍要打它,我说,你还是去找五叔吧,别把它打毛了踢人。
“盛去叫五叔,我把磨盘上的碎粮食收起来。不大一会儿,盛跑回来说,兰姐,王福禄来了。我说,他来干啥,大清早的?
“来了一群人呢,都拿着枪。
“我从箩墩上站起来,把腰里的围裙解掉,走到前庭去。
“一群人已经进了客屋。为头儿的屁股后挂着盒子枪,其余几个人背着长枪。
“老爷子站在桌边。王福禄伸着手让他们坐。我走进去说,王保长,大清早的,这是咋回事呀?
“这是咱们县民团的吴队长,他要找文昌。
“一听文昌这两个字,我的头轰一下就蒙了。我连声追问,文昌怎么了?他出什么事儿了?
“姓吴的盯着我上下打量,像审贼似的看着我说,你是马文昌什么人?
“我是他内人。
“马文昌在哪儿?
“他不是在陕西吗?在那儿教书。
“他不在陕西。你最好把他交出来。
“我从鼻子里嗤了一下,我把他交出来?他一年多没回家,我到哪儿去把他交出来?
“老爷子也插上说,是啊,他一年多没回来了。
“那人把眉毛一竖,昨天还在旗杆寨,今天就到陕西了?
“我笑了一下,旗杆寨?他到旗杆寨干啥呀?没亲没故的。你没弄错吧?
“好了,好了!对不起老先生,我们这是公事公办。
“看他要搜查,我说,爷,你陪保长在这儿坐,我带官长去看看。
“前院、后院、车棚、磨房他们都搜了,连茅房也进去看了看。把箱子、柜子、神案、粮食囤全都翻个底朝天。
“我站在那儿插着手说,还有个地方没看哪。
“哪儿?
“鸡窝你们还没看,那里头说不定能钻个人呢。
“姓吴的冲我眨眨眼,我往地上啐了口唾沫。
“民团的人一走,老爷子歪在椅子里嘴唇发紫,说不出话来。我赶紧给他倒水,从抽屉里拿出镇心丹,扶着他的头让他喝下去。
“过了一会儿,老爷子喘口气,长叹一声说,昌啊昌,我这条老命迟早是要丧在你手里呀!
“我说,爷,你老人家别那么操心。是风是雨打门里来,文昌没在家,他们找不到他,想抓也抓不到不是?
“老爷子眼看着门外,自言自语地说,他到旗杆寨去干啥呀?
“你忘了,爷,旗杆寨不是有他的同学?
“老爷子想起来了。他头一仰,噢了一声,你是说林家那孩子吧?
“其实民团的人一说旗杆寨,我当时就想到了林春生。昌和他最要好。到难童学校教书不就是他邀去的吗?两人都是从留洋预备班出来的,一样的不安分。他俩在一起,早晚不得惹事?
“我把他们翻乱的东西收拾一下连忙往磨屋走。一进磨房,看见那头驴正扭着头在磨盘上舔吃粮食。我抄起棍子照它屁股上就是两下,打得它绕着磨道飞跑,把磨盘拉得呼呼叫。
“我做了一锅高粱面糊粥,贴了几个高粱面锅贴,调了一盘辣椒。这是老爷子最喜欢吃的。爷爷端着碗呼噜呼噜喝了几口把碗筷放下,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桌子。文昌他到底犯了啥事啊?
“我说,爷,他们不是搜过了?人不在家,谁有啥办法?你别着急,待会儿我去找王福禄,看民团的人是怎么说的。
“我嘴里劝着老爷子,心里七上八下琢磨。这个浑货,他不是在陕西教书吗,怎么会跑到旗杆寨去闹事儿?
“我去找王保长。王保长说,八成马昌是入了共产党了。听吴队长说,前天他在旗杆寨把一个团丁打伤了,民团在到处抓他。
“我从保长那儿回来,老爷子到旗杆寨去了。老五叔说他坐立不安,不放心,一定要亲自到旗杆寨去一趟。
“别看我嘴上劝他,其实心里比他还着急。文昌给家里写的最后一封信是6月,麦子才收罢,秋庄稼刚种上,日本人还占着县城。转眼秋庄稼都快收完了,日本鬼子也投降了,听说迁到陕西的学校都在往回迁。这个浪荡鬼连个信也没有。那些天每天一起床我就看见爷爷在墙上写诗,‘夜梦不祥,写在东墙,太阳一照,化为吉祥。’这是他的老套子,夜里只要做了不吉利的梦,第二天一大早他都会在太阳出山之前把它写到墙上。”
“爷爷从旗杆寨回来天都快黑了。他两手背在身后,佝偻着腰,老远就能看见下巴上的胡子乱蓬蓬地向前翘着。扎着腿带的裤脚沾满黄土,两条腿像掂不动似的,身子一晃一晃,满脸灰白,一进堂屋就歪坐在大椅子里。
“我给他倒了一碗茶,点上灯。他把烟袋接过去,放在桌上,一声不吭,黑着脸靠在椅子里。看他手里攥着一张报纸,我心说,这是从哪儿拿的报纸啊?
“爷,你见着林家人了?
“他不吭声。
“我又问,文昌他真从陕西回来了?
“爷爷把手里的报纸啪地摔在桌上,马文昌死了!
“我瞪大眼看着他,闹不清他的话究竟是啥意思。
“我没这个孙子!马家没他这个人!
“我知道昌一定是闯了大祸,把老爷子气坏了。我说,爷,你别生气,自己孙子,你还不知道他啥脾气?你说这浪荡鬼把天戳破了我都信。
“登报!他还有脸登报!他把报纸抓起来又摔了一下。
“我想把报纸拿过来看看,爷爷不让。他一把抓起来,把它揉成一团,扔在门后,拿脚跺了跺。从今往后,咱们马家没他这个人了!
“我给他擀了一碗豆面条,放上芝麻叶,把酸腊菜和韭菜花端上来,浇上点小磨油。
“爷,你再生气那个没良心的他也不知道,气坏了身子,还是自己遭孽。
“爷爷突然用手捂住前额呜呜哭起来。
“来到马家十几年,我还没见过爷爷这么伤心。我站在那儿默不作声地看着他。
“他一边哭,一边呜呜咽咽说,都是我把这个小畜牲惯坏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送他到省城读书,让他学洋文,把礼义廉耻都给扔了!我这是自作自受啊。”
太祖父没把他到旗杆寨见到林家人的情况告诉娘,也没把父亲登报离婚的事对娘说。哭过一阵,他站起来,走到脸盆架子那儿,拿起毛巾,把脸擦干净,还不忘把他的胡须擦擦,然后坐在桌边,就着韭花吃芝麻叶豆面条。
屋里点上了灯。太祖父的腮帮在灯影下嚅动。娘把蒸好的高粱面馒头递到他面前,看着他的脸说,“爷,他是不是真回来了?”
“你太祖父把黑面馍掰开,放在嘴里慢慢咀嚼。过了好大一阵,抬起眼睛看着我说,兰姑娘,咱们权当没这个狼羔子。以后永远别在我面前提他。
“趁老爷子起身漱口,我把门后的报纸捡起来。我想看看报上到底有啥东西让爷爷这么伤心生气。
“我回到自己屋里,把报纸一点一点抻平,拨亮油灯,伏下身子细细寻看。小时候读过几天三字经、百家姓,报上的大字还能磕磕巴巴认下来。找了半天,让我找到了。
“不知是好气还是好笑,我对着桌上的报纸连拍了几巴掌。这不讲理的想得倒美,登个报,就算跟我离婚了!
“爷爷走进来,站在我身后说,这个小畜牲,叫民团抓走的时候人家救过他的命啊,他倒好!差点把林家的妹妹拐跑!瞧这儿!你瞧!老爷子用手指着另一行字,这闺女把那么好一桩婚事都退了!作孽呀!人家把女孩从西安带回来,这个没出息的,竟然追到旗杆寨去跟林家闺女偷着见面!还要带她跑……胆大!真真胆大!
“老爷子没说完,我哇一声哭起来。马文昌,你个没良心的,你的心都叫狗扒吃了?
“他登报也是白登!三媒六证当着乡亲们拜过天地,他说拉倒就拉倒?没那么便宜的事儿!你别生气,兰妞,有爷爷我呢!明天我进城,我也登报,跟这小畜牲断绝关系,以后他死了也不准进咱马家的坟地。
“爷爷刚说完这些绝情话,老五叔来到房门口。他说,吊庄的老憨来了。
“我连忙擦干眼泪走出去。
“廊檐外黑影里站着一个人,我一直走到他跟前才看清他的脸。我说,段姨夫,你咋不到屋里坐?他说,我就站这儿吧。
“老爷子探出头说,老憨,你吃饭没?快进来,进屋坐。
“他把段姨夫引进堂屋。段姨夫站在爷爷面前,吞吞吐吐说,听说今天民团的人到家来了?大少爷……他……
“段姨夫你是不是听到了啥消息?
“……大少爷——他没啥事。二伯你放心。
“你见他了?他在哪儿?
“旗杆寨的团丁想抓他,他和他们打了一架。
“他伤着没有?伤得咋样?
“没事,只是胳膊扭伤了,一两天就会好。
“爷爷从椅子里站起来,直盯着老憨姨夫,他,是不是在你那儿呀?
“昨天晚上刚喝罢汤,小辫她妈正在灶屋里刷碗,有个人从陈刺砦后头闪出来,走进院子。我走过去一看,是大少爷。
“这狼心狗肺的!他真想和家里断绝关系不成?
“他怕您老人家生气,说是躲一两天就走。
“没人知道吧?
“我把他藏在红薯窖里呢,没人看见。
“爷爷拿出一条香烟,一包点心,算是对老憨姨夫的酬谢。
“兰姑娘,你去,把这小畜牲给我接回来。
“我站在那儿没动,我的气还没消呢。
“老爷子叹了口气,都是我的罪孽,还是我自己去吧。
“打开后门的时候,我决定跟爷爷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