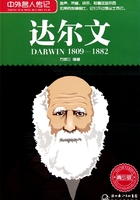他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到安迪的背景,吃惊地发现,这真的不是一个能够随便招惹的人,这样一来,更加不能放心。于是第二天立刻请假来G市。只是走得太急,只能买到傍晚的机票。下了飞机,便直奔Z大,谁知刚来到中文系宿舍楼外,便看到了这令他呼吸停顿的一幕。
若不是临时决定了来G市,或是再来迟一些,她还不知要遭遇到什么。只要想到这些,他心中便是一阵后怕,又觉一阵心疼。
然而转头看看,还好!身旁的她安静地走着,已经及腰的长发披散着,额前的刘海有些凌乱,垂下来遮住了那张熟悉的脸庞。胸膛里那颗凌乱的心,终于宁定了。于是这一日一夜来的种种忧心、焦虑、急迫……都只化作一声轻轻的叹息。
梅飞飞偷偷看了看他,路灯之下,显然脸上有些伤痕,不禁心里微微一疼,轻声问道:“你……伤得厉害吗?”
傅远侧过脸,淡淡一笑:“我保证他比我伤得更厉害!”
梅飞飞抿了抿唇,扭过头去。
“飞飞,你总是心软。”他的语气里有一丝无奈,“他就是看准了你这一点。”
“是啊!我也很讨厌自己这样心软。”她笑了笑,又认真道,“可是,难道你真的要把他打死不成?你可知他是什么人?”
傅远“哼”了一声:“知道。”
“知道?”梅飞飞皱眉,“知道你还下那么重的手!要是他出了事,你一定会吃亏的!”
他蓦然停住,她不解地转头,却迎上他深邃的目光:“飞飞,你能不能少考虑别人,多为自己想一想?”
她一怔,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远在B市,而安迪,近在咫尺。他不可能每次都像今天这样来拯救她。如果没有人能保护她,他宁可帮她永远除了这个后患。刚才那句话,真的不是开玩笑!
想到这些,心里突然有了复杂难言的感觉,既有感动,却又有一些歉疚与……不安。
他怎么能爱她到这种程度?这种爱,对于此时的她,未免太过沉重了。
“飞飞,我不需要你为我考虑。”他像是看穿了她的想法,“我只想要你好好地活着,得到幸福。”
他说得极认真,极诚恳,语气执着,态度坚定。梅飞飞顿时觉得一股热流从心头淌过,又涌上了眼眶。她急忙狼狈而逃避地扭开头。
傅远将她的一切细微表情尽收眼底,见她如此,也不以为意,只是温和地一笑,重新朝前走去。
学校里就有招待所,傅远办理了入住。梅飞飞在小药店里买了些药水和棉球,回到房间先拉着他处理伤处。
所幸安迪有一只手使不上什么力气,但尽管如此,傅远脸上还是青了几块,嘴角也裂了个小口,血渍已经干涸,凝成了血痂。
梅飞飞用棉球沾了消毒水小心地帮他擦拭,血痂终于擦掉的时候,消毒水在伤口引起一阵刺痛,傅远嘴唇一抖,眉头紧紧地拧了一下。
“怎么?很疼吗?”梅飞飞着急地问,不由自主地朝他伤口吹了吹凉气。
两人站得很近,此刻她柔声细语,吐气如兰,傅远顷刻忘记了伤口的疼痛,不禁心荡神驰,如在梦中。
梅飞飞吹了两下,蓦然反应过来这动作似乎太过亲昵,再看傅远,只见他眉头早已舒开,却只是痴痴地盯着自己。于是脸上一红,急忙羞赧地退到一边,有些尴尬地道:“好了……”
“飞儿……”傅远上前一步,有些沙哑地低唤一声。
不料,这近乎呢喃的一句,却使梅飞飞如遭电击地全身一震,让她猛然从暧昧的氛围里冷静下来。
飞儿!这极其熟悉的两个字,这曾专属于极其亲密的某个人的称呼,她怎么可能忘记!她更不会忘记,那个人后来是让她如何地失望如何地伤心!而那个人……是眼前这一人吗?
“不要这样叫我!”她的语气突然变得冰冷。
傅远蓦地一怔,眼中的热情渐渐消散了,看着梅飞飞冷下来的表情,他的眼中快速地掠过一抹悔恨,随即很快地转开头,勉强一笑:“对不起,我唐突了。”
见他如此神情,梅飞飞不觉又有些歉然。
眼前这个人,不再是前世那个人!
眼前这个人,他千里迢迢地赶来,为她打架为她受伤,而她连个好脸色也不给,实在有些过分了。
抬眼瞥了瞥,他已经走到窗口,一手拉开了窗帘似乎在看些什么,看不见他的表情,那背影却显得格外落寞。
“傅远,以后还是叫我飞飞吧!我……不喜欢人家那么叫我。”解释的话脱口而出。
他转回头,一瞬间她好像在他脸上看到了忧伤,但再仔细看,却只有温柔的笑意:“好,我知道了。”
中午时分,阳光火热,但茂盛的树木却为人们撑起一方阴凉。一粒粒青翠圆润的芒果诱人地挂满枝头,白玉兰的幽香弥漫在空气中。
看着不远处正细细低语的两个男人,江玉容捅了捅梅飞飞:“喂,你说他们俩在说些什么悄悄话呢?”
梅飞飞耸肩:“我哪儿知道呀!”
“那,你说傅远为啥一定要见周子易?”江玉容又问。
梅飞飞睨她一眼,懒得回答。
傅远第二天就要回去,临走之前他提出要见周子易。其实,个中的原因,梅飞飞可以猜到:他是想说服周子易不要再追究张凡的过错,从而息事宁人。
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