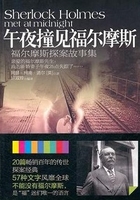赵光义觉得心中苦闷,除了发呆,什么事情也不想干。死死地盯着窗外那一方荷花池,就盼着有什么奇迹出现,哪怕一丝风吹草动,都能勾起赵光义的兴趣,就算最后只是以失望收场,也不在乎每一次的空空等侯。
那窅娘到底是何许人也?是人?是鬼?赵光义不得而知。但是赵光义心中并无恐惧之感,这种一见钟情,就算是鬼,他也要爱她一回。
赵光义走出寝宫,来到院子里面,靠近荷花池的时候,他故意放慢了脚步,轻轻缓缓地向着池边的荷叶走出,生怕有一些不温柔之举,就能将那些荷莲吓跑一般。他轻轻坐在池边,将龙靴脱掉,把脚放在了水里,冰冷之感立马传遍全身,甚是酥麻。赵光义闭着双眼,好像很陶醉的样子。
他渐渐沉醉其中,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身在何处。
突然,一声“父皇”从赵光义的身上闪了出来,吓了他一跳。这一声又硬生生地将他拉回到现实,心中极为不快,但听声音就知道是谁,所以也是轻轻责备,脸上虽然有些难看但也未转过身来,只是背对着她说道:
“父皇在思考问题,你岂能擅自闯进来。”
那人轻轻一笑,在赵光义身后欠了欠身,说道:
“女儿知罪了,女儿担心父皇寂寞。”
此女儿不是别人,正是七公主怀柔。
赵光义看着池中点点莲花,自知今日又是无果,但他并不怀疑窅娘的真假。那一夜她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是如此的真实,就连她的呼吸也能感受得到。但荷花池中依旧平静,就算是一点点涟漪,也算是啬望。
七公主见赵光义对着荷花池发呆,不明事理,便问道:
“父皇有何心事,女儿愿来分担。”
赵光义长吁了一口气,一股郁闷也渐渐散开。他转过身来,将双脚抬了起来,水珠一滴滴地从脚跟滴落下来,滴在草丛中,就像把自己的心事,一滴滴说出来后,却又要藏在草丛里,隐没起来。
“朕只是觉得心中苦闷,若能此刻有一曲琴音该有多好。”
“让女儿为父皇弹奏一曲吧。”
说完,七公主命人取来长琴。她席地而坐,也不管那些高贵姿态,就这样很随意地坐了下去。她手扶琴弦,首先以一曲低音迈进,舒缓自然,渐渐拉开,随着音律的调高,变幻得十分空灵,仿佛真有某种仙物在这院中漂浮一样,亦真亦幻,又拖着赵光义坠入相思。直到最后一个音符又回到轻柔之上,才缓缓结束,似乎又有无数个尾音延绵不绝,飘荡,飘荡,直至飘到人的心里。
七公主抬头再去望望赵光义时,觉得父皇此刻比起刚才更加沉闷了许多,脸上强作欢笑,却瞒不过怀柔的眼睛,她知道父皇心中难受。
“女儿的琴音太过于忧伤,引起父皇不快了吧。”
“朕知道你的一片孝心,只不过这琴音并非能改变人的心情,相反是心情可以左右琴音了。”
“也许是女儿琴艺不佳,不妨命琴医前来一试?”
赵光义突然心中一动,想起那夜正是自己的一曲酣畅淋漓的琴音才使窅娘现身,而从此之后,他再也弹不出像那一夜的琴声了。也许,现在只有琴医之技方能了却心愿,就算窅娘不再现身,就凭琴医的医心之术,或许也能减轻相思之苦。
“还是女儿知父心。”赵光义装出无奈之色,说道,“罢了,罢了,传琴医吧。”
七公主轻轻点头,心中却也是高兴无比,只是女儿家总应该害点羞,不适合将此心情表露于外。她随意地拨弄着琴弦,或者亲自为赵光义端来茶水及桌椅,这一举动好像是在为等琴医的琴声做好准备,其实她的心里是激动的,惟有多做些事情,方可以隐匿一些。
稍时,琴医闻旨前来。在庭院之中,向赵光义跪安之后,第一眼就看见了赵光义身边的七公主,此时刚好是眼神相对,他俩都是心中一动。琴医不敢思辩,立马就取出琴来,正要演奏。而七公主没有这么多心思,身到他的身前,一边拨着琴弦,一边轻声说道:
“心很乱吗?当心弹错了音调。”
琴医不作回答,只是拱手说道:
“请公主放心,草民的琴音可以安抚所有人的心。”
“哼,但愿如此。”七公主又退回到赵光义身边,说道:“父皇,这琴医爱说大话,他说可以安抚所有人的心,如若他办不到,或者不能使父皇痊瘉,可要治他一个欺君之罪了。”
赵光义摇着头轻轻笑之,对琴医说道:
“琴医,你都听见了,以后说话要收敛一些。”
“草民尊旨。”
随即,琴医的琴声由一个轻快的节奏迈进,但每一组音律都变化无常,似乎是跟随著人的心而变动,又似乎这人心是跟着琴音而变,谁也分不清原由,只知道这音律和人心就像风一样捉摸不定。
琴音终止,这三人都沉默良久,他们的心思纷纷飞到各自想去的地方。
赵光义的心思飞到了荷花池中;七公主的心思飞到了琴医的心里,而琴医的心思呢?他也说不清,只是觉得怪怪地,他找不到自己的心思在哪儿,只是时不时地偷看一下七公主,看她是快乐,还是忧愁。
“皇上,你有心思。”琴医突然开口说话打破了沉默,但是他立马就察觉这句话是多么的傻。
“废话。”七公主在一旁说道,依然是一副公主模样,不过眼神中少不了关切或者调皮。
“不可无理,”赵光义轻声责备,“琴医知朕有心思,必有解救之法。”
“回皇上,此心思不好救。”
“哦?此话怎讲?”
“应该说,这一次皇上的心思不在自己心里,所以草民不好救?”
“哼,”七主公觉得好笑,“这自个儿的心思不在自己心里,还能在别人心里吗?”
“正是。”
“那你说说,朕的心思在谁的心里?”
“李煜。”
赵光义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句:“在谁心里?”
“李……煜。”琴医放慢语速,将李煜二字说得甚是言重。
赵光义不断摇头,心想,这琴医终于还是有失足之时,不禁问道:
“琴医啊,你这一次可没能看出朕心病的根源在哪儿?”赵光义望了望七公主,又转过脸望着琴医说,“朕的心思为什么不能放在天下百姓的心里,为什么不能放在国事上,为什么不能放在女人身上呢?就偏偏要放在那李煜的心里?”
“回皇上,您的心事当然可以放在天下百姓,国事,就算是女人的身上都无可厚非,这些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是您的心病之源正是因为李煜。”
“为何?”
“皇上不妨命李煜前来,将自己的心中苦闷说给他听,就能在此找到答案了。”
赵光义又望了望七公主,问道:
“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七公主用眼睛瞟了一眼琴医,心中难免有些担心,不过她还是肯定地点头:
“女儿相信,父皇不妨叫那李煜前来,一试便知。”
赵光义沉思片刻,大声喊道:“召李煜进宫。”
另一边厢,那李煜得知自己升为翰林院总撰官,心中满是疑问,自从陶谷下狱那时起,所有的事情都让李煜想不明白。但是想不明白之事,他尽量不想,因为他没有太多心力去应对官场,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逃离汴京,寻找白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