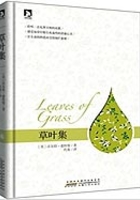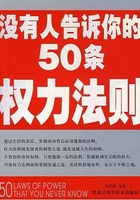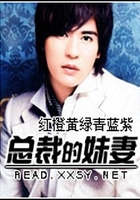冯至先生这时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他每星期进城两次,一次步行十五里。就在这样的行进中,他完成了充满现代精神的《十四行集》的写作,而这种堪称是象牙塔中精品的作品,却是在战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产生的。冯先生回忆这些十四行诗的写作时说,“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十四行集序》)
与联大的师生们创作那些现代诗的同时,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前些日子我访问腾冲参观了滇缅战争纪念馆,史料记载说,那场战事极其惨烈,我方付出了伤亡二十万人的代价。1942年3月8日中国远征军失去侧翼,同古失守,曼德勒、腊戌、八莫、密支山陷落,时年六十二岁的史迪威将军,身着士兵服,肩背卡宾枪,与远征军一起撤退野人山。援缅的中国远征军十万三千人中幸存四万六千余人,伤亡近百分之六十。在这些士兵中,就有联大的学生。
联大的师生,倾心于科学和艺术,写着精美的诗篇,却是从来不忘社会盛衰、民族兴亡。
据统计,联大先后有学生8000余人,参军人数达834人,平均每一百人中,就有十四人参军。穆旦、杜运燮的一些经典诗篇都作于军中。这是杜运燮的《滇缅公路》——
歌唱啊,你们,就要自由的人路给我们希望与幸福,——给我们明朗的信念,光明闪烁在前面,这是穆旦的《赞美》——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躇我踟躇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巳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巳经起来。
我进北大是1955年,当时正是中国的“百花时代”,到处弥漫着早春气息。战争已经远去,建设正在展开,生活开始了新的内容。当时我们大学生活中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向科学进军”,学校号召我们争当“先进集体”。北大在马寅初校长的领导下开始了充满理想的无忧无虑的学习生活。
我在入学的第一学期就参加了“北大诗社”。在开学之初,诗社发表文告,向新同学介绍北大诗刊:“北大诗刊是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创刊的。在创刊号上,诗人力扬在《给青年诗歌工作同志》一文里写道:‘被共产主义思想所照耀着的英雄时代,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前进着的我们伟大的祖国,每时每刻都出现着无数新生的美妙的事物,值得我们去歌颂。’一年多以来,它已经成为热爱诗歌的同学们亲爱的伴侣,同学们喜爱诗刊上登载的诗,也愿把自己的诗拿出来发表。到现在为止,《北大诗刊》已经出了十六期,诗刊的编辑从内容到形式都在不断地改进着。”当年的诗刊是十六开本,人工刻写,油墨印刷,封面是简单的套色。记得每本售一角钱。我参加诗社好像是有老同学介绍,他们不知从何得知我有写诗的经历。这一年的年末,我写了迎接新年的诗:《一九五六年骑着骏马飞奔而来》。
50年代北大最重要的学生刊物是《红楼》。《红楼》筹划于充满幻想的1956年,而于1957年元旦正式出刊。我参加了出刊的筹备工作,创刊后担任诗歌组长,张元勋和林昭都是诗歌组的成员。《红楼》周围集聚了北大最活跃的作者,尤以诗歌为甚,这时我认识了众多的北大诗人,除了张元勋、林昭,还有李任、马嘶、沈泽宜、蔡根林、杜文堂、王克武、孙克恒、孙玉石、刘登翰、江枫、任彦芳等。
《红楼》的创刊号上,我们延请中文系的林庚先生为之写了序诗,百年校庆前后经马嘶、张元勋和我几人核对,是这样的四句整齐的“林庚体”: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
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青
在当年的北大诗坛,女诗人很少,才华横溢的林昭就格外引人注意。她曾以任锋为笔名为一张照片题诗:
世界是这么广大
友谊是这么真诚
生活是这么美好
我们又这么年青
这四句诗代表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我们的思想情感。当年我们是非常纯真、甚至是非常天真的一群。这种纯真和天真,不单是由于轻信,而且也由于发自内心的热爱。那时我们不会、也不敢怀疑。我们的坚信一直延续到梦想被现实的打击而破灭的最后。在我们的同辈中,有人因才华横溢而遭不幸,其中最让人扼腕的是林昭之死。这一点以后将有叙说。
1957年的春天依然美好。《红楼》编辑部的同人们,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结伴出行,我们“沿着‘五四’的道路”从“民主广场”出发,经赵家楼,过段祺瑞旧宅,直抵天安门。事后写出了一批纪念“五四”的诗歌,这些诗歌在那年五四广场的簿火晚会上朗诵。张元勋的回忆文字《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记述了1957年5月4日夜晚在北大广场上的簿火晚会与诗歌朗诵的盛况:
当时,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主席台上把第一支火炬点燃,递给站在台前二级台阶上等待传递的第一位同学1那同学接了火炬转身把主席台下的数十支火炬顷刻点燃,那数十支火炬又把等待着的数千支火炬点燃,整个操场顷刻之间变成了火炬的海洋,光明的海洋,炽热的海洋,呼啸的海洋!而诗朗诵便在高音的麦克风里响起!林昭站在主席台的南侧,她是为诗朗诵做“顾问”的,她看着那翻动的火炬之山,火炬之海;听着那诗歌之风,诗歌之雨,而在这诗与火、声与色、灵与情、静与变的美景里沉思着,她只是看着。
最后,所有的火炬都堆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座山,涌起了凌空的烈火,把东操场照得如同白昼。数千北大儿女在这火的周围,鼓掌、跳跃、呼喊、歌唱一直到夜深。斗转星移,余烬渐熄。我与林昭离开这里时,晨光熹微,巳是5月5日的早晨。
5月是乍暖还寒的季节。而我们依然沉浸在春天的诗意之中。1957年的5月19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那日,《红楼》编辑部的同人相约前往颐和园。因为临近学期末,暑假来时一些高班同学要离校,借此小聚也是,亦有预为话别之意。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大家心情都很好。林昭那天带了一架照相机,我们在排云殿前有一个“全家欢”。我不会吉他,却是抱了它做样子。1998年12月11日《南方周末》发表张元勋文章时用的就是这张照片。红楼的诗人们大部分都在其中,马嘶、李任、孙克恒、薛雪、康式昭、谢冕、任彦芳、杜文堂、张钟、张元勋和林昭。因为是林昭摄影,所以画面上没有她。
那日大家玩得尽兴,回到学校已是黄昏。当晚大饭厅举行全校大会,天气已暖,学生们,饭厅外的广场上也坐满了人。散会时人头簇拥,大家争看刚刚贴出的大字报,有一份是诗,赫然写着:《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向着我们的今天
我发言!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今天,
我要鸣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鞭笞阳光下一切的黑暗!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
诗的作者是我同系的同学,也是一起写诗的朋友沈泽宜和张元勋。这是1957年的5月19日,是我们同游颐和园的那个日子。我们下午刚刚从颐和园回来,晚上就贴出了这张大字报。《是时候了》发表的这一天,被不同的人分别叫做“五一九民主运动”或“右派进攻”发端的日子。这一天对于我,也是刻骨铭心的。作为《红楼》的成员,作为这首诗作者的朋友,我受到了激烈的震撼,且陷入痛苦的内心冲突。就我个人当时的心理,我为他们的勇气所折服,同时又有某种惊恐。
《是时候了》引发了大论争,赞成的和反对的都有。对这首诗,我也是充满了矛盾的心情,由于谨慎,也由于胆怯,当年我的态度是暧昧的。《红楼》编辑部在上面的授意下决定开除张元勋和李任——因为他们所谓的“右派言论”,我也举手“赞成”了,记得林昭也是赞成的。那时 我们内心有矛盾,也有顾虑。就这样,1957年关于诗歌的第一场悲剧开始了。随后是张元勋和李任被捕,《红楼》改组,随后被改编成《北大青年》,那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刊物了。
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也由于我自己认识的改变,我对自己有过反思。我铭记着1957年的早舂时节的那一声无畏的诗的呐喊,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酷的天谴。我在内心深处敬重我的诗歌朋友,我永不会忘记当年石破天惊的那些激昂的诗句。1996年我出任《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诗歌卷》的主编,在考虑选目时,貧先想到的就是将《是时候了》正式入选。这在我,是想通过我的工作为这首诗正名,其次,也是将我自己对于历史的反思公之于世,也是对当年遗憾的一个补偿。
这是《是时候了》作为优秀诗歌的正面形象,首次在庄严的正式出版物刊出,为此,我们为它特别写了一篇注释:“《是时候了》是北京大学第一张诗体大字报,写于1957年5月19日。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该诗张贴后反响甚大,两位作者随即均被错划为‘右派’。《是时候了》也被当作‘反面教材’广为转载和批判。《中国百名大右派》(张杉尔著,朝华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和《反右派始末》(叶永烈著,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征引了该诗。”
在北大,诗曾经唤起新一代献身建设新生活的热情,诗是和自由思想、理想情怀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年代的青年,以心灵的创伤,乃至身陷囹圄,以至血泪为代价,谱写了一曲悲怆的乐章。我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亲历者,我以自己的谨慎和怯懦而躲过了这番劫难。但我一直没有忘记那些走在思想解放前列的时代先驱者的敏锐和锋芒。那些受难的灵魂一直照亮我的内心,我不能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