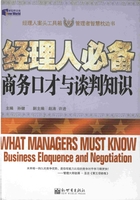火车经过格林威治,暴风席卷着雪花,落在车窗上。他们经过格林农场和西港,路过小而脏的工业城镇。雪越下越大,列车不得不暂时停靠在小站,等待暴风雪过去。陌生人开始互相交谈。此刻,就是圣诞节。
凯莉点了一支烟。她的脑海中全是圣巴茨岛。她想象着那个男人,还有杰森·莫徳和他女朋友(管她是谁呢),三个人躺在别墅的游泳池边,头顶就是湛蓝的天空。杰森·莫徳的女朋友会穿着白色的比基尼,戴着黑色的遮阳帽,用吸管啜着饮料。午餐的时候,人们都陆续来了,每个人都身材修长,面容姣好,肤色是很美的小麦色。
雪花从车门的裂缝里飘进来,凯莉打了个哆嗦。她默然地想,是不是这辈子永远都不可能做对任何事情。
午夜时分,斯基普正在家里,给加州那边打着长途电话。他站在窗前,看到一辆出租车驶过来,停在街对面。他能清楚地看到车后座的一对情侣在卿卿我我。之后那个女人下了车,身上穿着一件厚重的毛皮大衣,连头颈也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穿了十二件羊毛衫一样臃肿——是萨曼莎·琼斯。
两分钟后,斯基普家的门铃响了。
“萨曼莎,”斯基普说,“我正等着你呢!”
“拜托,斯基普,别这么幼稚,我是来借洗发水的。”她说。
“洗发水?先来喝一杯吧!”斯基普问。
“一小杯。”萨曼莎说,“别跟我耍花招,别放什么摇头丸之类的。”
“摇头丸?我从不嗑药,我连可卡因都不碰。我的天啊,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会出现在我的家里。”
“我也觉得难以置信。”萨曼莎说。她在客厅里溜达着,东摸摸、西看看。“你知道的,虽然别人都觉得我很有条理,但其实我挺‘随性’的。”
“你为什么不先把外套脱了呢?”斯基普说,“坐下吧。你想上床吗?”
“我真的很想洗洗头发。”萨曼莎说。
“你可以在这儿洗啊,”斯基普说,“上床之后。”
“我不想。”
“在出租车里亲你的那个男人是谁?”斯基普问。
“一个我对他没兴趣或者要不到的男人,”萨曼莎说,“就像你一样。”
“但你可以要我啊,”斯基普说,“我单身呢。”
“是,你当然‘单身’了。”萨曼莎笑了笑。
你真调皮
“切瑞,”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我真高兴你来看我。”
“你知道的,我一直想来看看你。”波恩说。
“过来,我有礼物送给你。”
波恩在富丽堂皇的前厅照了照镜子,然后走进客厅。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沙发上,喝着茶,腿抵着咖啡桌,脚上穿着意大利拖鞋。
“来这边,让我看看你,看看你这两个月有没有变老。上次我们去爱琴海,没有把你晒伤吧?”
“你可是一点儿都没老,”波恩说,“看起来永远这么年轻。有什么秘诀吗?”
“秘诀就是你上次给我的面霜,”那个男人说,“什么牌子来着?”
“契尔氏。”波恩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帮我再带几瓶吧。”男人说,“那块表还在吗?”
“表?”波恩说,“哦,我送给一个流浪汉了。他一直在问我时间,所以我觉得他比我更需要它。”
“呵,你可真调皮,”那个男人说,“老跟我开这种玩笑。”
“我有把你送我的东西给过别人吗?”
“没有。”那个男人说,“来看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开司米外套,每个颜色一件。要不要试试?”
“好啊,每一件我都要。”波恩说。
立瓦的派对
立瓦·维尔德家一年一度的圣诞派对总是热闹非凡,音乐放得震天响,到处都是人。嗑药的,在楼梯里不知道干些什么的,瞄准楼下的警察从阳台往下撒尿的……斯坦福带着一对刚来纽约的双胞胎男模过来了;波恩也在,但对斯坦福·布拉奇却视而不见;斯基普正和一个女人在角落里调情;圣诞树早就不知道被谁弄倒了。
斯基普好不容易抽了身,走过来跟凯莉打招呼。凯莉揶揄他,问他为什么老想亲吻女人。“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啊。”斯基普说,然后转头问比格先生,“难道你不觉得我的进展很神速吗?”
斯基普又跑到立瓦身边。“你怎么最近都不找我了?好像所有的朋友都在笑话我。是因为麦克吗,是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我?”
“你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没人会喜欢你。” 立瓦说。紧接着洗手间里传来呕吐的声音。
凌晨一点,聚会一片狼藉。地板就像是被酒精洗过一遍似的;一群瘾君子霸占洗手间不出来;圣诞树倒了三次了;大家都找不到自己的外套了。
斯坦福对立瓦说:“我终于放弃波恩了。我以前从来没有看错过人,但没准他真的是个异性恋。” 立瓦茫然地看着斯坦福。
“嘿,过来!”斯坦福突然又开心起来,叫着立瓦,“过来看看你的圣诞树成什么样子了。哈哈,可真漂亮!”
第一章 交际女王的性爱与悲哀:他很有钱,很爱我,也很……丑
凯莉走出波道芙购物中心的时候碰到了伯妮·恩特斯威尔。
“亲爱的!”伯妮叫道,“我好多年没见到你了。你看起来气色真好!”
“你也是啊。”凯莉说。
“你得陪我一起吃午饭,现在就去!我刚被艾玛丽塔放鸽子了。对了,她也在城里呢,我们还是朋友。”
“估计她在等杰克的电话吧。”
“啊,她还跟他在一块儿啊?”伯妮拂了一下头发,说,“我在二十一号餐厅预订了位子。拜托,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吃饭,我都一年没回纽约了,我们得好好聊聊。”
伯妮很漂亮,一点儿都看不出已经四十多岁了。黑色貂皮外套衬着她浅金色的长发,肤色在洛杉矶的海边被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她最近在演电视剧,但之前她可是纽约远近闻名的交际花,就是夜店里玩得最疯的那种姑娘。男人们觉得她太野了,没人想把她娶回家,但想跟她上床的男人却不计其数。
“我要后面的那桌,那边比较清静,我们可以抽抽烟、聊聊天。”伯妮说。刚一落座,伯妮就点了一支古巴雪茄。“赶紧跟我说说那个结婚启示的事,我迫不及待想听了。”她指的是克洛伊和杰森·金斯利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宣布结婚的事情。克洛伊三十六岁,依然是个倾城美女;而她嫁的男人却是个相貌平平的普通人。
“呃,杰森很聪明,人很好,家境也不错,”凯莉说,“他对我一直很友善。”
“拜托,亲爱的。”伯妮说,“像金斯利那样的男人可不是适合结婚的类型。纽约有好多这种男人,对你很好、关心你,你需要人帮忙的时候他会立刻出现在你的身边,这也就算是个不错的朋友了。当你晚上孤孤单单一个人难过的时候,你可以安慰自己说,至少还有一个像金斯利这样的人可以当备胎,嫁给他至少不用担心房租了。但问题是你仔细想一下,你真能忍受晚上跟他睡一张床,早上看着他刷牙吗?”
“桑德拉说他有一次想亲她,”凯莉说,“她跟他说:‘我要是真的那么需要人陪的话,我会养只猫或者买个抱枕。’”
伯妮突然打开她的粉饼盒,假装看她的眼妆有没有花,但凯莉觉得她是在看男人有没有注意到她。“我想直接给克洛伊打电话问问她,但不行,她已经好几年没和我说话了。”伯妮说,“奇怪的是,上东区那些博物馆的慈善活动最近一个都没邀请我——我敢打包票是因为克洛伊成了主席。我好几年没去那些晚宴了,大不了交三百五十美元自己去一次好了。我就想看看她现在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了!”
伯妮哈哈大笑着,好几个人转过头看她。“几年前,我人生最低谷的那阵子,生活简直是一团糟,有时候脸上还带着可卡因粉末就出门了。我爸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家,我问他为什么。‘你回家我就能看见你了,’我爸说,‘我只有见到你才能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所以我想见克洛伊。我一见到她就能知道她过得怎么样。她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啊?很厌恶自己?她是不是开始吃百忧解了?”
“没有吧。”凯莉终于说了句话。
“那她是被什么宗教给洗礼了?精神力量之类的?”伯妮追问着,“最近好像好多人都在干这个,很时髦。”
“我之所以想知道这个,是有我自己的原因的。几年前,我差点就嫁了一个像金斯利那样的男人,”伯妮缓缓地说,“那件事到现在都没解决。也许永远都解决不了吧。”
“服务生,给我们开瓶香槟。”伯妮打了个响指召唤侍者。她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那个时候我刚和一个恶心的男人分手。那人叫多米尼克,是个意大利的银行家。他跟他妈一样蛇蝎心肠,典型的欧洲垃圾,但他自己还挺得意的。他那会儿对我一点儿也不好,但我当时居然一点儿也不介意,全都忍了。当然,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牙买加喝迷幻茶喝多了,才醒悟过来他其实根本不爱我。但那都是后话了。在那之前我完全就是另一个人——在缅因州的小镇长大,长得挺标志,还算有教养,一天到晚都有陌生人跟我搭讪。但其实我挺坏的,内心挺冷的。我对谁都没有感情,也从来没真的爱过谁。
“可我还是和多米尼克同居了三年。一个原因是他和我约会的第一天就这么提出来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公寓很高级,打开窗子就是东河,他还在东汉普顿有一栋大别墅。我当时既没钱又没工作,平时只能靠给电视广告配音、唱歌之类的杂事过活。
“后来我终于跟他分了——我跟其他人偷情被他发现了,他还非让我把他给我买的那些珠宝都还给他。所以我当时就想,我得马上找个人结婚,越快越好。”
软毡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