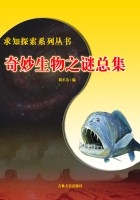乔纪年赶到太医院,写了退热的方子让其他的太医帮忙熬药,自己拿了腰牌匆匆赶往宫外。
十一阿哥府,博果尔看着密函,上面是南明的近况。
“十一爷,乔太医求见。”
博果尔听着这姓氏觉得陌生,太医来做什么?他把密函放在红木抽屉的最底下,然后起身相迎。
“十一阿哥,您快跟微臣进宫吧。”乔纪年一见到博果尔,不顾礼数,拽着他就要往出走。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博果尔一愣,连忙问道:“宫里可是出什么事儿了?”可就算是出事,也不该让个太医来通知啊。
“佟妃娘娘高烧不退,梦里一直喊着您的名字,汤药也灌不进去。微臣想,解铃还须系铃人。”
莲儿高烧不退?且在梦中念着自己的名字?仅仅这样一句话,他便不需要多想什么了:“小安子,更衣,入宫。”
乔纪年听见这话,方才松了一口气。“那微臣便先告辞了,太医院里,给佟妃娘娘的药还熬着呢。”
“多谢。”博果尔轻轻说了一句,乔纪年并没有说受之不起,因为此刻,他们不过是在共同担心一个女子,君臣之别,无需记在心上。
博果尔换了朝服入宫,进门时侍卫的眼神都奇奇怪怪的,估摸是猜测许久不露面的十一爷怎地想起回宫了?
博果尔直奔着坤宁宫的方向去,这既不是清晨也不是节日,说是进宫拜见太后固然不好,倒不如说去见过皇后,前些日子自己因讨厌烦乱抱病未参加立后大典,如今补上,岂不是正好。不过他不知道,这一点,他跟乔纪年想到一块去了。
博果尔走到御花园的假山后面,让小安子将包袱里的太监服取出来,还有小安子的腰牌也一并要了来,并且让他跪在此地,说如若有人问起,就说是得罪了大总管,罚跪在这儿的。
小安子点头称是,催促博果尔快走。
咸福宫的路,他很熟悉,几个月前听闻莲依被封为庶妃,他早已悄悄从阿哥所走到这里无数遍。他想不通那时候的自己是在祈求什么,也想不通现在的自己到底是放下了什么,可走入咸福宫内殿,看到床上烧的浑身发红的人儿,心底却已然隐隐作痛。
“你们先下去,守好门,若是乔太医端了药来,抓紧送进来。”博果尔示意流苏和花雏下去守门道。
“是。”
“莲儿,你怎么把自己折腾成这个样子。”博果尔抓起莲依的手,轻轻握在自己的手心,他把自己的体温带给她,想要让她安稳。
她的唇干裂的不成样子,已经暴皮,博果尔便俯身下去,轻轻舔着她的唇,可就在这一刻,他看到她略微敞开的中衣里面,有青紫的吻痕,顿时愣住。
他的唇离开的那一刻,她使劲儿睁开眼,沙哑到让人几乎听不清字句的嗓音说着一句话:“博果尔,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博果尔很想转身离开,可他站起身那一刻,脚步却挪不开,终究舍不得,闭着眼询问她:“要不要喝水?”
“嗯。”那细小如蚊的声音使博果尔不敢多想,起步去桌上倒了一杯茶,然后坐到床边揽住莲依,让她靠着自己坐起来,将茶杯放在她唇边,看她一点一点喝下去。
“立后大典你没有来,你得的病重吗?”看见博果尔真的在自己面前,莲依笑着伸手去摸博果尔的脸,可手举到半截,就因没有力气而垂落下来。
博果尔握住她的手道:“哪有你严重呢,倒是你,端午离现在才多久,就把自己折腾成这个样子。皇兄,怎么那么不懂得怜香惜玉。”一看那些青紫博果尔就来气。
哪知,听见他的后半句话,莲依却“哧哧”地笑了,“我是谁?”
博果尔没明白她的意思,于是回答:“莲儿啊。”
“对啊,我是莲儿,只是你的莲儿啊。”博果尔听见这话心里一痛,再次吻上她的唇,这一次是那么深入,他不要放过她,他要用自己的舌告诉她,她只是他的莲儿。
“咳咳。”门口有咳嗽声,莲依连忙推开博果尔,那本已是潮红的脸蛋上,如今又添了一抹艳色。
“主子,药熬好了,让十一爷喂您喝下去吧。”流苏端着药碗走进来,见主子气色已经好了许多,便知道这次的药方子是开对了,于是将药碗递了上去。
“不必了,本宫自己能喝。”莲依欲抢过碗,却被博果尔抢先一步,博果尔用勺子盛了汤药,放在唇边轻轻吹着,待到凉了,才放入莲依口中。
莲依觉得,从未喝过这般甜的中药。
一碗药喂完,博果尔将莲依脸上的碎发拨了拨,轻轻说:“我得赶紧走了,不然被发现就糟糕了。你要乖乖养好身体,不然如何做我的莲儿?”
这句话说的莲依眉开眼笑,一个劲儿点头:“你要小心。”
望着博果尔的背影,莲依觉得他穿太监服都这么帅,果然是好模子。
博果尔前脚刚走,后脚咸福宫就来了客人:“宁悫妃驾到。”
她来做什么?莲依刚刚绽开的心突然一紧,博果尔出去没被瞧到吧,宁悫氏可是宫里的老人,遇见博果尔是定然能认出来的。
“听说妹妹病重,姐姐甚是担忧,特来看看。”
“生病时晦气重,娘娘还是离远点的好。”
“妹妹这话说的就外道了,昨儿个刚侍了寝,如今便是自家姐妹了。今晨钟粹宫着火的事儿,不知道妹妹听说了没有?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莲依愣在床上,好半天重复道:“你说,是静妃的钟粹宫?”
“是呀,静妃的钟粹宫。”宁悫氏还没懂莲依怎么变了脸色,忽然想起今天早晨在坤宁宫,皇后提了一句,三阿哥送至静妃抚养,难道
“流苏,快帮本宫换衣服,去钟粹宫看看。”莲依跳下床,腿一软,还是被宁悫氏扶住的。
“妹妹莫急,定然没大事的,不然宫里早传消息了。”宁悫氏安慰道,心中也埋怨自己非跑来多这个嘴做什么。
“我不放心。”
流苏也阻拦道:“主子,您病成这个样子还去哪儿啊,再传染了小阿哥怎么办?”
“也是,不能传染了灼儿的。”莲依强忍着冲动,又坐了回去,眼神迷离的跟宁悫氏说话:“让姐姐见笑了。”
“哪儿的话,罢了,我也不再这儿扰你清净了,好好养病。”宁悫氏笑着拍拍她的肩,看这丫头没什么心计呢,怕是活不长远。
说来也怪,莲依这场病来的快,去的也快。喝了两幅药,第二日竟然好了大半,一清早虚着身子就让流苏伺候着换了衣裳上了妆,去了坤宁宫,说是怕皇后娘娘怪罪。可实际谁心里都明镜似的,她就想看见静妃,问问灼儿的状况。
“佟妃正得圣宠,这病好的也比常人快三分啊。”皇后见到莲依,没什么好气儿,且不算旧账,当初静妃为后的时候,皇上还连去了三夜呢,怎么到她这儿,坤宁宫才留了一夜,便招了这个?
皇后这一起话头,众嫔妃又开始议论不休,以至于让莲依认为每日的坤宁宫请安,不过是这群后宫女人过于无聊,凑在一起八卦的时间。自打进这屋子,静妃就没看她一眼,似是故意躲避着一般。
“静妃娘娘,听闻昨夜钟粹宫起火,不知您可伤着?”可算出了坤宁宫,莲依紧跑慢跑着拦住静妃。
“不曾,三阿哥也不曾伤到。”静妃淡淡地说,全然没有了当日在咸福宫耀武扬威的样子。
“要不是咱家主子冒死冲进火场救了三阿哥,三阿哥指定没命了。”静妃身边的侍女大声嚷嚷。
听见这句话,静妃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神色,莲依看着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好好的宫殿,说起火就能起火,且就在三阿哥送去的第二天,这是不是太过巧合了点?静妃娘娘是三阿哥的养母,拼死相救理所应当。三阿哥乃皇嗣,真出了事儿,你们,谁能活命?”虽说莲依是指着那侍女说的,可这话明明白白就是说给静妃听的。
“你好大的胆子,怎敢跟我家娘娘这样说话。”侍女好个不乐意。
“你胆子也不小,敢跟本宫这样说话。流苏,掌嘴。”莲依一点不客气,就仗着皇上近日宠我如何?怕尔等记恨不曾?她就不相信因此静妃敢虐待三阿哥分毫,那也是静妃的靠山。
流苏应了一声,走上前扇了那侍女一巴掌,力道说轻不轻,说重不重,恰好让她脸上通红。
“够了,穗儿,咱们走吧。”静妃率先转过身去。
“娘娘,您今儿个怎么?”侍女似是不可置信,这样的话怎能从自家娘娘嘴里说出来?
“走。”静妃没再多说话,她只要想办法让佟妃,不再升上品级就好了。
莲依此刻的心是不安的,是焦虑的,如她身上那袍子花纹,紫不紫,红不红,乱的很。“流苏,我入宫的那一夜就知道,这辈子的漫漫无休,没有尽头。”
内务府刚分了夏季的料子来,流苏跟花雏正在整理,听见莲依的话,愣了一下,没听懂。
“我以前总觉得皇上多情,其实他比咱们难,他得让天下人都心平气和,他做不到,谁都不记他的好。”
“主子别总说那些扰人烦闷的事儿了,您看看,这湖蓝色的料子,上面带着莲花,美得紧。”花雏抱过其中一匹料子,欣喜若狂的模样。莲依抬眼一瞧,是挺好看的,说是素雅有不准确,那莲花的纹儿怎么瞧着还有点魅劲儿?
“收着吧,什么时候想起有用了,再做。”
莺哥一清早就换好了大喜的吉服,描了最黑的眉,点了最艳的胭脂,涂了最红的唇。太美,美到以至于不忍在镜子前挪动步子。她的肤质本就白皙如玉,她的伤痕皆在看不见的地方,例如背上,例如心底。
出乞祥宫的时候,她看到了一顶雕花的木轿,她的行礼里除了赏赐的几身新衣裳外,只有一只丑陋的木簪子,那是当初乔纪年亲手做的,她看到,抢了去。
如今,竟成了唯一的念想了。
她入轿,她是新嫁娘,她才有资格在这紫禁城内,穿最高的主子才能穿的正红,可她耳边没听到一声祝福,哪怕是奴才的。
皇上没有来送,太后没有来送,皇后与后妃都没有来送,哦,也许她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宫里还有个格格,今日出嫁。
也罢,就是命了,日后,惆怅对清风,淡漠于孤月,流泪时许是还有花儿怜。
此前,莺哥想过无数次出嫁的场景,她着那华丽的袍,面上是不点胭脂也惹了的红霞,她的出嫁会成为宫内的一桩喜事,有唢呐声声,有宫娥起舞,有皇兄赐宴还有外臣来贺。她只需安安稳稳的做个最美的新娘,一端红绸交到手心,她扭头便可看到红绸的那一端是她心心念念的意中人,然后他们一起在皇上的作证下跪拜,结为百年同好
可到底,那只是个美好到虚幻的梦。
她不曾见过未来夫君一面,除了陌生的名字外一无所知,可是她却要去陪伴一辈子。
亦或者,是去服侍一辈子。
她以为此刻有泪要涌出来,深手欲去擦,才发现眼睛干涩,根本流不出什么液体来。
轿子颠颠簸簸不知道走了多久,出了宫门就会换马车了吧,她早上还没吃饭,肚子饿得很。
“臣乔纪年叩见固山格格,格格千岁千岁千千岁。”
这请安的声音像是惊雷,把莺哥从里到外震了个透彻,她一定是太饿了,心里太急了,竟然出了这等幻觉。
“皇上说了,他这个做皇兄的没什么别的贺礼,便让乔太医与您见上一面吧。奴才的话带到了,格格啊,您也就抓紧功夫,叙叙旧吧。”唐吉顺说完这话,看了一眼那轿子,转身离开。
莺哥掀开帘子,走了下去,她定定的望着眼前的人,她看不到一点思念,看不到一点焦虑,甚至因为乔纪年太过顾及礼数,略垂着眼帘,她都在他的瞳孔中,找不到自己的影子。
“臣奉皇上之命,特来送格格一程。”乔纪年的声音那么淡,只是开口,莺哥就知道他多么想把自己拒之千里之外。
“送过了,回去吧。”莺哥轻轻咬着下唇,好半天道。
“格格出嫁,臣特意备了一份贺礼,虽微薄,聊表寸心。”乔纪年也不看莺哥,而是从身上的荷包内取出一个油纸包来,递给过去。
莺哥接过,打开来看,是晶莹的薄荷糕,转眼似是回到几年前,她常常中午饿着肚子,下午跑去太医院,缠着乔纪年做薄荷糕给她吃。
她轻笑了一下,将糕点掰了一块放入口中,闭上眼细致的品着,如同这便是她今日的全部任务,直到口中再无糕点,她才睁眼轻轻说:“乔太医,你的心意,我收下了。出了这紫禁城的门,想必是再不会回来了,当年莺哥年幼无知犯的错,还望乔太医宽恕。”
她想,她放下了,在看到这薄荷糕的那一刻,她就知道这样执着的爱下去毫无意义,倒不如放下,好好走以后的路。
“格格言笑,臣怎会那般胸无肚量?”乔纪年也轻笑出声,抬头看这最美的红妆,他忽然觉得,当日缠人的小丫头,长大了。
“那便好。”说完这句话,莺哥转身走出了午门,那里有带她去准格尔的马车。她没有回头,她没有对乔纪年诉说她在冷宫中三年的苦,因为说出口,也改变不了什么。
“你要安好。”这一句,是乔纪年望着她鲜红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自己的视线,而在心里默默说出的。
要安好。
此生,怕是再无相逢的机会,这最后一面,许是化解了什么,由许是斩断了什么。
那一份曾经的执着,却是毫无瑕疵的大爱,可惜却因不逢时而化成了两人的大痛,受了伤,留了血,结了疤。
还好,莺哥决定,让那疤痕重见天日,让那毒液流出体外,让自己有颗完好的心,去面对下一个人。
莺哥坐上马车,看着唯一的随侍嬷嬷也爬上来,她将手中的油纸包也递给她,笑着说:“嬷嬷,尝尝吧,不错的手艺。”
她莺哥,似乎本就该是那最动人,最自在的鸟儿呢。
这一夜,顺治召了布三珠格格侍寝(此处格格指皇家的小妾,在康熙以后,后妃制度得以完善,才去除这些称呼,顺治期间,还在沿用)。
待福临睡去,布三珠静静地躺在龙榻上,这是她今生的第一次躺在龙榻上,也许是最后的一次了。如果能怀上一个龙种该有多好?可这样的希望,太过渺茫。再过一个时辰,自己又要如同货物一样,被被子卷着带回自己的寝殿,而这龙榻,此生再与自己无缘。
身侧的男人,注定是自己的主子,而不是自己的夫。
想到这儿,她的眼神再也明亮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