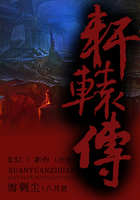“我放不得他。”他平静开口,凝着她的后背,连她最细微的颤抖都入尽眼中,他很心疼。
“我知道。”声音都带着哭音。
他上前一步,进来前早已秉退了身边人,在她身边单膝跪下,认真道:“缘儿,我向你保证,念在他救过你,往后我自会放他一命。”这已是他退步的极限,想起那五年,皇甫少恒藏起他的女人,他就恨得牙痒痒。
“可不可以不要伤到他?”她恳求,眼中带着泪,可怜的就像只只受了伤的小鹿,眼睛中盈着波动的水光,让人一见生怜,“不要伤害他,好不好,我答应你留下来,不在想着离开,只求你不要伤害他。”她在三企求只为另一个男人求情,皇甫少卿强忍着心中的那团快喷出的怒气点头。
其实,他的保证,她根本不相信。
返回江夏的前一天,她借病拖延到皇甫少卿来水榭殿。
“怎么无缘无故就病了?”他坐到她身边,手不由自主的摸上她的额头,是有些发烫,“传御医了吗?”
“回万岁,传了。”马德顺跪在那回道,“御医说娘娘是心中郁结所致。”
“郁结?”皇甫少卿仰头望着上方片刻,郁结么?他在心里苦笑,郁结的病症在皇甫少恒么?竟然已经思念到如此地步了。
“皇甫少卿,我觉得你以后会要了我的命。”她在软榻上趴着,喃喃自语般问他。
他眼中凝重着一股情绪,却无法发泄出来,“你说什么?”
“我说,以后你可能会要了我的命。”她得向他讨一个免死金牌,郭太后曾经给过他们一块,可是金牌大概已经毁在了恒王府的那场大火中了,所以她必须在要一块,然后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把金牌送到南宁。
“不会。”他的话平静而坚决。
“会的,记得在我失忆的时候,我听说梅希兰曾经有过你的孩子,可是最后没了,我不知道传闻是不是真的,可是我也是女人,我不想像她一样。”她伸出了手摊在她面前,“我已经几翻对你不敬了,我不知道你何时到了极限就会将我如你其他女人那样对待,或者推我出去砍了,你能给我一个保障吗?”
“别说胡话!”他几乎是想也不想的就打断了她的胡思乱想,“缘儿,你是我的发妻。”
“算个屁!”发妻,梅希兰与你情谊浅么?最后呢,还不是独首青灯。
“算朕求你了,不要在这样了好吗?”她总是喜欢变着话的噎他,让他很不舒服,他说过专宠就一定会做到,所以她还担心什么,况且他怎么可能伤她,为了她,他甚至可以放皇甫少恒一命,她还要他怎么做呢?说出来,他便去做。
“给我一个免死金牌吧。”她笑着提出,摊出了手也适时的收缩着,“给吗?”
“你要那东西做什么?”
“不舍得?”
他闭上眼睛,真的猜不透这女人想干什么了,为了让自己不那么累,最后他还是让马德顺端来一块金牌,金牌在她手上时,她专注的神情让他心中隐隐作痛,又是为了皇甫少恒吧。
一日后,返回江夏的途中,皇甫少卿与她同乘一辆马车,皇甫承与皇甫熙带着嘉宝与皇甫澈,头天皇甫少逸就带着他的王妃赶回了江夏没,说是国师已到逸王府,赶着回去见老丈人,皇甫少锦随队,人不多,沿路有暗卫保护。
车撵中。
“我想过了,嘉宝是长公主,就用祖宗族谱中的福字为她封号。”福,皇甫家从打下江山开国至今,族谱中最为尊贵的一个字,当年也就开国皇帝的嫡亲姐姐被封为福姬长公主。
“福柔如何?”
她只低恩了一声,然后身体也软软的趴在了身边的软枕上,她真的好累,每次跟他独处时就觉得累,也觉得跟他已经没什么话可说了,可他却好象浑然不觉她的态度。
现在的他,其实也是知道她的态度,他料到了她的态度会如此,所以很多时间他不逼她对自己的话和一些行为做出回应,只要她在身边,听着,就算不回答,他说就好,他就觉得很安心,他的女人,不管变成什么样子,心里有谁,还是他皇甫少卿的女人,他就有时间去找回她。
“你不觉得累么?陛下。”
他自然知道她话的嘲笑之意,只默默的低着头,将那席绒毯盖在了她身上,如果她喜欢这样嘲笑自己让自己舒服,他无所谓,虽然心里难受,“是我不好。”他还能说什么呢?
她早已不去在他身上期待什么了,所以她不会在痛,可是他眼中失落,痛苦还是在刺痛自己的心。
毕竟,她曾经那么爱眼前的这个男人。
车外,却突闻侍卫的声音,“有刺客,保护陛下!”
撵中,皇甫少卿将她拉进自己怀中,护着,眉头皱着,单依缘也就那么随他去了,没什么好挣扎的了,可是却听见撵外皇甫承的声音传来。
“二皇叔,你还真来了。”
“太子殿下将大婚的消息传到南宁,不就是为了今天。”皇甫少恒熟悉的声音传进她耳中,单依缘蹭的从他怀中挣脱出来,皇甫少卿欲抓回她的手横在中途,她早已跳下了车撵。
“错!本殿不是为今天,为的可是二皇叔你。”皇甫承仰头一笑,继续道:“没想到,皇叔果然来了。”
“少恒!”
她是身后男人永远不能遗忘的爱念,亦是眼前男人万丈光芒中残缺的一块,可今日她却只能为一个痛,她挣脱开一切束缚,义无返顾的奔向了皇甫少恒,甚至选择性的无视掉身后哀怨的挽留:“缘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