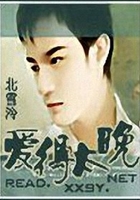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各种色调充满天地间:有蓝色、绿色以及金色。
走过混凝土坪之后,他们穿过门卫来到距离点火处不是很远的地方。有一根接着发射场的特大的电缆。之后,他们走到那巨大的石灰岩悬崖边稍做停留,眺望着英伦三岛的美丽风貌,据说凯撒就是2000年前首次在这里登陆的。
一块一望无际的绿草坪在他们左边一直延伸到沃尔默和迪尔海滩,朝着桑威奇与巴伊海湾的方向婉蜒而去,草坪上数不尽的小野花迎风摇摆。薄薄的白色轻雾从那边的拉姆斯盖特的悬岩顶上升起,将北福尔兰遮住,将曼斯顿灰色山岩旁的飞机场保护起来。美式雷公式喷气机在机场的上空拖出一长串白色的烟雾。萨尼特岛的伊勒依稀可见,泰晤士河河口则一点也看不见。
还尚未涨潮。到了涨潮的时间,南古德温海湾金光灿灿,恬然静谧,仅仅只有一少部分船只在波光粼粼的蓝色航线上来回穿梭。一顶顶桅杆撑起在船上,仿佛是在述说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样。白色字母在南古德温灯船上隐约可见,甚至带色字母也在北边的姊妹船的红色船壳上模模糊糊地显示出来。
内里兹湾就在沙底和海岸之间72英尺深的海湾里,有几只船正从唐斯摇摇晃晃地飘过,在平静的海面上,一阵阵砰砰的声音从发动机里发出来。遥望远处,挂有各国不同颜色旗帜的船只来来回回往返穿梭,油轮,商船,以及笨拙的荷兰军舰,还有几艘很可能是去朴次茅斯的精巧的护卫舰向南匆忙驶去。英国东海岸也在视线之内,穿梭往来的船只或者驶向近岸,或者驶向远处的地平线。它们或者驶回到最初的停泊处,或向世界的另一边驶去。这是一幅绮丽的风景画,里面充满了不同的色彩和浪漫的情调。邦德和加娜·布兰德站在悬岩边静静地欣赏着这令人陶醉的景色。
两声警报从大房子里发出来打破了眼前的宁静,重新把他们拉回到那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的混凝土的世界里。从发射场的圆盖上伸出了一面颜色鲜艳的红色旗帜,只见有两辆气派的皇家空军的运输车从林子中开出来,红色的十字在车身上画得非常显眼,那两辆车靠着缓冲墙边慢慢停下来。
“已经开始添加燃料了,咱们还是离开这里吧。假如有什么意外发生的话,这里是非常危险的,甚至会丧命。”邦德说。
“的确,”她微微冲他笑了笑,“每当看到那混凝土我就会头疼。”他们从那缓坡慢悠悠地走下来,很快就过了点火处,他们的身影消失在铁网之外。
加娜·布兰德一直以来所保持的冷漠在灿烂的阳光下很快就溶化了。
她身上穿着令她更显漂亮迷人的地道的外国货。上身是一件黑白条纹的棉衬衫,下身配了一条粉红色的裙子,另外,腰间还扎了一条黑色的宽皮带,显得格外活泼可爱。她如此的穿着打扮,突然让邦德觉得在自己身边漫步的姑娘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面无表情的冷面女人。她愉快地嘲笑邦德,原因是他甚至叫不出来诸如海篷子、牛舌草之类的野花的名字。
加娜·布兰德在路边惊奇地看见一枝漂亮的红门兰,兴高采烈地摘下来放在鼻子前闻了闻。
“假如你能够了解到在你采它的时候,它呻吟得多么痛苦,恐怕你以后就再也不会那样做了。”邦德说。
加娜·布兰德奇怪地看着他问:“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认为这句话不是在和她开玩笑。
“难道你真的没听说过吗?” 邦德看到她那一脸严肃的认真模样,忍不住笑出来。“有个印度教授写了一篇论文,那是一篇有关花卉神经系统的论文。他将一枝玫瑰被折时的痛苦呻吟声详详细细地记载了下来,那声音听起来真是痛苦不堪。我在刚才你折花时似乎也听见了那种凄惨的声音。”
“我不相信,”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怀疑的眼光望着手里被折的花枝,“但是,我认为你并非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像你们这些秘密情报局的人不都是经常杀人的吗?我说的不是折花,而是杀人。”她恶狠狠地还击他。
“但是要知道,可怜的花是不懂得还击的。”邦德说。
她瞧了瞧手里拿着的红门兰,“你的话让我认为自己是个凶手。但是假使我能够找到你所说的那位教授,并证明你所说的话全部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以后就再也不会折花。那么我手里的这朵花该怎么处理呢?我觉得似乎我的双手已经鲜血淋漓了。”
“那就把它交给我吧。假如按照你的逻辑来推理的话,那么我的手早就已经应该算得上是血淋淋的了,即使再多一点也没有多大关系。”
她把那朵花递了过去,两人的手轻轻地碰在一起。“你可以将这支花插在你的枪口上。”
邦德笑了,“枪眼根本不需要用什么东西来装饰。我那支手枪是自动式的。我已经把它留在房间里了。”
他在蓝色衬衣的扣眼里插进那支花后说道,“我认为仅仅只挂着肩式手枪套而不穿外套的话太过于显眼,希望下午不会有人到我房间里去搜寻什么。”
两人各自把手默契地抽了回来。邦德把早上发生的事情跟加娜·布兰德说了一遍。
“是该教训教训他,我对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好印象。雨果爵士有没有说什么?”
“我在午饭前和他谈了几句,并且作为证据我拿出克雷布斯的刀和钥匙交给他。他听后暴跳如雷,带着满腔怒气去找克雷布斯了。他回来时说克雷布斯伤得比较严重,似乎再对他加重惩罚有点太不合时宜。还有就是他一直强调的那句在现在这种关键时刻,不要搞得他手下的那些人惶恐不安等等。他对下星期将克雷布斯遣送回德国表示赞同。但是在此之前,不管他去哪里都要密切监视。”
当他们沿着蜿蜒盘旋而又陡峭的悬岩小道来到海滩时,再向右转,就能看见旁边那个迪尔皇家海军要塞已经废弃了的轻武器靶场。沿着覆盖有鹅卵石的海滩,他们走了差不多两英里,有好长一段时间,两个人都没有开口说话。之后,邦德先开了口,他将自己在这一天所想过的一切全部都说给了布兰德,最后总结起来,依然还是那个陈旧而又根本的问题:到底“探月”号的安全措施是否已经万无一失了?
泰伦与巴尔滋之死只能让他们看到这个问题的表面现象。克雷布斯的行为也不能算作是什么严重的问题,然而假如把这些问题串联在一起加以考虑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显得非同一般了。他对敌人是否在蓄意破坏“探月”号发射计划这个问题表示深深的怀疑。
“你觉得我的看法怎么样?”邦德问道。
加娜·布兰德不再继续前行,而是遥遥地望着那陡峭的岩石以及海边那些不断随海水来回波动的海草。刚刚从满是鹅卵石的海滩走过来,她已经热得满头大汗了。假如能够跳进大海舒舒服服地洗个澡该有多好啊!她瞥了一眼立在身旁的邦德。他褐色的脸上除了一脸严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表情。生活中恬然宁静的时刻,是否他也和常人一样地渴望呢?不,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他所喜欢的应该是那种由巴黎、柏林、纽约,以及火车、轮船、美味佳肴和漂亮的女人等等所组成的动荡生活。
“你怎么了?”邦德问道,还以为是她想起了什么细节,正在犹豫着是否需要告诉他。“你刚刚在想什么呢?”
“不好意思,”加娜·布兰德说,“我在胡思乱想。我认为你刚才的判断并没有错。我从基地竣工起就已经工作在这里了。虽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些诸如枪击之类的怪事,但幸好还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失误。雨果爵士那帮人全部都专心致志地把心思放在制造导弹上,他们甚至都能够达到忘我的地步。看到这种情况真是让人感到欣慰。那些德国人全部都是令人佩服的可怕的工作狂。我敢保证,巴尔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被压垮的。他们都非常愿意听从雨果爵士的使唤,而他又懂得应该怎样使唤他们。他们对他都非常地崇拜。就安全来说,这种崇拜的确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假如有谁想打‘探月’号的主意的话,那么他最终就得完蛋。至于说克雷布斯,我对你的看法表示同意。很有可能他是遵照德拉克斯的指令才那样去做的。因此我并没有向德拉克斯汇报关于他偷看我东西的事情。不过当然,他也不可能找到任何秘密,因为那不过都是些私人信件之类的东西。我想或许是由于雨果爵士要使基地绝对地放心吧。我在这一点上非常佩服他。但他是位冷面无情、不可理喻的人,我愿意为他工作,但愿‘探月’号的发射能够成功。同它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如同所有其他人一样,产生了一种息息相关的感觉。”她说完之后抬起头来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邦德点点头,“虽然我来到这里仅仅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我对于你现在的这种感觉也非常了解。你所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可能我的顾虑也不过是我的直觉而已。总之,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要保证‘探月’号如同皇冠上的珠宝一样安全,或者比这还要更安全些。”他耸了耸肩膀,似乎是要将他直觉中的不安全部抖落一样,“咱们已经花费掉很多时间了,还是赶紧走吧。”
她对他会意地笑了笑,跟着他走了。
他们共同来到悬岩的拐弯处,看到海面随波浮动的海草缠着升降机的底部。他们又继续前行了五十码左右。看见在这里有一副如同粗管状的铁架,上面是护着岩石的格子状铁条。排气隧道那又黑又粗的大孔从差不多有二十英尺的岩面上伸出来,已经被风化了的石灰岩掉落在下面的岩石以及圆卵石上。邦德似乎看到了那熊熊燃烧着的乳白色岩浆柱从岩面呼啸而下,沉入汹涌的大海,海水发出令人战栗的咆哮声和数不尽的气泡。
他把头抬起来遥望着发射舱,那发射舱比崖面高出二百多英尺,脑袋里情不自禁地想象着头戴防毒面罩、身上穿着石棉衣服的四个人,一面认认真真地观察着计量表,一面将输料管插进了导弹的肚子。
邦德猛然想到,加油这一环节若是有什么以外的话,他们这一带可得算是一个危险区。
“咱们还是立着远点吧。”他对加娜·布兰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