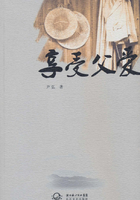姜成泽道:“脾气不像个人样,病也不是个人样,这个任师弟。”众人都忍不住笑。
自无情剑破封出世后,阴山南麓的沙漠慢慢地青绿起来,大片绿洲绵延,使得这里不再是商旅谈之色变的吃人之地,也使得中原塞外不再千里相隔,以至于天演教与翡月教成为毗邻。
中原与塞外的物品交易空前繁荣的同时,天演教某些资历老的坛主看着翡月教如此嚣张的开地扩土,如同骨鲠在喉,恨不得将翡月教再次打回塞外。然而混在芝芝药人里的三个坛主杳无音讯,加上中原混乱,自顾不暇,他们都不敢轻举妄动。
相比天演教,云氏家族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处在了无限惶恐中,尤其是老一辈的三个老古董。
是夜,任风侠悄悄地来到了云芳尘的故乡,他想来瞧一瞧她曾经住过的地方。
大半夜的,路上静悄悄的没有人,只有一个打更的老头子敲着梆子吆喝着:“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相比关外,中原此时正是气候宜人的深秋,打更的是个结实的小老头,大半夜的忽然见有人纵马追风逐电的穿过长街头,摇摇头叹道:“哎!这又是谁,大半夜的赶着投胎似的,黑灯瞎火不怕撞客着。”
话刚说完,眼前忽的冒出个人,打更的吓地一个趔趄,嘴里的烟袋都掉了,待看到昏黄灯笼下有条黑暗的影子,心里一稳,不是鬼就好!这才看向他的脸,不由得一怔,好一个清俊的小伙子,似乎还在哪里见过,年老容易忘事,他不由得皱眉思索,究竟在哪里见过他。
任风侠不容他多想,问道:“你知不知道云府的大小姐?”
打更的拍了拍胸口,皱眉道:“她早就死了啊,还好早就死了,要不也要给云家老祖宗给拖来烧死了。只是也不知道她造了什么孽,连坟墓都被人掘了,有关她的不堪传言近些日子才平息喱。”
任风侠脸色一白,一股怒火就涌了上来,他从来不知道他给她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扰,这么久了竟然还有人对她议论纷纷,说道:“那云家老祖宗在哪里住?”他一个男子再心细也不能十分明白那种舆论压力,何况他不是那么心细的。这是他第一次听见有人对云芳尘的闲言碎语,寥寥几句,然而那不屑的语气神态刺的人抓心挠肝。
打更的指了三个方向,说道:“大半夜的,都睡下了,你有什么事天亮去也不迟。”
任风侠没有回答就离去了。
那打更的琢磨了半天,却想到,眼前这人,眉目之间,依稀有点像靖南之妻段素素。顿时明白,原来,被称作败家恶灵的他没有死。
任风侠来到云府,他望着那大大的牌匾,心里一阵难受。
其实,这里也是他的生身之地,可是除了有个念念不忘的云芳尘,他对这里没有丝毫的好感。
而后,依着模糊的记忆,云家三个老头子被他从被窝里挖了出来,来到云氏宗祠,他一脚踹开了那沉重的大门,将三个人丢了进去。
一支支烛火亮起,每一支犹如催命的鬼火幽幽跳动,照的三个云老愤怒的面容有些扭曲狰狞,却依然一副固执正气凛然的样子。
云氏宗祠,怎能容一个外人涉足?可是这个人,不但涉足,还冷笑着站在那里,轻蔑地看着那一个个云氏祖宗牌位,偶尔伸手弹倒一个,或者丢到地上。
这个人就是任风侠。
灰衣云老忍不住大喝道:“你是哪里来的野小子?竟敢来沾染云家的宗祠?”
任风侠笑道:“死到临头还大呼小叫,活得不耐烦你马上去死,死了好进这个狗屁宗祠,叫你的后人跪拜千万年,怎么样?”
紫衣云老义正词严地道:“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对我们这些糟老头子动武,不怕传出去叫人笑话,你赶快解开我们的穴道。”
任风侠冷笑着,说道:“我怕人笑话?被人千里追杀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笑话二字怎么写。你们烧死那些无辜女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她们的感受?你们三个,当初又是谁想要火烧云芳尘?”
三个老头有两个衣衫不整,只有紫衣老者还因为有事没睡下,形象还好一点。
白衣云老蓦然明白眼前人是谁,大声道:“你这个灭门祸胎,当年靖南就该掐死你,你连自己的宗祠都入不了,竟然跑到这里来撒野,你是个好小子!竟然还勾搭上了云在兴的女儿,那不要脸的做出了丢人现眼的事,活该被烧”
“啪!”
一声闷响,白衣云老左脸被一个牌位打肿,一口所剩不多的牙顿时掉了个精光。
任风侠阴森森地说道:“你以为你是谁?可以随便辱骂她?”
三个老头被捧惯了,自以为摆个架子就能吓到所有人,哪里知道眼前的人是怎样的心狠手辣?更容不得有人骂云芳尘。
这一下震得三人终于露出不安之色。紫衣老者强自支撑着,说道:“是她错在先,火烧也是应该”
任风侠冷笑道:“如果那是你的孙女呢?”
紫衣老者怒道:“莲儿洁身自好,哪里是那卑贱女子比得的?”
任风侠神色更冷了,不是这三个老废物,他的云儿就不会被迫离乡背井,辗转千里受尽苦楚。
从今天起,每一个迫害过云芳尘的,他都要一个个的报复过去,也包括,他自己。
他一拍桌案,大片牌位倒落,夜色里,有三个女子被推进来,被几个无赖押着。这三个女子面色潮红,不住的扭动,要扑上身后的男人。
三个老人气得青筋爆出,差点吐血,这三个女子正是三人的孙女。
紫衣老者大喝道:“莲儿!你怎么了?”
莲儿一惊,看到威严的三个老者,顿时噤若寒蝉,却抵不住身子里一阵阵难受的涌动,说道:“我不知道”没多大一会儿,她忍不住抱住了一个无赖,无赖低低地调笑着她,她觉得屈辱,却控制不住自己。另外两个也不顾矜持的各自抱着一个男子乱扭。
任风侠一见也是满脸怒容,他可没叫他们给这些女子下药,隔空解开紫衣老者的穴道,还没说话,紫衣老者就冲上去抓住莲儿边骂边打了下去。看着老者扭曲的脸,任风侠有些不可思议,长居草原的熏陶使他理解不了紫衣老者的顽固。
草原苦寒,女子珍贵,没有从一而终的困扰,丈夫死了,也可以嫁给他人。他忽然就觉得老者可恶的要死,那是他的亲孙女,他却下得了如此重的手。
任风侠对着那几个无赖冷斥道:“滚!”几个人看了看三个女子,大半夜的被眼前这个人找来,挖来三个俏生生地女子,以为有什么好处,便自作主张地给这几个女子喂了点媚药。眼见到嘴的肥肉就这么飞了,他们有些不甘心。
任风侠是男人,一见便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拿起一个牌位就丢了过去,立即将一个无赖打得胳膊折断,痛得他杀猪似的叫了起来。
任风侠道:“再叫,我就让你没命叫。”
那个无赖惊地住嘴,连忙一起诺诺离去。
任风侠左手一引,一盏油灯便飞向紫衣云老。紫衣云老被油烫得跳脚大叫,再也顾不得打孙女。那灯火却已经着上了他的衣服,遇油烧的极快,老者立即就痛的要打滚扑灭,却发现自己忽然又动不了了。痛苦之下嚎叫着向孙女求救。莲儿就奋不顾身地去扑火。
任风侠隔在二人之间,说道:“她要活活打死你,你还救他?”
莲儿道:“是我不好,那是我祖父,我不能看着他死,求你不要杀他。”紫衣老者又哭又骂,形象全无,一听莲儿的话,立即就向任风侠求饶。平日里再道貌安然,他也惧怕死,以往都是他看着别人被烧死,哪里想到自己也有被烧死的一天?
任风侠看着莲儿,冷笑道:“无情无义的祖父,要他有什么用?”这时另外两个女子不顾一切的向他扑来,任风侠一阵厌恶,抬臂将二人推了出去,两个女子飞滚着撞倒墙上,一时头晕目眩,却并没有伤到,躺在地上昏昏而睡。
莲儿眼神焦急,却慢慢地又要失去焦距,似乎药力又要发作。任风侠一指点住她的昏睡穴,转身冷冷地看着紫衣老者,看着他痛苦扭曲的脸,心里不但没有报复的快感,还隐隐地难受起来。
他不过是个老人,很顽固的那种。他伸手一拍桌案,无数牌位飞起,呼啸着向紫衣老者飞来,牌位密密地紧紧地贴了他满身,火也被熄灭。
他又一指点在灰衣云老与白衣云老身上,内力透过,毁去了两人的嗓音。有生之年,二人将再也不能开口说话。
清晨,众人发现三位老人时,都惊骇地说不出话来。有人就来拿紫衣老者身上的牌位,紫衣老者发不出声音,痛得张大了嘴,扭曲着脸直摇头,很痛的样子。
后来延请大夫来看,却发现,牌位与紫衣老者已经血肉相连,无法拿下。而另两位老人自此再也说不出话,动也不动,除了眼睛会动叫人知道没死,已经形同废人了。
三个人只有紫衣老者还有意识,却是直到终老,都没再踏出过祠堂一步,他这幅样子也没有脸去见人,日日都是子孙送来吃食,奉养着他。
不久又有消息传来,靖家祠堂地上血迹斑斑,靖南夫妇的牌位不翼而飞。
而自那天后,靖家仅剩的一支忽然子孙旺盛,不复这些年的子息艰难。
人人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愚夫愚妇却最会穿凿附会,说是云家克了靖家,而今云家祠堂被毁,靖家自然就旺盛了。还说靖家祠堂地上的血能镇邪,能兴旺子孙。
始作俑者的任风侠已经背着双亲的牌位,回了翡月教,将二人供奉了起来。出生的当天二人便横死,以至于他根本不记得他们什么样子,可他还是对十月怀胎将他带到这个世上的夫妻存着怀念。如果他们活着,也会像师父那样疼自己吧?
由于他大闹云家祠堂,伤了人,犯了教规,自动的向松士阳那里领了责罚。
翡月教自开教以来,都是自给自足,对江湖中人可以快意恩仇,却绝不允许奸掳掠、欺凌弱小的事情发生。任风侠也是想到这一点,才留住老人的性命,也使得松士阳不至于太难做。而他知道,这样的活着,对他们三个老人来说,还不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