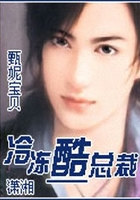“听起来挺不错呢,可是怎么说呢,我还是很难过呢。很难过。”
“我肯定会的第一的,那时音叙你一定要回来,我为你单独唱歌。”沈音叙艰难地说“好”然后与善晚分别。站在街头目光蜿蜒成一条线,跟随在她身后。车流喧嚣至及,他仿若置身于世界之外,那样安静而又宁和。许久,沈音叙慢慢埋下一张脸,泪水庞大地落在地上,没有人知道他心里的那一片波澜是如何潮涨潮落。
决赛当日以抽签形式排序,善晚是最后上场,她决定唱霎时写给她的那首歌。
冷锦是倒数第三个,一上场整个演播厅沸腾得欢呼声和口哨声此起彼伏,男生依旧不为所动,用食指抵住唇,霎时全世界就为之安静。
缱绻的慢情歌,配着漫天挥舞的荧光唱毕,他把话筒拿在手里还有话要说:“一直以来,我都想要感谢两个人,他们是纪善晚和沈音叙。”
是完全不曾预料的情节,台下顷刻便喧哗起来,所有的目光都转向错愕惊讶的善晚,她心中没有因为被人广受关注而惊喜,反而泛起不好的预感,为什么会提到音叙呢。
“善晚,有一件事我从没有告诉你,有一句话我也从没有对你诉说,这本来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可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和你分享了。”
所有人都摒住呼吸拭目以待,期待电视剧里庸俗的告白情节真实在眼前上演。冷锦的笑容依旧带着薄凉的温度,清脆响亮仿若刺口,直直剜进她心里,句句羞辱言语:“纪善晚,你可知道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
步履踉跄的善晚张着震惊的眼,胸腔中就似有寒冷呼啸的风,空旷苍凉地来回穿荡,疼痛片刻漫天漫地地倾来。冷锦的目光依旧直视她,不带着丝毫的温度,嘴唇一翕一合对全世界说:“从来没有。”
善晚在后台抓住冷锦的衣襟,目光像把利剑,直插入他的身体:“你说什么。”
冷锦低下头,一根一根地掰开善晚的手指:“纪善晚,我追求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抛弃你。那次你深陷灾难,不过是我为了接近你而刻意安排的一场局。不过现在统统告诉你都没关系,因为,”冷锦抬起头来,嘴角缓缓露出讥讽的笑意,“沈音叙已经去美国了,他的父亲是无辜但被陷入牵连,他被急忙安排出国了。或许半年后他就会回来,又或许,他永远不回来。”
“你骗人。”善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崩溃。冷锦吐出的每个字就像一把利刃,而他毫不在意地向着她最痛的地方狠狠地扎进去。
“我再告诉你,其实你喜欢的人应该一直都是沈音叙,因为他就是霎时。你知道我有多讨厌你们俩么。荣誉光环掌声崇拜,这些本来都是该我拥有的。如果没有沈音叙如果没有沈音叙,我的人生早就光芒四射了,而不是活在他更有才有天赋的阴影下。乐队时是他现在又是你,你们两人可还真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呢。不过我已经能预料到,这次比赛我一定是第一。”
善晚看见冷锦的嘴唇翻涌着不可一世的喧嚣,眼中露出轻蔑的笑,然后飞快地手起手落,一个耳光清脆响亮地扇过去,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仰起头直视冷锦的眼:“这一巴掌是替音叙打你的。你就承认吧,你嫉妒音叙嫉妒得发狂。在我看来,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会K歌的男生而已,因为你对待身边的人只有利用和虚情假意,你唱的歌里从来没有真情流露,所以无论多久,你都赶不上音叙,这就是最终的结局。”
善晚从僵硬的人群中背脊笔直地离开,她想回到休息室,喝水补妆做最后的准备之类。善晚推开门,所有的喧嚣便瞬间融进空气里寻不到踪迹,照射过来的光线顿时汹涌铺展在脸上,她看见青桐和另外两个女生围在自己位置周围,想要拿走某件东西,见进来的自己干脆藏在身后,横眼看过来。
善晚与青桐长久地相望,空气中却蹿满火药,只等一根引火线,便能伺机爆发。
善晚走过去,摊开柔软的掌心,带着得体的微笑向青桐讨要东西:“还我。”
青桐丝毫没有被抓捕于案发现场应有的做贼心虚,反而不依不饶地嚷嚷:“东西在我这里,但我不给,你能拿我怎样。”
话音尚未落毕,善晚唇角垮下来,没有任何人看清她是怎样快速地拿起桌上的剪刀,擦过青桐的脸颊,在众人眨眼的瞬间,一小截似锦的头发便悄然落地。青桐不可抑制地感到恐慌而尖叫,善晚依然在微笑但温度不曾抵达眼角就已冰冷:“就这样。”
她们还当善晚是那夜被她们关在狭窄暗仄的房间里的孱弱女生,可在一瞬间她就已完成令人惊异的蜕变,她变得仿若独自一人便可抵挡千军万马的侵袭。
青桐把东西完璧归赵,如惊慌的兔子般逃得飞快,是自己的伴奏CD。善晚在空荡荡的房间坐下,眼中突然泛起哀伤的潮湿。
音叙,你看,你没在我身边,我总会把事弄得一团糟呢。
以前善晚闯了祸还无所畏惧,把双手交叠在背后仰起头撅着嘴:“怕什么,反正不是都有音叙你吗。”沈音叙低下头温柔地教导:“善晚,你要乖,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那你怎么办。”
善晚奇怪地看沈音叙,飞快地回答:“怎么会呢,音叙不会不要我。”
当日自信满满,从未想过意外比潮水的速度更让人措手不及吧。
音叙,现在的我一个人走路一个人看风景,一个人过人行道一个人望橱窗里寂寞的模特,一个人唱歌一个人又当自己的听众。
原来我的世界没有你,我就不再是往日骄傲的自己,我必须自己学着独立和坚强。我多希望我能再任性一次,闭上眼再睁开眼你就出现在我眼前。
果然任性到极致了吧。
掌声稀稀疏疏地响起时善晚独自走上台,置身在聚光灯下等待前奏,但等待良久第一个音都没有响起。观众席上有人带头起哄,口哨声尖锐地划破耳膜。
善晚跑下台到音响师那里确认,终于看清现在放的伴奏CD并不是自己事先放在桌上的那张。
导演急匆匆地跑来拉着善晚问:“能唱吗能唱吗,这种情况还能继续唱吗。”
善晚蓦然回首,就看见沈音叙在观众席中对自己无声地比口型,眉眼间带着无法掩饰的兴奋:“我说过会赢你们的。”
善晚全明白过来,是被人动了手脚。刚才青桐不是想拿走自己的CD,而是想要把调换的CD放回去。
善晚不可抑制地发笑,嘴角逐渐绽放荼蘼的花朵,眼中落满灯光一阵晕眩。她逃到洗手间,放着水发出很大的声响,她在水声的掩饰之下哭得厉害。以光洁的镜面为眸,看那个狼狈的自己。
不能唱下去。没有伴奏,没有化妆,没有觉得幸福的气息,没有音叙你,我好想逃掉。
音叙,如果你能看见现在的我,是会沉默还是难过。
可是,我想有一天,可以做你的骄傲呢。
善晚重新上场的时候,湿漉漉的头发随意地散在脸颊周围,淡而微凉的香味。素净的脸上没有任何妆眼瞳依然很亮。她穿着白色有褶皱的裙子,仿佛一朵开在悬崖的水仙。骤然打亮的追光灯下是一架安静的白色钢琴,善晚的手指很美,轻轻地蜷缩成寂寞的姿势,音符如水般流淌出。
可是这一次呢,我是为音叙为你而唱的,用你最喜欢的钢琴,以你最喜欢的姿态,唱你写给我的歌。
音叙对不起,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除了音叙你还能有谁写得出这样对自己口味的歌词。还能有谁熟知我的每一个缺点和习惯。还能有谁能为自己写出这样的一首歌。
唱歌时应该想最开心的事吗,那次和你去游乐场结果走散。四周是随着时间倒数的人群,手里端着玻璃器皿的人扮玩偶,滑着旱冰鞋溜过的环卫人员,被提前放的稀稀疏疏烟火,却没有你,那么盛大节日的欢喜我却不能和你共同见证。
我看不见你。整时的钟声开始响起,原本像下沉深海与世隔绝的岛屿的游乐场,灯光倏然喧闹地亮起。许多只玩偶呆呆地冲大家微笑,然后散发用好看发出清脆声响的糖纸包裹的糖果。人群欢呼着拥抱着欣喜。五颜六色鲜艳气球被放飞。七彩涂满各种油漆图画的旋木魔法般的轻盈旋转。机器发出微弱欢快的声音,那些悬挂在竹签上的棉花糖像一团团刚伸手摘下的云朵。
巨大的人扮玩偶离开原地,我才看见了对我微笑的你,原来你从未走开一直在我身旁,看着到处张望寻找你的我,一瞬间觉得快乐得天下无双了吧。
音叙,你等我等了那么久,这次就换我等你,你说好不好呢。
一时间受到无限关注的歌唱比赛终于落下帷幕,获得冠军的竟是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女生,她说她叫做纪善晚,她在等待一个男生。她要出一张专辑,叫做等待薰衣草,因为她在等待爱情。
玻璃盏里盛着酒红的樱桃暗紫的桑葚甜酸的杨梅,简深瞳单手撑着头吃。落地窗延接着阳台,种着一些白色小小的柔软雏菊,宋时迁坐在木椅上看一本小说,露出细长白皙的小腿,促狭心突起便转过一张如茶花般洁白的脸,一本正经地说:“深瞳,你知道吗。比起那些昂贵的指甲油,用新鲜的桑葚可以染出独一无二的紫色。”
简深瞳虽强烈怀疑过,但是身为中文系的时迁,说话总有一种让人信服的魔力,于是她便开始尝试。
时迁清浅一笑,把小说搁在脸上迷迷糊糊地睡过去,只有一段浓稠似锦的头发散落下来。隔了一会,是听到简深瞳发出的夸张尖叫惊醒,拿下小说转过脸去的。看到水果都被她扬起的手臂打翻全部滚落到地上,最后留下一屋狼藉借口逃进洗手间。是今天广播室的特邀嘉宾顾沿途,比安排时间提前半小时到来。
难怪深瞳一副惊慌失措的表情。她在染着指甲,而办公桌上的化妆用品和乱七八糟的时尚期刊杂志,都还没来得及收拾。
顾沿途并没有看到恍惚的时迁,而是随手拿起办公桌上的A4纸,那是时迁的呢喃故事,消遣地念:“无论如何我依然会等你,会一直等下去。”
风吹乱时迁的头发覆着大半张脸,露出的眼中流露着颠沛流离几个世纪的悲伤,隔了很久才艰难地说:“可是怎么说,其实你不会等我的,对不对呢。”
“我会陪你直到世界的尽头,请你,相信我。”台词如是说,无意窥见时迁泪水的顾沿途一瞬失了语。
简深瞳从洗手间出来,落落大方地对男生伸出右手:“你好,我是播音系的简深瞳,能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深感荣幸。”
因为是专科出生的缘故,说起话好听又得体,而简深瞳早已学会娴熟的化妆技巧,对于穿衣搭配很有心得,即使是在以声示人的广播室,打扮得也宛如平面模特。有多少男生爱慕她如一朵芍药般的容颜。
顾沿途伸手一握,一语双关地说:“应该说,是我的荣幸。”目光越过简深瞳的肩膀不偏不倚地落在时迁身上。
较校园里那些艺术生的骄傲自负眼高于顶,已小有名气的顾沿途却丝毫没有大牌架子,一举手一投足尽在细节体现他的好修养。宋时迁不说话只是亭亭地呆在一旁望着顾沿途,发现他的察觉目光后不自然地转过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