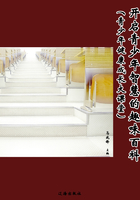”“老哥,你过谦了,能在你的领导下搞出我国第一代飞行器,实在是人生的大幸。你的事忙,时间紧。你快去联络其他人吧。”高瘦身材的刘粟禾,像一株坠着籽儿的高粱秆,谦逊地弯了弯腰,满面笑容。从刘粟禾家出来,他们赶到清华园,踏进了高睿琦的办公室。经美仙一介绍,高教授立即从办公椅上直起身来,满面笑容地说:“我正在等你,中央要求许多项目都要立马投入研究和实验,没有高性能的战机与火箭,别人就要看不起我们欺侮我们啊。”张克城握着他短而肥的手掌,激动地说:“要把你请去吃苦了啦。清华是全国最高学府,你能走出你的实验室真不简单哪。”“还不是受你夫人鼓励。她那三寸不烂之舌一摇动,许多科学家都为她描绘的前景所吸引。唉——这人啦,说起来也怪,许多领导来做我工作,叫我去领导这领导那,我都没答应,美仙却把我说动了。你们两口子真不简单哪,郎貌女才天成一对。好,今后我们就是同志加兄弟,让老美都生气。”高睿琦矮胖身材,大脑门、大鼻头、厚唇阔嘴,然而眼球被下垮的上眼皮和上耸的眼袋拥挤着,仿佛永远都露着一线浅浅的笑容,弥勒佛似的逗人可爱。他的名字和身材凑在一起,很有幽默感地使人发笑。
短短的半个月时间一晃而过,张克城在美仙的引荐下,拜访了几十名科研人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放弃了在大都市优越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乘上了空军指定的包机直飞成都。先到院里报到的人,听见这个爆炸式的新闻,纷纷放下手边紧张忙碌的工作,在山岩和沟畔采摘了许多不知名的野花,捆扎成束,串联成环,拥到了院大门外,加入了由院共青团组织的欢迎队伍。到机场接人的专车还没到达院大门,雄壮的锣鼓声早已敲打了起来,在唢呐和锣鼓声中,青年男女扭起了秧歌,富有激情地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科研精英。米德璘教授一行九十八人刚进大院下车,几十名着装一致,白衣短裙、靓丽可人的少女便蜂拥上前,向科学家们献上了束束鲜花,并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了野花编织的花环。教授们见张克城远在首都却把院子里的事安排得如此井井有条,深深地佩服起了这个大兵的领导才能。欢迎仪式的锣鼓和唢呐一直把科学家们迎进了刚落成不久的院部大礼堂。主席台上下,早已贴好了落座人姓名的椅子都显眼地摆在前几排的位置,姑娘们有序地把他们引领到自己的位子上。张克城的讲话简短有力,科学家的发言也掷地有声。
都有坚定的意志和决心搞出共和国的第一代航空航天器,好为新中国的崛起助威添彩。在几沟农田和山湾建研究院,体现了敢想敢干和人多力量大的浩然气魄。到院的第二天,张克城和副院长米德璘便带着新到的科学家到施工现场指导和察看。十多位所长都手拿图纸身处现场,对自己所的业务结合研究方向提出了许多科学合理的建议。瘦小的米德璘跟在高大的张克城身后,不住口地感叹道:“现在的确是科学技术人才大显身手的时代,中央作出规划不到一年时间,各所研究和实验大楼已基本盖成。
克城同志,你干得好啊,辛苦你了!创业阶段的艰辛我是感受过几次的。现在,多数科学家都已经到位,你应该好好休息几天啊。”米德璘的目光里充满了慈爱和关切。克城立即拉住德璘的手,谦逊地说:“米副院长过奖了,一年时间仅仅是盖了几十栋研究大楼而已。现在来的许多教授都是拖家带口,我们要加快进度,力争在年底前再盖成十几栋专家宿舍楼,不让你们挤大屋,俗话说‘安居乐业’,只有让你们安心地居住下来,我们的事业才能够全面地开展啊。”“你的观点我同意,这里环境好、气候好,离大城市也近。若全部按图纸建成了,并不比美国的航天基地逊色。”米德璘想着未来,顿时眉飞色舞地谈起了将要实现的美景。
星期六到了,科学家们纷纷走出临时办公的窝棚,帮助建筑工人递物件,搬砖头,挑灰浆,用金刚砂轮砖擦磨水磨石风洞两壁和顶壁。喜欢运动的刘粟禾边干活边哼着“我心中怀着美好的愿望,像苹果花在树枝上摇荡,它飘落进你温柔的胸膛……”还没唱完,在他身旁挥臂磨水磨石的屈秒音助理研究员,“咯咯”地一笑,说:“刘院长,我今天好幸福哇,劳动中还享受着天籁之音。”“劳动与歌声,都是中国人发明的……”粟禾一瞟身旁的秒音,见她正对自己温柔地微笑道:“可是,但你唱的不是中国的劳动号子呀,刘院长,你哼的是英国古老的伦敦小调啊。”刘粟禾睁大了双眼,吃惊地斜睨了一眼这个刚毕业不久的小妮子,仿佛在心里说:“咦,这个黄毛丫头懂得还多呢。看来,在这个研究院里,张克城聚的是八方英才。我还是应该先观望和研究一下别人的思想,才不至于贸然把人论出亲疏来。”想着,他立即故作惊喜,仿佛遇到知音似的欣慰地一笑,说:“屈秒音同志,还看不出来呢。你肯定是个唱歌的高人,下次,我专门找时间听你美妙的歌喉,好不好?”“哪里,哪里。
我只是知道音韵,母亲是唱越剧的,从小就训练我唱歌。但我却考上了清华的理工科目。出于对飞机的兴趣,才学了这个专业。”“好啊,好啊!虽然少了一个女歌唱家,但科学家队伍里却多了一个人才。难得,难得!”“我们初生牛犊,今后还望刘院长多多帮助、教诲呢。”“岂敢,岂敢。你二十四五岁就硕士毕业,今后还要靠你们呢。”“哪里,哪里。中国也应该像苏联和美国那样,造就一大批像你这样在专门领域里领军的优秀俊杰,民族的地位才能提高呀,才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啊。”秒音不卑不亢地回答着他。“嗨,看不出来,你还会恭维人呢。提高民族地位,是我们全所每一个人的责任。包括你也不例外,我们还渴盼院里多出几个巾帼英雄呢。”不知不觉中,一个上午就在这愉快的谈论中过去了。劳动中人们的肚子饿得格外的快。排了好长时间的队,屈秒音才打到饭菜,生在上海的她喜爱米饭和面食,喜欢吃清淡略带甜味的菜肴。但食堂里的厨师全是四川本土人,做的都是川菜。克城给食堂里的厨师开了会,厨师在炒菜时才分出了些南方和北方的味道。但上海是不南不北的城市,每当打菜都要难住她。
幸好她脑子灵光,每次就干脆南北味各打一些,在菜盒里一调和,就生出了不南不北,不甜不咸,不酸不辣的南北怪味来。正吃着饭,张克城来了,他见小姑娘挑挑拣拣地拈着菜儿,俯身问道:“你吃不惯这儿的菜饭,是吗?”屈秒音抬眼一望,见是院长在她身旁问询,连忙起身站定,雪白的脸蛋刷地染上了红晕,她哧哧地答道:“吃得惯,只是太辣了一些,还有麻麻的花椒味仿佛把舌头都捆住了似的,其他也没啥——哦,张院长,你还没有吃吧?”“我刚从省委回来,你快吃吧,下午我与你们一道劳动。”张克城刚在答话,刘粟禾吃过饭从小厅里出来。见克城询问的正是他的下属,立即上来介绍说:“她是研究空气动力的屈秒音,清华来的,上海人。”“嗨,我记起来了,你是我电话催你来的。你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服从祖国的需要’是不是?”张克城兴奋地笑着。“张院长,你的记性真好。哎——到了这儿一看,啊,才知道这里还是一片工地。住的是窝棚,吃的是食堂,看的是山头,耍的是河沟,夜晚蟋蟀叫,白天蚊子咬,无聊数星星,门前行人少。”“嚯,好厉害的嘴啊。看来你是选错了专业,你应该读文学和表演艺术什么的。
”刘粟禾听见屈秒音这么伶俐的口齿,接口惊叹地说。张克城却不一样,他笑呵呵地盯住这个美丽的女孩,赞叹道:“我没选错人,机械物理与文学艺术是姊妹,连成一体的。物理学家成就的突破,往往是受到音乐和诗歌或者是哲学的启示。好,屈秒音同志,你提的问题我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请你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这里将比上海大城市更美好哪。”刘粟禾站在张克城身后,悄悄地向秒音竖起了大拇指。下午,张克城来到风洞施工工地,这是研究院建设难度最大,施工技术最高的项目。歇工喝水的科研人员都围拢到院长身边,纷纷地谈起了他们到了院里的感受和对工程施工的建议。张克城见他们对科研的事业热情似火,立即说:“你们对工作的热情,求速的思想,想出成果的愿望,我都支持和理解。但现在我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留住你们这些人才。初创时期,条件差,让你们远道而来都吃苦受累了,我内心很不是个滋味。
我已经给省委汇报了,第一步是把实验、科研大楼建好;第二步是建像样的专家住宅楼和职工宿舍;第三步是逐步解决分居之苦;第四步是盖科研配套厂和加工厂,招收一批大中专毕业的女生,解决科技人才单身的问题。最近,我们职工医院要来了三十名年轻漂亮的女医生和女护士。他们不仅仅是来这里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在这里筑巢成家。”年轻的科技人员听了张克城的即兴演讲,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纷纷交头接耳地说:“张院长是个有人情味的通才,在他手下干事业既有奔头,又开心舒畅。我们在天府之国的根扎定了!”创业的劳动之苦没有人抱怨,但劳动结束后的洗澡却成了大问题。小型的澡堂一下子接纳不了拥来的一二百人,许多男士们便主动提出把大一点的男浴室让给女同志洗,他们都到风洞外的涟漪江去洗天然澡。这一提议立刻得到全体男士们的拥护,不一会儿他们都趿拉着拖鞋,端起脸盆向涟漪江边的盘羊沱拥去。盘羊沱是涟漪江的一个洄水湾。一个花岗岩的山嘴宛如盘羊的头,挡住了直射而来的江水,万千年飞流直下的江水,陡遇阻力,便拼命冲刷山体,日积月累,水流就掏空了山脚前的泥土和碎石,使之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浴塘。
椭圆形的浴塘足有二百亩水面,江水清澈见底,波纹涟漪荡漾,最深处不足五米,在江底游荡的白条鱼、麻秆鱼、鲢鱼和鲫鱼清晰可见,由于水清,缺乏营养,鱼儿们个个都是精瘦机灵,十分可爱。张克城是在河边生长的孩子,见了这一湾好水,立即率先跳下去探底,他觉得山嘴前的浴塘没有旋涡,便踩着水向岸上招手:“能游泳的都下来,游不来的在浅水湾,注意安全。”他叫过已下水来护卫他的童成壁,说:“我游得来水,你去浅滩下游盯住每一个人,若有危险,即时叫人去营救。这么多的人下水,难免有个闪失和意外,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童成壁转过山嘴,他和丁霁向下游游去,他们选择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岸边站住,紧紧盯住在浴塘里洗澡和游泳的人。日落西山了,最后一抹斜阳也从岩罅中收走了它的余晖。塘湾里的人早已洗去了满身的泥浆和疲乏,只觉得江水凉爽,纷纷说:“今年是秋里伏,真的是热得人哭,我们再凉快一会儿吧。”说完,他们都又泡在水里面去祛痱子,退暑热了。日落后没有日光照射的山谷江面,很快就起了一层薄雾。张克城见状,立即叫丁霁招呼大家上岸,许多人还对清洌的江水恋恋不舍,迟迟不肯上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