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仙听完父亲话里的意思,站起身来,给父亲母亲鞠了一个躬,含泪说:“爸,妈,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婚姻的事我懂,我也考虑过。但这事就请你们放心,我不会给你们出乱子的,也不会给你们丢脸面的。我想再去钻研几年科学技术,现在不考虑订婚结婚的事,就请父母大人代我谢过大姐夫。请原谅女儿的不孝。”邵力琛听完美仙的话,气得脸色发青。鹓看见了,忙过来给他捶背,温柔地劝着说:“唉,力琛哪,你是知道美仙的脾性的,女大不由娘。这事你就不要气了,待我与她商量了再说吧。”美仙见父亲为了她的婚事生气了,忙过来替鹓为他捶着肩背,恳求着说:“爸爸,都是女儿的不是,使你生气了。但婚姻的事,的确请你们不要为女儿操心,我再次谢过你们的好心与爱心。但一定请二老不必为此事怄气。以前你常给我说:‘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马牛’。我想在这件关于我的婚姻大事上,最好还是看个缘分,最好还是由我自己来选择、来决定,请你们一定不必为我的婚姻操心、怄气,伤了身体。”邵力琛见美仙态度坚决,也知道她性格比较刚烈,脾气倔犟,说一不二。他只好叹息一声,由书琴陪着下楼到工厂里面去了。
秋凉了,美仙辞过父母,由任菊花陪着,乘下江的轮船到了上海,再由上海换海轮到达天津。在天津,在途中又花了二十多天,八月底她们才疲惫不堪地到达学校。总务处办事员说:“学校带研究生的导师们到日本受训去了,要九月初才开学。”在学校安顿好寝室,美仙和菊花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先由菊花去探路,看哪些地方适合游玩。美仙则在寝室里整理带来的书刊和笔记,她想开学了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寝室里和一般的饭食就由菊花料理。总务处的人对美仙说:“这学期的女研究生只有你一个,你可以单独住。”所以,任菊花就留在了北平,陪着她度过难忘的岁月。在北平三年的读书、实验和研究,把邵美仙整个人也变成爱思考、爱静坐、爱做事而不爱蹦蹦跳跳,不爱喜笑欢乐的人了。从外表上看,她已是一个冷静、沉思的学者。写完了论文,校长就找她谈话,五十多岁的老学者,和颜悦色地在校长办公室对她恳切地说:“美仙哪,可以说你是理论物理研究和物理学这个领域屈指可数的女性。在医学领域的实践应用中,你的研究成果得到不少国外学者的钦佩,也有人请你到国外去研究或教学。但我们考虑过了,现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赶走日本强盗,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已迫在眉睫。所以,我们已经决定,待你毕业后,就聘你留校继续从事理论物理研究或教学。现在,你好好准备论文答辩。从这个月起,学校就给你薪金。”美仙望着校长慈祥和善的面孔,听完他的谈话,没有反对也没有答应,只是微微地笑了笑,说了一番感谢校长栽培的客气话,便退出了校长室。这个春夏之交的北平,人们比往常显得躁动不安。强盗们在垂死挣扎,整天大街上都有刺耳的警笛声,他们露出狰狞的本性和丑恶的面目,举起刀枪,加紧对反抗侵略的爱国人士进行血腥的屠杀。越是镇压,越有反抗,工人和农民愤怒地举行了罢工和罢市,进行了反饥饿,反迫害,反侵略的游行;学生们见工人和农民抗日的情绪高涨,就联合起来走上街头,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还我河山,消灭强盗”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地响。成千上万的市民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地支援学生、工人的罢课、罢工和罢市。正在侵略者被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苏联红军进入了东北三省,勇敢的红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老巢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似乎跟苏军配合默契,随即便进入了东北三省。
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空前强大和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以及全世界反战形势的变化,逼迫日本帝国主义举起了投降的白旗,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随着这一特大喜讯的传开,北平沸腾了,中国沸腾了。在北平,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举着旗帜,流着热泪,或欢笑,或狂歌,或鸣炮,或舞龙,在欢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八年的血、八年的泪、八年的苦战和奋斗,终于迎来了欢呼和兴奋的时刻。北平的大专院校和其他社会机构一起,组成了上千个慰问团,纷纷到军队的驻地,慰问在前方取得胜利的将士。邵美仙听到消息,不顾论文答辩后的疲劳,作为留校教师率先组织学生报名参加了慰问团。她与师生一道,不顾酷夏的溽热,不顾物资的匮乏,匆促地排练了欢庆节目,率团乘火车转汽车到了河北省太行山下的易水河畔。没吃一顿饭,没喝一滴水,她便登台演出抗日和人民欢呼胜利的文艺节目。
她报幕,她领唱,她演小品,仿佛压抑在她心中的苦闷一旦被释放,她那少女般激情似火的性格又瞬间地爆发了出来。台下的观众有国民党的军队,也有共产党的军队,四围的群众把军人团在核心,让他们与演出的学生一道,享受着胜利的欢呼与激情。张克城带着团部的人员和在易水的一个营,参加了军民联欢。本来他要登台演出的,但陈赓司令员上午在太岳军区召见了他,要他明天就率领全团的指战员,分赴太行山的五个县城和村镇,去接收日本强盗的投降。对顽抗和不放下武器的鬼子要迅速、干净、彻底消灭。他领悟了首长的指示,去掉了节目单上他参演的节目,只登台即兴地作了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我们今后的任务为话题的三分钟演讲,便博得了台下雷鸣般的掌声。美仙在台后化妆,猛地听见一个熟悉的男中音在台上演讲,那振奋人心的语句和带有磁性的嗓音,不就是她思念了七年多的张克城么?美仙停止了化妆,她想到台前去看个究竟,去认个明白。
刚才报幕时,她只是照别人写着的字条念出:“现在,有请抗日英雄张团长讲话。”接着是掌声,她没有看清楚上台人的面相,便匆匆地下台来化妆了。没想到先前便错过了与克城相识相认的良机。她刚迈步往台上冲,团长讲完话已挺着胸往台下走。她心里忽然又想:“我刚才在台上宣读请他讲话并做着手势时,难道他都没有认出是我邵美仙!”想着,另一种可怕的预兆又涌上来,她心里“咯噔”的一声,立即止住了脚步,心想难道他不认我了吗?难道他果真是二姐所言的“没有良心的,猪狗不如的,丧尽天良的东西”了吗?她从后台口刚冲上舞台边沿,见他已坐进了一片军人堆里。她情急生智,立即又做出报幕的姿势出现在了舞台上。她没有照纸片上所写的去念,而是扬起头,激情万分地以自身的情感祝贺着抗战的胜利,向着台下的军人动情地说:“台下抗日的英雄们,你们在前线流血,你们在前方杀敌。但在大后方和沦陷区,却有你们的父母,有你们的妻子和儿女。
他们在守望着你们,在期盼着你们,在日夜地祝福着你们!他们流干了眼泪,盼瞎了眼睛,等白了头发,为的就是企盼和等待抗战的胜利,为的就是祈祷抗战胜利了好与你们团聚,好与你们同享胜利的喜悦与快乐呀!“可爱的士兵们,将军们,我生长在苏南,全家被日本强盗逼迫,我们跋山涉水迁到了重庆,我从南方辗转到北方求学读书,就是为了寻找我那投奔延安矢志抗日的丈夫,就是为了追上我丈夫那抗日的脚步与激情,共同到前线去杀敌,去雪恨。可是,在茫茫人海中我虽然望眼欲穿,渴盼似焰,却没有追寻到他。抗战胜利了,他也许成了功臣,也许就坐在我们那可爱的士兵之中。我仿佛已经听到了他的心跳,听到了他的声音。也许他已经忘记了我,但是,此时此刻,我想念我丈夫的那一颗忠贞而纯洁的心,在为他颤动,在为他流血,在为他流泪,在为他呐喊……”美仙在舞台上哭了。她的倾诉打动了台下所有的观众,有的在偷偷地流泪,有的在轻轻地交谈。
就在她呜呜哭泣的时刻,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猛地冲上了舞台,他疾步上前,猛地搂抱住美仙,热泪喷涌而出地呼叫道:“美仙,美仙!我就是张克城,我就是你的丈夫张克城啊!”美仙推开张克城的拥抱,惊诧万分地审视了他一刹那,突然她又猛地扑进他的怀抱,飞快地抡起了双拳,边啼哭边捶打着他那宽阔的胸膛:“恨死你个张克城!你把我想得好苦,等得好惨啊,七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你,一直在盼望你,一直在想念你。结果——结果你连音信都不给我一个……你害得我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台下的人见此情景,以为是安排的剧情,演出的是小品,都瞪大着眼睛,目瞪口呆地观看着。这时,从舞台幕后走出一个五十开外的女子,她边走边用白皙的手指抿了抿短发,用圆润好听的北京话语,热泪盈眶地对着台下的观众说:“先生们,女士们,我是邵美仙所在大学的副校长冉雪馨,台上的俩人,是真实的一对好鸳鸯,是失散了七年多的一对恩爱夫妻!没想到在抗战胜利的舞台上,他们得到了真正的团圆。在此,我代表燕京大学真诚地祝贺他们夫妻团聚,祝福他们恩爱一世,白头到老,永不分离!”听过校长的话语,台下一片哗然。很快,便暴风雨般地响起了人们的鼓掌声、欢呼声、跳跃声和祝福声。
慰问演出结束了。士兵们都围着美仙和张克城。他们激动地把平日威严的团长抬起来抛向空中,把美仙抬在手臂上,他们尽情地欢笑着,呼喊着,你挤我拥,一路人声鼎沸、喜气洋洋地回到了驻地。政委李昌达听过了团长这段爱情的传奇,比打了胜仗还要高兴,他立即回到驻地,叫来一班战士,以打歼灭战的做法,很快就给这对分别了七年多的鸳鸯,布置了一间新房。待欢呼的人群到达时,政委却摆手轰散了这帮喜爱追闹的男人,他严肃着面孔,对他们说:“时间这么紧迫,都回去休息吧,不要打扰了团长和邵美仙同志团聚后的相亲相爱。他们还有好多话要说嘞。”说完,他和团政治部主任罗德仁把团长和美仙拥进了战地这间简陋的洞房,祝福了他们几句,便喜悦地离开了新房。第二日天刚破晓,窗口已透进亮光,张克城跃起身子,轻轻地在美仙的唇上吻了吻,便穿衣走出了营房。美仙起床后,见卫兵已给她端来了早饭。她匆匆吃过早餐,便叫卫兵带她到营房里转了一圈。
蓦地,她心里产生了一种新的概念与主张。慰问演出的师生回北平了。临行前,美仙给冉雪馨校长递上了一份解聘的辞职报告。冉雪馨接过报告一看,立即摘下眼镜瞪着大眼睛,惊诧地说:“嚯,邵美仙哪,你是专家型的学者啊。你只有在北平那样的大城市和有影响的大学里,才有你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啊。你跟着张克城在山沟里跑,能出成果?好,好,你现在脑壳热,我们先走了,待你冷静地想好了,我们的大学和学科,随时都欢迎你回来。”送走了校长,美仙穿上了张克城的土黄色军服,叫卫兵带着她到了团卫生队,她找到了队长祁爱雪,说她要到卫生队当军医。祁爱雪连连摆着手,说:“你吃不消,你吃不消。听说你是博士,我们整个八路军还没有一个博士女军医哪。这个,这个我可做不了主啊。当然,当然我是非常欢迎,非常欢迎你的。”
祁爱雪十八九岁的年纪,不高的个子,但天生有一张好看的瓜子形脸蛋,瘦削的下颌尖尖的,两腮有一对浅浅的酒窝,一笑便要醉人似的挂在嘴角边,薄薄的双眼皮,薄薄的双唇,仿佛有许多包容不住的智慧和灵气要喷薄而出。别看她是个小个子女孩,平时,她对伤病员说话都是干脆利落,今日一见到邵美仙,却支支吾吾地表达不出她的意思,内心仿佛隐藏着一种秘密和期许,要被人戳破了似的。美仙见她说话不爽快,就转身到几个临时的病房转了转,见卫生队的医疗设备是如此的简陋,除了一些最基本的医疗器械外,医生均是通过传统的望、闻、问、切的方法诊治病人,药品也非常少。看完,她没吭一声便离开卫生队,回到了她的新房。军营里的生活使她感到新奇,见驻地剩下不多的小伙子们整天都忙忙碌碌,她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但插不上手。见紫荆关的夕阳落了一次又一次,她终于忍耐不住游手闲逛的清静与寂寞了。她去找政委,政委到易县的乡镇上去了,守发报机的参谋对她说:“团长和政委今晚都要回营地。”美仙谢过参谋,又回到新房。她闭门思考她如何才能把平生学到的知识与技术,用来为战场上的伤病员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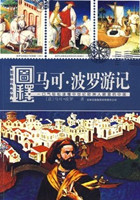
![[重生]女配的姐姐](http://c.dushuhao.com/images/book/2020/03/14/16272906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