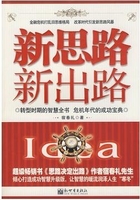“又来了,姑娘的嘴比我厉害百倍,我是说不过姑娘了。”紫鹃笑道:“不过,姑娘,我今儿晚上却觉得从没有过的安心呢,不知是不是那两个人的缘故。只是姑娘总不能就这么和北静王耗着的,你们毕竟是夫妻的。”
黛玉模糊地说道:“谁知道以后的事啊?快睡吧,明儿你还要早起做早饭呢。”紫鹃听了一会,却听不到黛玉说什么,只以为她睡着了,自己也就翻了个身睡了。
其实黛玉不想和她再说这个话题了,听到紫鹃均匀的呼吸声,黛玉心里浮想联翩:这个丫头大了,不能再耽误她了。瞧着白天她和凌云的默契,黛玉就知道,紫鹃是留不得了,再留下去,自己的良心上过不去了。
可是自己又该怎么办呢?就这样跟着水溶回去,还是守着这间小屋子过完一辈子。今晚看水溶那情形,是不会由着自己就这样的,但是他也不会逼迫自己的,不是吗?
从这一点看来,他还是一个比较儒雅的人啊,自己究竟对他是有心还是无心,黛玉一时半会也说不清,可是自己为什么会担心他夜里受凉,而让紫鹃送了被子过去呢?
难道这就是心里有他吗?黛玉摇了摇脑袋,怎么都想不明白,索性不去想了,就由着自己的心吧,正如紫鹃所说,今儿晚上真是说不出的安心,难道这真的就是一种归属感吗?
枝头上的鸟儿吱吱喳喳的叫声,吵醒了黛玉,她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看到紫鹃还躺在那儿大睡,不由用手碰了碰她:“快起来吧,小心你那情郎挨饿了。”
紫鹃还没睁眼就听到自家姑娘打趣自己,也不当真,就笑道:“姑娘还说我呢,今儿一大早就说上这些不着调的话,看来姑娘心情好得很啊。这几日里都没看到姑娘笑过,今儿一大早,看来就得了个彩头儿呢。”
黛玉起身披衣,一边笑道:“真真如你这死蹄子说的,我昨儿夜里睡得特别香,一早上醒来就说不出的高兴呢,许是太久都揪着心,昨儿终于能安心了吧。”
紫鹃利索地穿好衣服,赶紧着打理起黛玉一头长长的黑发来,嘴里也不闲着,絮絮叨叨地说道:“姑娘,我冷眼看去,北静王真的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呢,且不说地位摆在那儿了,但看他小心伏低的样子,就没有几个男人能做到呢,连以前的宝玉……”
紫鹃正说得顺嘴,不防就提到了宝玉,见黛玉脸上已是变了色,忙住了口,拿手打了自己的脸道:“姑娘,你别生气,都是紫鹃的这张臭嘴,什么不好偏要说什么。”
“好了,”黛玉淡淡地道:“你也别自责了,我又没怪你,连你也以为我中意的是宝玉吗?”
紫鹃不解地问道:“若是姑娘不中意宝玉,为什么每日里都要因为他哭上几回呢?”
黛玉对着镜子照了照自己的脸,才道:“自那次活过来之后,我对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小时候儿,我们两个一处起坐,日子久了,比别人亲密些倒是真的,他也许因了这个,就想到别的上头去了,你们自然也信以为是了。”
黛玉顿了顿又道:“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我只想平平静静地过我的日子。”
紫鹃在镜子里瞧了瞧她的脸色,不敢再说什么,两手灵巧地给黛玉挽好了发髻,就去叫醒厨房里大睡的两个人。
厨房里,北静王水溶和护卫凌云正裹着一床夹被,呼呼大睡。紫鹃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进去后就看到这幅情景。
凌云身负武功的人,听到动静早就醒了过来,眼睛半睁着,只见一抹淡绿色的身影,正是紫鹃。
于是他猛地坐了起来,紫鹃不防他醒了,正要上前晃醒他,却见他一下起来了,倒唬了一跳,摸着心口小声道:“你做什么?吓死我了。”
凌云无声地笑了,小声说道:“谁知道你的胆子像个兔子似的,这么不经吓!”
转脸看了看水溶,凌云悄声道:“爷功夫并不弱于我的,怎么还没醒?”水溶躺在一边,全然不知两个人正在说话。
凌云心下诧异,忙用手推了推他:“爷,该起了。”水溶方睁了睁眼,用手揉着,问道:“什么时辰了?”
紫鹃在一边恭敬地回道:“王爷,大概卯初了。”水溶“哦”了一声,坐起身来,从怀里掏出表看了看,确实该起了。于是穿了外衣,一边系着纽子一边问道:“你家姑娘起了吗?”
“起了,正在洗漱呢。”紫鹃小声地答道。水溶点了点头,就往外走了两步,但是身子却晃了两晃。凌云眼疾手快地忙上前扶住了他,关切地问道:“爷,你身子不舒服吗?”
水溶摇了摇头:“没什么,可能昨夜里没睡好,有点头疼。”凌云还是不放心,担忧地看着他。
水溶摆摆手,让他和紫鹃留在厨房里做些饭菜,自己一人摇摇晃晃地到黛玉的屋里去了。黛玉这时正在洗漱,水溶来到她的身后,凝神看了她一会。
黛玉转过身来,发现水溶正站在后面,一声不响,不由埋怨道:“你这个人,一大早上的就站在后面,想干什么呀?”
水溶无声地一笑,看见黛玉洗好了,就说道:“我就在你这儿洗洗吧。”也不管黛玉同不同意,水溶自己上前用黛玉洗过的水,洗了一回。见黛玉正在擦香脂,也张着手去要。
黛玉哭笑不得地看了他一眼,嗔道:“你一个大男人也用这些?”水溶听后方讪讪地撤了手,只是看着黛玉出神。黛玉也不理会他,自坐了桌子边写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