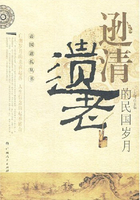水溶不着痕迹地躲开了,把手伸到袖子里,自己穿上了,一边系着衣纽,一边说道:“王妃也该多加件衣服,夜深了,怎么还不早点歇着?身子才好些了,要好生保养着才是。”
王妃听着水溶这貌似关心,实则拒人千里的话,心里一阵翻腾,不知道自己到底什么地方不好,怎么就是走不进他的心里呢?
本待要走,想想不能就这么放弃了。王妃打定主意后,依然笑着说道:“王爷回来才几天,府里就出了那么多大事,想必王爷也没能好生歇着。这都是妾身的过错,不能让王爷省心哪。”
水溶见她说出这些话,也不好就打发她走,淡淡地应道:“这怪不着你什么,你身子本来就不好嘛,府里的事情一向是李侧妃打理着,你哪能知道那么多。你还是安心的养好身子要紧。”
王妃见水溶句句都是为自己着想的话,可听来却一点温情都没有,自己已经受够了这种相敬如宾的日子了,多想和他像普通夫妻那样,过着温馨平淡的生活,可是这一切看来是不可能的了。只是她仍然不死心,都说“水滴石穿”,自己就不信水溶是个石头人,先前不是也为林庶妃的死痛心疾首吗?
想到这里,王妃低声下气地说道:“王爷,妾身这些日子身子大好了,王爷也是多日没到后院里去,今晚就让妾身伺候王爷歇了吧?”
水溶不成想王妃竟然亲口和自己求欢,再看王妃的脸,早已低得看不见了,想必她也是鼓起极大地勇气的,只是现在的水溶,心里装不下别的女人了,又怎能和她有那夫妻之事呢?只是王妃的要求却也合情合理,容不得自己拒绝。
水溶心里犯了难,沉吟了一刻,方道:“近来本王奔波于外,身子疲乏得很,想要好好地清静几日,王妃还是先回去自歇了吧?”
王妃见话已说到这个份上,知道无望了,也就低头福了福身子,黯然地离去了。水溶望着她失神的背影,默默念道:“对不起,你嫁给本王就是一个错误,本王不能给你任何承诺。”
此时,京郊的别院里,黛玉正手托着腮,独自一人对烛独坐,默默沉思。白天那个人好生奇怪,怎么就突然跑到自己的院子里?听他话音,自己是他的妾侍了,只是自己怎么又被白衣公子带到这儿了?
如果那人真的是自己的夫君,那为什么自己对他一丁点儿印象全无?紫鹃说过,贾家把她送给了北静王,难道他就是北静王?那么那白衣公子会是何人?北静王当时揪着他说道“什么皇子也不怕”,那他就是皇子了?皇子把她放到这儿干什么?
黛玉努力地想着,无奈脑子里一片模糊,越是想着,头就越疼,不禁两手揉着太阳穴,懊恼地捶着自己的头。
紫鹃进来添茶,正好看到了黛玉正拼命地用拳头砸着自己的脑袋,忙上前箍住黛玉的手,道:“姑娘,你这是怎么了?好好地怎么打起自己了?”
黛玉也不好告诉她缘故,就打起精神,接过紫鹃递上来的茶,轻啜了一口,就放下了。紫鹃转到她身后,轻柔地给她捏着肩。黛玉不觉好了许多,转过头来,拍着紫鹃的手,笑了笑道:“我没事了,你歇着吧。”
紫鹃收了手,来到黛玉对面,黛玉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小脚踏,道:“坐在那儿,我们说说话。”
紫鹃顺从地坐了,黛玉递给她一盏茶,也就接了。黛玉以前就和紫鹃的情分不同,如今只剩了主仆两个相依为命了,黛玉更拿她当姐妹,紫鹃在她面前拘束了几次,结果每次都是被黛玉数落一通,不让她再用这些常礼约束自己,紫鹃也就慢慢地习惯了。
主仆两个面对面地坐了,黛玉只管端着杯子把玩着,紫鹃见状,就笑道:“姑娘说是有话说,让我坐了,却不说话,又在这儿打哑谜呢。”
黛玉不禁也笑了,嗔道:“小蹄子儿,这才几天,你就上头上脸的了。口里就你呀我呀的叫起来。”
紫鹃笑道:“姑娘也真是的,偏爱挑小刺儿,前儿个我说了‘奴婢’,结果姑娘就把我数落了一通,这会子又提起这个来。”
紫鹃见黛玉有点心不在焉,没接自己的话,就试探着道:“姑娘,不是我替你操心,论理,你也到了该嫁的年纪,就这样主不主、客不客的住在这儿,终究不妥啊。”
“你以为我想常住在这儿吗?”黛玉放下了杯子,站起身子走到窗前,眺望着远方,幽幽地说道:“如今,我就像水上的飘萍,无依无靠,我还能到哪儿去呢?你又不是没见过,老家的宅子早就让贾家卖完了,但凡我有个地儿,还能在这儿呆下去吗?”
紫鹃见黛玉说着说着,眼里迸出了泪,忙起身上前递过帕子,自个儿埋怨道:“姑娘,都是我不好,不该提这个的。我原本想着为姑娘打算一番,没想到倒惹得姑娘伤心。”
黛玉擦了擦眼角,转过身来,直视着前方,苦笑道:“没什么,你说的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分,有什么话不能说的!你为我好,这我心里有数。只是我现在一点法子也没,倒叫我为了难哪。”
紫鹃扶着黛玉来到床边坐下,自己掇了脚踏坐在下首,看着黛玉,认真地说道:“姑娘,既然不愿寄人篱下,我们也要想个万全之策才是。”
黛玉倚着床半躺着,问道:“如今倒有什么万全之策啊?”
紫鹃小心翼翼地说道:“姑娘,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横竖要嫁人的。以前在贾家又是她们做主,现在你孤身一人,万事还不是自己说了算?这婚姻大事,是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儿,姑娘眼前有那么好的人选,为什么不及早地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