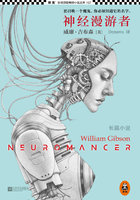黛玉心里有些紧张,屏住呼吸,手上的动作不由轻微了许多,轻柔地将药粉撒上,一面撒一面注意地看着他的表情,不住地寻问着水溶疼不疼,见她神情关切,水溶心里大快。
看着近在咫尺不住眨动着的长睫毛,细腻柔滑的肌肤,心里一动,突然起了促狭之心,佯作疼痛地低呼了一声,见他双眉微蹙,想是极力地忍受着,黛玉忙满是歉意地道:“王爷,是不是弄疼了你了?”
见她一脸的不忍,眸子盈盈如水看着自己,水溶忍着心头的笑意故作轻松地道:“无碍,本王能受得住!”
黛玉动作小心地用纱布一圈圈为他缠好,有些不解地道:“王爷不是摔伤的吗,怎么会有外伤?看样子好象是什么利器所伤呢!”小手在自己的臂上移动,那份异样的感觉令水溶有些失神,恨不得总被他这么抚摸下去才好。
心里一动,墨眸潋滟,俯下首看着近在咫尺的娇颜,肌肤细腻如瓷,莹白如玉,此刻在灯光下越发显得娇柔清丽,微微翕动的长睫毛说不出地动人。水溶竟然有种不想隐瞒,欲告诉她真相的冲动。
强压了压,黛玉兀自疑惑道:“王爷的身手民女虽没见过,但月下的身手应该不错罢,这是谁人有这么大的胆子伤到王爷呢?”蹙着眉头不由她不多想。
见她关心和纳闷,水溶心头一暖,知她聪慧,即使自己不明说,她只怕也会多想,但终不想更多的人知道此事,淡淡地道:“是个意外而已!”
黛玉水眸微微一闪,方才水溶说是不小心骑马受了伤,此刻又是另外一个说辞,看来其中有端倪,见水溶似是不想说,黛玉微微点点没有继续往下问。
动作越发轻柔起来:“好了!”如花的笑靥牵动人心,水溶眯起墨眸,手抚着她包扎的手臂,似乎连疼痛也减轻了许多。见天色不早,黛玉方起身回清苑,见黛玉的倩影消逝于融融的夜色之中,水溶轻抚着伤臂,脸上扯起一抹慵懒而温柔的笑意。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连数日,程达自从在皇家禁苑隐太子陵寝前出现后,如同几年前一样,再度消逝不见。
皇宫大内的的侍卫,以及水溶等紧张了数日后,见此人毫无踪影,水昊天便似了然于胸地道:“怎么样,是你们多虑了罢,如今他们早大势已去,识实务者方为俊杰,不过是为了尽一下主仆之情罢了!也值得你们这么大动干戈的,好了,将皇宫多余的守卫撤去,一切照常就是了!这些天闹得人心惶惶地,你们不累朕瞧着还不自在呢,好似朕真的老了不中用了!”
说着似觉自己这番话有点重,毕竟这是两个儿子对自己的关心,摆摆手道:“罢了,这几天你们也跟着担惊受怕的,现在可以好好睡个安稳觉了!”
水溶掀起一抹淡笑不吭声,水漓不惊不扰地道:“父皇的安危重要,谨慎一点也是应该的!”
水昊天摩挲着搭手上的龙头,微一沉吟道:“渤海国使后天便到,溶儿的胳膊也好得差不多了,你们俩会同礼部,好好地安排接待事宜,不得疏忽了!”二人领命。
见水昊天面色严峻陷入沉思,二人先后相跟着退了出来。风乍起,吹动二人衣袂,发丝飞扬,飘然如飞。拐过石拱桥,水溶收住步子,笑不丝地道:“二哥此次深谙父皇之心,不知何时二哥如此会揣摩父皇的心思了?”
面对水溶着那双含笑的黑瞳,水漓背影一顿,转过身来不动声色地道:“父皇为君为父,即使是个普通的臣子,也该为其分忧,身为他的儿子,你我更是责无旁贷!”
水溶笑容一收:“这一点,三弟还得向二哥学学如何讨父皇的欢心,如何揣摩父皇的心思,有时间三弟会向二哥讨教下妙招!”说罢轻拈着发丝,笑不丝地转身向慈宁宫方向而去。水漓看着他的身影,双拳握了握,脸色一沉,片刻后不动声色地迈开步子。
清苑内,那棵高大的月月桂,此时仍开着淡白的小花,一簇簇,挤在枝头,热闹而馥郁,香气随着风的轻拂沁入各个角落。
黛玉手拈一枚棋子,正凝神思考,这一步她已经思忖了半晌仍拿不准如何落子。此刻蹙着秀眉,迟疑不绝。紫鹃收拾着案头的笔墨纸砚等物什,那一张秋菊傲霜图此时字迹已半干,紫鹃小心地吹拂着,生怕落下什么脏东西。
黛玉头也不抬地道:“紫鹃,由它罢,不过是闲时的玩意罢了,不必那么小心的!”
紫鹃却执意道:“那不成,姑娘的东西,全是好的,不能随便糟蹋!”说着小心翼翼地放到一旁,黛玉瞥了她一眼,随意地笑笑,注意力复又投入到了棋势上。
紫鹃收拾得差不多了,眨着大眼忽地问道:“对了,姑娘,想起个事来!”黛玉嗯了一声:“说!”轻轻落下一子,并不抬头。
紫鹃便道:“姑娘天天给王爷抄写,王爷一个月给姑娘多少银子啊?”
什么银子啊?黛玉仍沉浸在黑白世界里,对紫鹃的问话有些不明。紫鹃便重复了一句:“姑娘总不能替王爷白抄写罢,怎么着也得给点酬劳的吧?”
哦,黛玉终于抬起头,一双妙目看了紫鹃半晌扑哧一笑,紫鹃一挑眉:“姑娘笑什么,我不该问吗?”
黛玉掠了掠鬓边的散发笑道:“我们俩在府里白吃白喝白住的,难道还伸手向王爷要银子?亏你说得出,我可做不出!”
说着复低下头去:“王爷的救命之恩无以为报,抄写些东西算什么呢,还想要银子?”说着笑不丝地瞅着紫鹃:“你是越来越会精打细算了!难道是有什么东西缺了手,我们不是还有些散碎的银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