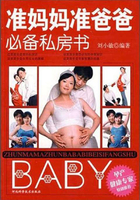话出口想到贾母的吩咐,不觉蓦地收住口,宝玉猛地转向她大声道:“林妹妹呢,她去哪了,你们把她弄到哪去了?”
见宝玉的话又似有些糊涂,袭人一皱眉,宝玉回过身摇晃着她急急地问着:“你快说啊,林妹妹她去哪了?你一定知道的,你们全瞒着我一个人,是不是?”
情急之下,宝玉的力气大得惊人,袭人被他抓得胳膊生疼,一狠心,索性道:“二爷,林姑娘暂时有些事,过些日子才能回来的,咱还是回去罢,不然,太太知道你出来,责罚我们事小,只怕二爷又要被关在怡红院了!”
“她真的走了?”宝玉愕然,忽地脸色惨白,袭人见状不好只得好言劝慰着。宝玉置若罔闻,神情僵滞地回过身来,复用力地拍打着门扉,神情迷茫,象个执拗的孩子般不肯停止,疯了似地不停地喃喃着。不一会儿,手指缝中慢慢淌下一丝血迹,门扉上斑斑驳驳全是血渍。
袭人愕然地看着,喃喃着:“宝玉!”
终于,拍得累了,宝玉的身子顺着门慢慢地坠落,脸上那丝痛状令人不忍:“林妹妹,你走了,你抛下我一个人去了,你真是狠心,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什么意思呢?”
身子无力地瘫软在门前,手掌上血渍沁出,但他丝毫感觉不到痛,头垂下来,喉间发出困兽般的嘶吼和低咽!
袭人望着绝望而痛苦的宝玉,心里五味杂陈,可又不敢近前相劝,只得呆怔着。良久,方小心翼翼地试着去扶宝玉:“二爷,这里风大,还是回去罢,你这个样子,若是林姑娘见了,只怕也不忍呢,过两天听说林姑娘便回来了呢,她肯定也不希望看到你这么颓废不兴呢!”
宝玉的眸子,些微转动了一下,无助地望着袭人:“她真这么说的,过两天就回来?”
袭人只得搪塞着,宝玉似是不相信地摇摇头。这时却见秋纹急急地跑了来,及到近前停下步子,喘着粗气,手里扬起一串钥匙,袭人便迟疑道:“这是哪来的?”
秋纹抿了抿嘴喘了口气道:“方才麝月见你和二爷往这边来了,便知二爷又上来倔脾气了,所以便去找了老太太,谁知老太太正在午睡,听琥珀说钥匙在琏二奶奶手里,于是我们俩便找了二奶奶,把钥匙要来了。二奶奶说,宝玉这是心病,就让他去罢,不然他永远也钻不出来!”
袭人一皱眉,神色复杂地接过钥匙,开了门,扶着宝玉道:“二爷,进去罢!”
宝玉眸内闪过一丝亮彩,被袭人和秋纹搀扶着走进了潇湘馆。馆内,人去屋空,一片寂静,唯有粉墙一带的几杆翠竹,依旧在风中轻摆凤尾,不时发出微微的声响,竟是说不出的凄凉。
宝玉打了个寒噤,心头一阵酸涩:“林妹妹!”这时,却听到廊上月洞里传来了脆生生的叫声:“紫鹃,沏茶!宝玉来了!”
三人均一惊,环顾周围,宝玉眸子抖然一亮,几步来到声音传出来的地方,一看原来是那只虎皮大鹦鹉,随即眸子复黯淡下去。
袭人初时惊诧地听着,不明所以,半晌方醒过神来,是那只鹦鹉在说话,于是忙紧随了过去,见宝玉形单影只,身影说不出地落寂,痴呆呆地望着那只鹦鹉。
那只虎皮大鹦鹉在架子上走来走去,宝玉呆愣了一下喃喃地问着:“妹妹走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
见宝玉呆滞地和鹦鹉说着话,袭人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衣襟:“宝二爷!”
宝玉丝毫不予理会,依旧望着鹦鹉出神,眸中的亮彩复又暗淡了下去。
这时,鹦鹉扑棱着翅膀叫着:“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宝玉一呆,嘴里默默地喃喃着:“愿奴胁下生双翼!”蓦地,脸色如死灰一般,嘴唇有些发颤,身子一趔趄,险些栽倒。
袭人一惊忙扶住他:“宝玉,你怎么了?”
宝玉嘴角扯起一抹苦涩的笑意,仰头望着天际飘浮的云朵,眸中虚空如梦:“林妹妹肯定不会再回来了,我能感觉得到!”
袭人惊讶地看着他:“宝二爷,别乱说了,要不回头林姑娘又生气了!”
宝玉充耳未闻,仍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脸上一片凄迷:“这里没有人可留恋了,你看天上的白云,多自由,她既然走了,还回到这个牢笼来做什么呢?”
黯淡的眸子转了转,对着鹦鹉道:“你说是不是,林妹妹不会再回来了,你知道的!”
鹦鹉歪着脑袋,两只黑豆般的眼睛乌溜溜地看着他,忽地又叫了一声:“质本洁来还洁去!”
宝玉蓦地脸色苍白,嘴角扯起一抹淡淡的苦笑,失神地望着蔚蓝的天空,整个人仿佛被抽去了所有的力气和精神,复陷入颓丧中。
袭人鼻子一酸,微咽着劝道:“不管怎么样,二爷还得当心自己的身子,不然老太太看着心里也难受不是!”
宝玉木呆呆地,嘴里不停地念叼着:“愿奴胁下生双翼!”
旁边秋纹低声对袭人道:“方才琏二奶奶说了,林姑娘最喜欢这只鹦鹉了,现在潇湘馆没有人了,教人偷偷地将这只鸟送到她那里呢,她帮忙照看着,不然只怕饿死了呢!”
袭人叹了口气,答应着!复看了一眼失魂落魄的宝玉,轻声劝慰着:“宝玉,回去罢!”宝玉嘴里喃喃着,任由袭人和秋纹扶着,慢慢地回了怡红院。
秋意浓郁,淡黄中泛着微红的枫叶,摇曳着秋的韵致和妩媚。清晨,一层薄薄的清雾,随着晨曦的灿亮而转瞬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