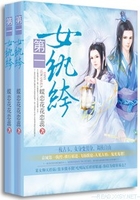“不必多言。”说着,秦凤舞从长袖中取出一份信放在桌上,沉吟道,“若真嫁不出去,我倒也甘心,有那样丈夫倒不如没有得好,你将这封合离书转交给爷,他若签了就好,不签我也得走。”
“我不依!”忽然从长廊深处传来一声清脆的嗓音,宫染夜脸色俱变,撩起长袍煞气腾腾的走了过来。
喜鹊寒颤了一下,赶忙上前几步福身恭敬道:“王爷。”
宫染夜黝黑的眼底淡淡扫了眼喜鹊,拂袖示意道:“退下!”
“是。”喜鹊低低应了一声,担忧的眼神看了眼秦凤舞,就走了。
“爷你来得正好,省得让人跑腿。”秦凤舞脸上表情随即放柔,磨着墨水,沾了沾毛笔连同桌上信封递给了宫染夜,声音极其温柔道,“签字吧!好聚好散。”
宫染夜瞳孔一紧,接过她递来的毛笔,笔尖一颤,落下一酡墨来,洇了信封。又见她面带微笑,恼得他将信封撕了稀巴烂,落得满地的碎纸片,这是她第二次提出‘合离’,这也是他第二次当着她面撕掉合离书。
“合离,你妄想!”宫染夜感觉肺都快气炸,快速噙住她下颚,深黑的眼眸逼视着她,眼底闪过一抹犀利的寒光,“你我竟已拜了天地,圆了房,又如何能合离?秦凤舞,我决不合离。”
“不合离?”秦凤舞眉尾轻挑,接触到他那决定的眼神,神色和往常一样镇定自若,目光却有些暗淡,“你我二人本就不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若不是凌家小姐有心设计,我怎会受屈当你个三房姨太?什么三世宿缘?依我看是三世孽缘,也不知我上辈子欠了你什么,这辈子跑来这个鬼地方受这份罪。你如今已贵为王爷,却到处沾花惹草,听听外头人是怎么说的?不说你不是,偏说我是个软柿子任由你欺。对我好一阵歹一阵,我秦凤舞不稀罕,这婚你不离也得离。”心一横,放下了狠话,头也不回的往回屋的方向走去。
望着秦凤舞离去的背影,宫染夜身影微微一滞,一阵清风微微吹拂而来,那头漆黑长发遮去那双压抑不住黯淡的眼眸,薄唇紧紧抿着。坐在冰冷的石凳上一言不发,稍稍出了神,这并不是真正的他……
想到这,从长袖取出香囊,嗅着香囊淡薄的清香,心着实酸痛,这是娘的味道。
小丫鬟提着灯笼打更,正巧路过后花园,瞧见二公子独自一人坐在凉亭处,见天色已晚,悄悄走上前几步,福身道:“王爷,天色已晚,早些休息吧!”
“滚!都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女人没一个好东西!”声音透着淡淡疏离感,一双狡长眸底淡漠如冰逼视着小丫鬟,不知为何一股怒意直冒在头上,将摆放在桌上的古琴拂手摔在地上,古琴当即折成两半。
在他囚牢般的眼神的逼视下,小丫鬟的眼睛犹如惊慌的小鹿眼睛,流露出惊恐和畏惧,来得偏不是时候,正碰到王爷枪口上。颤抖着声音,弱弱道:“王爷息怒,王爷息怒。”赶忙转身不敢多逗留。
脑海里闪过一张慈祥的笑容,他面色狰狞,眼底像似涌出什么,瞳孔一紧,两横冰冷的泪水渐渐滑落在下颚,狠狠咬着下唇,痛苦的扯住头发,“娘。”这既又熟悉又陌生的称呼不断涌入心里。
现在的他好比一具空壳,摆在面前的感情他却退缩,就像当初他放开柔儿的手,害怕得到的感情却忽然间从他身边消失得无影无踪,那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清晰……
自从柔儿走后,他不再相信爱情,只会一昧的玩弄感情,渐渐成了习性。
竟然她要走,也罢!
一回到屋子,秦凤舞从柜子取出几套衣裳和首饰盒一一放入包裹里,急得喜鹊不知所措,当下灵机一动趁她不留神下夺过包裹,死死抱在怀里,不依道:“秦姨娘,这是何苦呢?您这一走,太妃若问起话来,您叫奴婢怎么向太妃交代?”
“如实交代。”秦凤舞心意已决,任由喜鹊怎么劝说,她决定的事是不会改变,挪开莲步逼近喜鹊,神色极为严肃,“你无需劝说,把包袱给我。”
喜鹊步步后退,直至逼近门边,将包袱揽在身后,压抑住心中慌张,那双清澈的眼眸勇敢的直视着秦凤舞,“姨娘您就听奴婢一句劝,奴婢知道您受了屈,心里不好受。可毕竟婚姻不是儿戏,姨娘若真跟二公子离了,只怕会误了姨娘一生。”
“秦公子这边请,想来这会子秦姨娘应该在屋里头。”小厮身穿深蓝色素衣一路上领着秦槐玉从东苑绕进了南苑,长廊两旁的灯笼随风摇曳着,显得格外寂静。
秦槐玉穿着墨色的缎子衣袍,袍内露出银色镂空木槿花的镶边。腰系玉带,手持象牙的折扇,着实像是换了个人似的,身后两名家仆手各提着礼聘紧跟其后。
宫王府差人去秦府稍了口信,秦老爷得知宫染夜被奉了爵位,因路途尚有一段路程,都七旬的人哪能承受得起长途跋涉,五爷曾去过齐国,便托五爷代替他老人家送礼聘道贺。五爷自当乐意,一则是托父亲嘱咐前来道贺,二则是来看望秦凤舞在王府可过得安好。
一路上小厮带他饶过不少地方,王府果然气派,内设奢华优雅。天边晚云渐收,淡天琉璃,芙蓉月下妖娆,浅红色的新蕊,假山逼真,湖水似如面镜,是块清闲的宝地。
现如今宫染夜当上了王爷,六妹深得公婆喜爱,想来用不了多久王妃位置非他六妹莫属。这是他个人看法,却不知这会子秦凤舞正闹着要合离,偏这时候五爷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