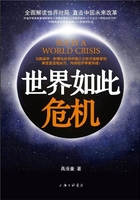第 47 章 (1)
正在图书馆憋论文题目,忽然接到钟汶的电话,我接起来的时候,她在那头兴奋的叫了一声:“我就估摸着你差不多要回来了,这阵儿干嘛呢?”
我跟她表示了一下论文压力很大,但她对我说什么根本不感兴趣,话没说完,就高分贝打断我:“去年几个同事给你买了件礼物,结果没想到你跑得比兔子还快。今天有空么?到公司来拿一下吧。”
听到“公司”两字,我顿时抽了一口凉气,讷讷不知道怎么回答。
钟汶叹了口气,说:“你放心,林墨淙不在。其实从你离开以后,他就很少来公司了,明眼人都知道是咋回事。这几天我手里有个项目很急,不能给你送过去,没事你就过来一趟吧。”
站在公司楼下的时候,已经到了快下班的点。根据我的经验林墨淙是不会在这个时候来公司的,所以我决定利用这个间隙,速去速回。
但我算计好了一切,却没把钟汶储蓄了一年的八卦能量给算上。一见面她就拉着我不撒手,说晚上要加班,正好让我陪她吃晚饭。然后四十分钟的晚饭时间只有一个中心思想:早知我如此暴殄天物,当初她就应该撸袖子抢上。我也不想解释那么多,装傻打了几个哈哈敷衍过去。
出饭馆出来的时候,钟汶就匆匆跑回公司大楼里加班去了。天色变得有些阴沉,这盛夏的气候果然叫人摸不着头脑,看着是要变天了。在我奔向公车站的半路,雨点已经狠狠的砸落到我的头上。
雨大得我已经基本看不清两米以外的东西,只是狼狈的抱着那份包装精美的礼盒低着头一个劲沿着路边往前跑。正想着胜利在望车站就在前方,却忽然额头一疼,好像是撞到了迎面而来的一个人身上。我正要道歉,却手腕一紧,被人扯到一把雨伞下面。
“怎么也不知道找个地方避一避?这么跑着算怎么回事?”
那个声音一传进耳朵,我便瞬间如同被点了穴一般,全身都不能动弹。还在抹水珠的手僵在额头上,如果可以,我实在很想一辈子都这么挡着。
面前那个人却轻轻把我的手摁了下去,用一条灰色的手帕缓缓在我额前的头发上擦拭着,熟悉的淡香从手帕上散发出来,飘进我的鼻子里,弄得它莫名有些发酸。
有的人,原以为再遇见的时候,要么天崩地裂,要么天打雷劈,反正总以为自己心里肯定承受不了那样的骤变,所以变着法的躲。但生活毕竟不是灾难片,真要遇见,也就这么遇见了。天也没崩,地也没裂,即使打雷闪电,还都没落到我身上,我还在坚挺的站立着。
任他擦了好一会,我才反应过来,这样亲密的动作现在在我们之间,实在有些不应该。便慌忙的推开他的手,说:“没事没事,两颗雨,死不了人。”
林墨淙的手顿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有再凑过来,只是把手帕塞到我手里,问:“你要回学校?”
我呆呆握着手帕,点了点头。
林墨淙说:“我送你回去。”
我忙说:“不用不用,前面就是车站了,我自己……”
话还没说话,一个轻柔的声音就替我完成了拒绝的程序:“墨淙,你怎么突然就下车……”我的身子震了一下。刘芊娜的声音真是很久没听到了,不过每一次听到时那种由衷的恶心真是一点没变,熟悉的很。
刘芊娜在看见我的脸时,很明显的愣住。我想她一定在想这满天的雷怎么还不把这妖精劈死,留在世上除了碍眼真是什么功用都没有。我之所以能如此细微的揣摩到她表情里的每一个意思,是因为我对她也是这么个想法来着。
刘芊娜撑着伞缓缓走到林墨淙旁边,对我浅浅一笑:“程小姐,真巧!你念书回来了?”
我功力确实不够她深厚,我实在笑不出来,只能轻轻点了点头,低声应了句:“啊,回来了。”
刘芊娜对林墨淙说:“快点走吧,Steven的补课时间要到了,他在车上等得都有点急了。”
恍惚之间,我真觉得我在看着一家三口的温情戏码。不知道是不是流到眼里的雨水太脏,我觉得眼角有些发酸,却也不敢伸手去抹。我绝不是被那妖孽刺激了,绝对不是!
不等林墨淙开口,我说:“孩子上课要紧。那我就先走了,你们忙。”
林墨淙又要伸手过来抓我,我抬起头,以一种拒绝的眼神定定的望着他,轻微摇了摇头。我不愿意同刘芊娜在同一个车里呆上一秒钟,死都不愿意。
还好,林墨淙应该是接收到我眼里的意思,他已经微微抬起的手终于还是放了回去。我心里有一种既如愿又失望的复杂酸涩,根本来不及细品,低低说了声“再见”,然后就从他的伞下冲了出去。
我不敢回头看林墨淙是个什么表情,只是埋头往车站冲。心里忽然难过得想死,为什么再见面,人家还光鲜亮丽的,我就不能是一副意气风发的模样?明明之前还人五人六的蹦跶,偏偏在被这莫名其妙的大雨浇这么狼狈的时候,就让他撞上了,这样子要表明我过得很好,连鬼都不相信。苍天,你是故意在耍我么?
我愣愣的等在公车站旁,忽然觉得有人在拉我的裤子,回头一看,竟是刘觅忽闪着他的大眼睛在看着我。一年不见,又长高了些,但头发表情一点没变,还是那个被我抱在怀里勒得喘不过气也不吭声的死小子。他说:“陈,爸爸叫我把伞拿给你。”
我忽然再也克制不住,俯下身去一把将他抱在怀里,眼泪顺着湿湿的脸颊就那么淌啊淌,酣畅得不行。
也不知道抱了多久,刘觅在我怀里动了动。我忙抹了眼泪,把他放开。顺手捏了他脸蛋一下,故作轻松的问:“怎么样,这一年过得还好么?”
刘觅吸了吸鼻子,说:“陈,你要能回来陪我,多给我带着小人书和吃的,我会更高兴些。”他的中文倒真是流利了不少,发音也正了许多,专业老师确实比我这个野狐禅高明多了。
我苦笑了一下,说:“这可有点困难……”
刘觅回头看了一眼,转过来对我说:“我要去补习了。陈,爸爸说我可以给你写信,你等着,我一定会写给你的。”
我用力点了点头,多好的孩子,可惜了妈是个妖孽。
刘觅又说:“但是你要给我回信。”他仰起头,一脸严肃:“你要不回,我就再也不给你写了!”我抱了他一下,笑着说:“放心,我一定回。”
刘觅把伞塞进我手里,举着一把小伞跑了。我扫了一眼,那就是刚才林墨淙举着的那把。鼻子又有点酸。
我知道,或许我的人生,又要开始混乱了。
世界上有一种生物,经常口是心非,最爱胡思乱想,迷恋自我矛盾,时时悲天悯人,这种生物就叫做女人。
如果这种生物还一个不小心有那么点爱好文学,曾经读过一两本启蒙大师什么千千结剪剪风之类的言情名著,且尚处于可以春心荡漾而不用背负老不正经这类骂名的年龄段,就可以称这种生物为文学女青年。普罗大众完全不要浪费精神去揣摩文学女青年们在想什么,因为她们的忧思可以一日千里,瞬间就漂洋过海杀去了另一个半球,光速都要在这样的神行面前捂脸锤地。
尽管我不想承认,但我确实是一个文学女青年,还是一个二十多岁才开始谈恋爱的文学女青年。用吴妮的话来说:这样的女人很可怕,会把矫情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一点,终于在林墨淙正式邀请我共进晚餐的时候得到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