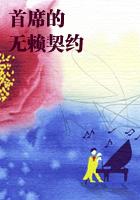王校长心里明白,按照芳菲的性格和做事方式,她应该不会撒谎,只是这样一次次没完没了,实在让人心烦。
“我可以答应你。”王校长说,“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去把孩子处理掉。”
有人搀扶芳菲,芳菲抬起头,是王少寒的姐姐,王晓明。这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衣着可谓讲究,她露出对同性姐妹的怜悯,嘴角笑盈盈,话中藏着刀:“你一定会答应我父亲的要求,对吗?最好是立刻。”
立刻?
芳菲想的是立刻拿到钱,立刻赶回家,她一定要在手术前见到父亲。妈妈说过这种手术风险相当大,即使手术成功了也有可能是植物人,芳菲有很多话还想说给父亲听。
她没有站起来,继续乞求道:“可不可以让我先带钱给父亲治病,手术一完,我自己会处理这个孩子。”
“那可不行。”王晓明不假思索,“如果你耍花招,我们全家岂不是又被你愚弄?几个月后你大概会抱着孩子来我家要钱了。这次我陪你去好了,我们在医院解决干净,然后你就可以快点见到你爸了。”
“不要这么残忍。”王少寒听不下去了,他制止住姐姐,“我自己的事情我跟她去处理好了。”
他一边说,一边去伸手拉芳菲,芳菲厌恶的拂开他的手,死死盯牢他:“残忍!?如今你还懂得什么是残忍!”
尔后,她绝望的向王校长看去,希望他能网开一面。得到的回应却是:“把你家里那边的账户名称和号码写给我,我马上就派人安排。”
他默认了女儿的说法,要先去解决孩子,才能放她去见父亲。彼时的芳菲真是太笨太天真,真相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她,愿意拖下去,这么简单而已。
芳菲站起来,接过王晓明递来的纸笔,手一抖一抖,艰难的写下几个数字。
闭着眼睛都能写出那个账号,多少次跑到银行,将手里零零碎碎的钱汇入老家,她忍辱负重,咬牙坚持,是希望家还能存在,天不要塌下来。
晚上只有护士值班,主治大夫不在,王晓明只能跟护士预约第二天清早。
芳菲忘记了那一夜是如何度过的,雪莲在一旁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没有得到一点有用的信息。
第二天清早,芳菲与王晓明如约见面。
在去医院的路上,王晓明一边开车一边腾出一只手来拍拍芳菲,安慰道:“别怕,很快就好。”
芳菲跟王晓明,象是借债人跟债主,债主的一点安慰辞令,给了负欠者不实的幻觉,她不想放弃希望,一路用不同的方式哀求。
“我的父亲危在旦夕,我真的很想先回去看看他,能不能回来再做手术?我保证不会留下这个孩子,你想想,我怎么可能留下?”
……
“医生说一定要先吃消炎药再做手术,我不太懂这些,你比我年长,能不能让我等几天?”
……
“我求你,让我见见我父亲吧,我爸爸他……”
……
芳菲记得,那张脸一直没有看她,漠然的开着车,惫赖以对,芳菲苦等她给一个交待,她只字不提,一直开到医院。
她眼的余光,同情又鄙视,看透了芳菲这嫩鸟的形容,一览无余:这个女孩,为母亲卖身,为父亲又来打掉自己的孩子,这么小的年龄,无非全是为了钱。
为了钱做这些就是贱,贱就是贱,粉雕玉琢,还是贱!
她在医院大方地楼上楼下跑,交了各种费用,极力说服医生无须再走消炎过程,就在今天解决,她谎称是芳菲的姐姐。
如此残忍的姐姐。
伤害最小的手术是的无痛可视人流,手术费两千五。
“姐姐”为她选择的是几百块的最普通的方式。她很明白,医生会将冰冷巨大的器具捅进芳菲体内,将孩子狠狠捣碎,再刮落出一片血肉模糊。
芳菲在手术室里疼的撕心裂肺,却没有出一声,痛到极点的时候产生幻听,她听见父亲的声音不断在耳边呼唤:“小菲,我的孩子,你受苦了,爸爸都知道,都知道……”
医生做完了,叮叮哐啷的收拾着夹子、镊子等硬冷而巨型的手术器材,一边去旁边消毒洗手,留芳菲一个人惨白着脸光着半个身子半躺在那里。
看芳菲半天没有动,一个护士冷冷的呵斥道:“快点起来穿衣服,晾在那里给谁看?”
每天有那么多鲜泽年轻的身体在这里遭受着炼狱之苦,护士小姐们恨这些女孩不懂得保护自己,根本不值得同情。
芳菲艰难的自己起来,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她慢慢挪下来,想弯腰把裤子提上,却完成不了这个动作。
腰变成了钢筋,直直向上,稍有弯曲,便要断裂,芳菲默默的流着眼泪,心想:“一定是报应,我刚刚做了谋杀者,杀死了我的孩子,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承受一辈子的疼痛。并且无任何尊严可言。”
她任由自己站在那里,光着腿,手指无力的扶着那略微发黄的手术皮床,一个新来的小护士实在看不下去,极不耐烦的胡乱帮她提上了裤子,里面内衣皱成一团,护士动作的粗鲁象是刀子一样又将芳菲的内里砍杀了一遍,她咬着牙齿屏主呼吸,很怕自己倒了下来。
芳菲缓缓的迈出手术室的门,扶着墙壁向前挪,小护士又极其不耐烦的搀了她两下,对着外面走廊喊:“家属呢,家属,来扶一把!”
又转头大声问芳菲:“你姐姐呢,刚才不是你姐姐陪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