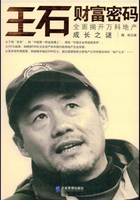芳菲没有理,自己朝前走,小护士没面子,对着芳菲的背影小声说:“活该受罪,让你再风流。”
芳菲抓住旁边长条椅子背跌坐下来,闭上眼睛呼一口气,觉得自己身体轻飘飘的,疼到极点原来是这样的感觉:很冰很冰,浑身冷的发抖。
她默默向已经消失了的孩子忏悔:“我没有想过要做妈妈,请你原谅我,如果用你可以换得父亲的生命,我只能舍弃你,求你原谅,求你原谅……”
眼前浮现父亲的笑脸,她不敢多做停留,缓缓走出医院门口。
凉风吹进芳菲的脖颈,把心田都吹的荒废了,长出了漫漫荒草,满眼都是寂寞和萧条,一望无际的萧条。
来到报刊亭,她拨了家里的电话,立刻有人接起来,是芳菲的小姨:“你妈妈在医院,让我守在家里等你电话,孩子,你妈妈光落泪,说小菲已经给家里寄了十多万了,要不是你,家早垮了,你快点回来吧,把那个借给你钱的男朋友也带来,跟你爸爸见一面,然后就安排手术了。”
“哎。”芳菲只说了这一个字就挂了电话,实在没有力气再说别的。自己叫了一辆出租,勉强把自己送回出租屋,雪莲正在门口翘首盼望,看见她的样子大惊失色:“你去哪里了?脸都变成白纸了,你去医院了?”
芳菲一句话也来不及说就晕倒在了地上。
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上。她环顾四周,正在自己的小屋,身下舒服了许多,有人为她添了一张床,陈正东趴在床边睡着了。
雪莲不在,一定是去上班了,桌子上有汤,冒着微微的热气,汤盘边上垂着一个鸡头,芳菲心下温暖,一定是雪莲在这个小屋子里,用电磁炉炖了几个小时才精心熬制好的。
芳菲伸手去摸闹钟,陈正东就醒了。
她开口问:“我爸爸怎样了?”
“还不知道。”陈正东说。他怎么可能知道呢。芳菲挣扎着要起来,有气无力的说:“我得回水秀,我爸做手术呢。”
“你的情况,我和雪莲都猜的差不多了。”陈正东说,“我陪你去吧。”
“你不上课吗?你好象为了我的事情总旷课。”芳菲看着眼前的男孩子,他在竭尽全力的为她撑起一片天空,可是因为没有独立,他能做的也就是如此了。
到现在也弄不清陈正东跟自己到底算不算情侣,更多时候感觉两人如亲人般熟悉,旧鞋子一样合贴,更象是莫逆之交。
“不要紧,我们坐飞机赶回去,这样快一些,我们应该可以买上中午的机票,至于齐墨这边的事情,等我们回来再处理。”陈正东说,又加一句,“以后不要什么事情都一个人做决定,也不要闷在心里,雪莲是个很好的朋友,你该信任她。”
芳菲点点头,多么喜欢这种感觉,有人为她安排好事情,她只需要象一个小孩子一样,牵着大人的手,一步一步跟着走就好了。
她乖乖的下了床,陈正东打来清水让她洗脸。
坐飞机,好奢侈,芳菲犹豫一下,机票一定是陈正东解决了,债务越累越高,还有点怕自己在飞机上轰然消失,但又立刻安慰自己,可是没有办法,时间不等人了。
没有来得及给家里打电话,也没有给雪莲留口信,陈正东领着芳菲到机场领了票,匆匆的向水秀飞去。
在飞机上,芳菲坐定吃完发放的餐盒,连桔子和牛肉干也不放过,她想在回家前吃饱些,好让父母看起来她比较正常,又将上下嘴唇抿起来吸个不停,这样可能会吸出点血色。
她想好了该怎样安慰妈妈,怎样照顾爸爸,她可能会留下来待一段日子,直到父亲康复出院。
飞机在云层上面飞翔,芳菲看着外面强烈的阳光,心生恍惚。
这两年每一步都走的迷迷糊糊,很努力但仍然狼狈不堪。想要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侥幸,真可谓千锤百炼,非常艰难。
她想要重生,把过去的一切狠狠抛掷脑后,不要再想了,只要父母都能建在,比什么都重要,自己还年轻,要坚强的活下去,努力使父母过的更好,当然也好努力还债。
她欠了陈正东太多,她将来一定会还他的,无论用何种方式。
飞机落地时候遭遇气流,上下颠簸,毕竟是第一次,芳菲有点怕,闭上眼睛,抓紧了陈正东的手。陈正东跟她对视,笑笑,让她放松。
芳菲眼睛湿润,默默讪笑,笑出声音,忽然说:“我不能死,如果我死了,谁来替我还你的债呢。”
芳菲变的敏感许多,无论如何要保住自己性命,逃避一切祸患,躲避所有危险,但凡此类都让芳菲有点神经质,一切都为了活下来,要抗争,要延长父母寿命。
陈正东闻声兀自懊丧,颓然感觉到悲哀,他竟然不能给予心爱的女孩一些安定和保护,芳菲还时时刻刻觉得欠了他的,他真为自己感到汗颜。
他要让自己迅速成长,早点变成一个男人,一个有担当有主见的人。
芳菲跟陈正东奔到水秀,日照渐渐西移,人也一寸一寸暗淡下去,芳菲急急赶路,额头冒出细汗,她很怕黄昏最后一线残阳收尽,象悲惨的电影,只怕人也随之形骸俱散了。
走进家属大院之前,她努力让自己步子更平稳些,刻意翘起嘴角,想好了见面后的说辞,要微笑,要放松,要让父亲安心手术,芳菲给自己打气。
身体虽然有所恢复,但还极其虚弱,下身随时都有被撕裂或者被剪开的感觉。
进了小区渐渐放慢脚步,气氛不对,环境也不对,来到自家楼下,摆放着许多花圈,白色的挽联随风飞舞。
芳菲驻足,一步也无法向前了,那白条黑字写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父亲的名字?!
难以置信,但无可置疑。





![都是吻惹的祸[完]](http://c.dushuhao.com/images/book/2020/03/31/10370668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