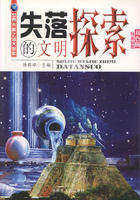“这是好事啊,恭喜您又添了孙子。”雪晴忙去柜台里取了一贯钱出来,递了过去,“这是我们给这没出世的小弟弟或者妹妹买衣衫的。我们买,怕不合穿,三婶帮着我们买了带去吧。”
刘三婶把铜钱推了回来,不肯收,“这不行,这不行,这么多钱,哪里使得。”
子容在一边道:“三婶,您就别客气了,这是我爹娘的心意。”
刘三婶见他这样说,才不再推,“我们这一走,少刚一年两年,长了就不知到什么时候了,我们这老房子,都是土堆出来的,哪经得起这么荒着。久了没人住,这墙都要垮。”
雪晴点了点头,“那倒是,这些老房子的确是要人随时整理着才结实。”
刘三婶停了停,看了看手里的铜钱,有些不好意思开口,经不得雪晴催,才道:“我们听说你们想再租间铺面,我们茶水铺与你们是门挨着门,再加上你们为人又是我们信得过的,所以我们想……”
三婶话说到这步,其间的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了。
雪晴在桌子下面捏了捏子容的手,她们早听说三婶他们要走,茶水铺也一直想盘出来,只是他们总认着自己铺子这地头好,价钱抬了又抬,要求也多,这不能改,那儿不能动的,一直没人肯接,反而得罪了不少人,背地里没少骂他们掉进了钱坑里,做梦都想着钱。雪晴他们也就琢磨着寻个时间去找他们说说,让他们把价钱降些,也不必有意压价,只要合了这街上的行情,就盘下来,一时间还没抽出时间去,他们倒先一步找来了。
子容笑了笑,“三婶,您的意思,我明白,可是你看我这做染坊生意,您门口那些炉子不合我们用。”
茶水铺门口摆了一排五六个烧水的炉子,熏得门口的墙一摸一手黑,前几次有人去看铺子,人家一看,就说,这墙得重新粉刷干净,这些炉子要拆掉。
刘氏夫妇不肯,说要粉墙,让他们自己粉,这炉子不能拆,他们也是怕万一以后回来,另买炉子又要花钱。
他们开的价本就极高,这墙还得自己粉,而这一排炉子把大门都挡了一半,进出还得侧个身,一不小心就蹭一下摆的黑。别人自然不干了,甩了袖子走了。
现在子容一提炉子,就扯到他们的心结了,“可是这炉子可是我们的老本啊,以后回来没准,还得用呢。”
雪晴扁了扁嘴,“三婶,我说话,您别不高兴,有你那几个炉子在,这铺面就没人肯租。象我们进进出出的布,光光鲜鲜的,万一从你那门口过,一个身子没侧好,在你那些炉子上揩那么一下,这布就得我们自己买下了,赔了钱不说,这信用也贴进去了,这买卖可就亏大了。”
刘三婶微低了头,斜了一眼丈夫,“你说呢?”
刘三叔向来没多少主意,看向子容,“子容,你看呢?”
子容轻咳了一声,有些为难的样子,“三叔,我也很想盘下你那铺子,和我们门挨门的,多方便啊?不过雪晴说的也都是实话,所以……我们也为难啊……”
刘三叔心痛的脸上抽了好一会儿,“那些炉子不拆,真不行?”
子容点了点头,“不拆,那铺子真不能要。”脸上神情没有一点含糊。
“哎!”刘三叔重重的叹了口气。
雪晴又在桌下捏了捏子容,“还有啊,三叔,三婶,不是我说你们,你们那价真的高得离了谱,你看我们比你们那儿大了两倍有多,在我们没买下来之前,才五十两银子一年,您那就要六十两,而斜对面也放了风说要把铺子盘出来,比您们那还大些,也就十几两银子,您说盘你这一间,可以盘下对面几间了……虽然门对门方便,便走两步,一年就少几十两银子,谁都愿多走两步。”
刘氏夫妇经过这些日子,也知道他们的价格要的太高,而媳妇那边又快生了,时间也不再等人,这不盘不行了,“你看多少合适?”
子容心里早有了打算,却不马上回答,佯装想了想才道:“您们看这样行吗?我也不压你们的价,虽然你们这铺比对面小些,但我们也图个方便,也按他们给出来的价钱给你们,二十八两银子,这炉子,我们帮你们拆,拆了也不丢,堆在屋后檐下。这东西也没人会偷,如果丢了,我赔你们,等赶明儿你们回来了,请个瓦匠糊糊,就能用,那黑压压墙,我们请人给你们清干净了,门口我们也重新装,这钱我们出了就是了,你们看这样,成吗?”
“二十八两?会不会少了点?”刘三叔迟疑着。
雪晴笑了笑,“如果您二位觉得低了,我们也没办法,光粉你们那黑炭一样的墙就得花不少的钱。再涨价,不如要对门的,不就过个街吗?叫伙计跑一跑就是了,那边只要装个牌匾就能开张做生意,我们也省心。”
刘三婶察颜观色,知道这价是抬不上去了,再说他们也是听说对面放了风盘铺子,价钱也是她去打听过的,也的确是二十八两,所以这才巴巴的拉了丈夫赶着来拦下子容他们,万一他们和对面一交涉,再压压价,就盘下了,那他们这铺子一时半会儿,又的找不到东家了。
也在桌下拧了还想再说的丈夫,“二十八两就二十八两吧,那些炉子,你可要帮我收好了,那些可是你三叔三婶的命。”
雪晴笑道:“放心好了,我包给您收得好好的,一块泥都不会少,少一块泥,我就削块肉给您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