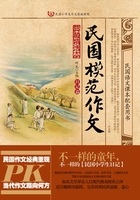雪晴觉得他真是没趣,以后肯定沦落成一个钻在钱眼里的铜臭商人。
心里嘀咕归嘀咕,仍是收拾了东西,关了铺子,前往马家村。
雪晴看着眼前的小河沟,揉着已经走得酸痛的膝盖,秀眉拧在了一块,“这一会儿功夫怎么就涨水了,刚才还能看到垫脚石。”
子容左右看了看,也没有地方可以垫脚,要过小河,只能趟着水过了。
放下手里的染料袋子,脱掉鞋子,挽高裤脚,微蹲下身,对身边的雪晴道:“上来,我背你过去。”
“我自己能趟过去。”雪晴弯下身,脱了鞋袜,纤细白嫩的小脚上起了好几处水泡,泡得老高。踩在鹅卵石上,水泡顿时崩破了一个,疼得她吸了口冷气。
子容抓起她的脚,看着她脚上的水泡,心痛了,一个姑娘家走了这许久的路,真难为了她,拦在她前面,“雪水化了不久,这水凉,你踩这冷水,别落下什么病根来,快上来。”
“你趟不是也凉吗?”
“我一个男人,怕什么,哪来这么多磨蹭,叫你上来就上来。”
雪晴脚上实在痛,又经不住他催促,伏上了他的后背。
他比同龄少年高了许多,刚捡他进门的时候,身上有伤,加上没得吃,看似单薄,这些日子下来,虽然没什么好吃的,但总算是填得了肚子,加上他一直在练武,而染布又尽是粗重活,他现在掩在布衫里的身板硕壮结实。
或许是他身上有许多伤疤的原因,他哪怕烤在炉子边染布,也从来不光着身子。
雪晴俯在了他背上,手扶着他厚实的肩膀,才知道他竟长成了这样。
他的体温隔着衣衫传来,雪晴脸上微微发烫,有些羞涩。
子容将自己的鞋子递给她拿着,站直了身,将她往上耸了耸,找到最佳的位置,拧起地上的染料袋子,小心的摸下了小河沟。
小河沟的水虽然不太深,但也没过了膝盖,有点刺骨的寒冷。
过了河他也不把她放下来。
“子容,你放我下来,抹干了脚,把鞋穿上,别受了凉。”
“这点凉,哪能就凉着我了。爹娘没收下我的时候,下大雪,也只有那么一条破单裤,那才叫冷呢。”子容又将雪晴往上耸了耸,“碍,话说回来,如果那晚没你给我的那个红薯,我可能还挨不到你下门板。”
“你还记着呢?”雪晴想着那晚,他在门外蹦达的模样,心酸中又有些好笑。
“怎么能不记着?我得记一辈子。俗语有说,受人点滴之恩,必定涌泉相报,何况这还是救命之恩。”
雪晴咬着唇瓣,抿嘴笑了,“那你也放我下来,你走了这许久的路,也累了。”
“不累,你脚上全是泡,也走不快,回去晚了,娘又该担心。”子容看了看天,太阳已经快没入西山,更加紧了步子,免得等天黑透了,在前面林子里遇上狼。
“子容,你说咱爹的腿真能好吗?”在医学并不发达的古代,再加上又是偏远的小镇,也没什么好大夫,这伤筋动骨,也实在不是小病。
“准能好。”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爹是好人,还得等着赶明享我的福,这腿怎么能不好。”
“你这是什么歪道理,再说了,爹以后也是跟着我的,怎么能享你的福。”
“嘿嘿……我说享我的福就会享我的福。”子容傻傻的笑着。
雪晴虽然觉得他的话纯粹没有依据,但心里却是甜蜜蜜的,“明儿,我也帮你一起染布。”
“你又不会,染啥布。”
“不会可以学啊,我学会了,多个人手,你和根儿也能轻松些。”自从有了子容和程根,张师傅月钱虽然涨了,却做起了甩手师傅,每天关了门调好了色,余下的重活全丢给子容和程根,他自个就到处听戏,逛青楼。
陆掌柜伤了腿,不能出门。
但凡是来染布的总要看见子容,心里才踏实,所以摊子上也里缺不得子容。
这样一来,子容要去摊铺上接生意,回了家还要染布,里里外外的忙,没有片刻的空闲。
所以,虽然雪晴每天守着摊子,程根帮着跑腿送料子,但大大小小的事,始终是离不得他。
别看他随时乐呵呵的,但雪晴哪能不知道他是咬紧牙关硬撑着的。
但这么个累法,铁打的人,也吃不消。
雪晴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想搭把手,他又说什么也不让。
“那些全是粗重活,一个女孩家,学那些做什么,有我和根儿足够了。”
“大男人主义。”雪晴撅着小嘴,小声嘀咕。
“你说啥?”他不懂什么是大男人主意,以为自己没能听清楚,侧过脸来问,残余的夕阳给他的侧影镀上一层金光,越发显得俊朗。
就连以前她们学校,被所有女生追捧的万人迷,也不及他十分之一好看。
“没啥。”这些日子相处下来,雪晴知道他虽然好脾性,但认定的事却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说不让她学,就不会让她动手。
春去秋来,转眼一年过去了。
永生染坊的生意在子容和雪晴的张罗下红火起来,凑了钱盘下了隔壁家快要倒闭的染坊商铺,总算是有了自己的铺子,不用守着那个一下大雨就得抱着布料,四处乱躲的小摊子。
他们自己捣鼓着粉了墙,又将原来的旧家俱重新漆了遍。
破旧的小铺焕然一新。
有了铺子,来往的客人也就更多,虽然对对面‘福通染坊’的生意影响并不太大,但王掌柜心里已经不大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