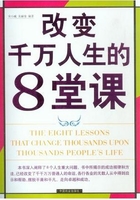染布的事,雪晴也帮不上忙,只得答应着去洗漱。
收拾完了,刚喝上两口粥,听外面‘哐当’得一声,抬头见张师傅把装热水的锅子给抛了,热水泼出来,差点烫了子容。
程根小心地缩在一边。
雪晴心里咯噔一下,站了起来,要往外跑,陆太太将她拽了回去,小声道:“别去,去了只能给子容添乱。”
外头张师傅骂道:“烧的水都能烫猪去毛了,能染绸子吗?”
子容脸上没有一点怨气,捡了锅子,“我就这就重烧。”
张师傅又骂:“染料不要钱?柴火不要钱?有你这么败家的吗?”
“我一会儿就去山里多打点柴火回来。”子容仍恭恭敬敬捡了锅盖,去重舀水。
张师傅不饶人,瞪着子容的背影,道:“陆掌柜捡了你这么个败家子回来,真是上天不开眼啊。”
雪晴看不下去了,要往外冲。
陆太太死拉住她,“雪晴,你真不能去。刚才子容就吩咐过,说今天那边不管什么事,都别去劝,别去求。”
“那条老狗疯了吗?”雪晴气得脸青,哪肯依,“不心疼子容,还心疼那些颜料呢。”
“子容说了,张师傅叫用的小锅,就说明他不会糟蹋太多染料,他才涨了月钱,还指着挣钱呢,不会把你爹逼得没钱过下去。”
“我心疼子容。”不过这话,雪晴只能在心里叫,不敢当着母亲的面叫出来,毕竟这是一个封建社会,这话不能从正经女人嘴里说出来,她可以不要脸,但不能不为爹娘考虑,“难道就让他这么疯下去,烫着子容怎么办?”
“你去了,只能给张师傅火上加油,遭罪的还是子容。”陆太太也心疼,“我问你,昨天,你不是不又惹了张师傅了?”如果不是她惹了张师傅,张师傅也不能这么故意折腾子容出气。
“我什么时候惹……”雪晴想到昨天在摊子上,子容在她面前拦了一把,支她回来,明白怎么回事了,胸口有一团火‘腾’地一下燃了起来,骂道:“那条老狗,真是丧心病狂。”
陆太太看她脸色,也猜到些,皱眉,“我就知道又是你,赶紧消停吧。要想子容好过,就离张师傅远些,别在他跟前绕。”
雪晴心里委屈,闷坐下去,“咱就这么由着那老狗折腾啊?”
“别左一个老狗,右一个老狗的,姑娘家说出来,多难听?”陆太太叹了口气,也坐下,“慢慢想法子吧,张师傅一走,我们家也完了。”
“没有他,我就不信能饿死,我就是给人洗衣服,也不愿受这窝囊气。”雪晴红着眼。
陆太太又叹了口气,“可是这家染坊是你老爷留下的,不能让它就这么倒了啊。”
雪晴不觉得这么守着这染坊有意思,但是知道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执念,爹守着老爷的这家染坊,也就是爹的执念,默了下去,瞪着仍在那儿挨骂的子容,一定有别的办法。
陆太太也看子容,眼蓄了泪,“这孩子落在我们家,真难为他了。”
“他没到我们家,已经饿死了。”雪晴嘴硬,看着子容受气,心里跟刀割一样。
陆太太摇了摇头,“我总觉得子容是大户家流落出来的孩子,只是不知是哪家的孩子,没准哪天要认祖归宗的,到时想到在咱家遭的这些罪……唉……”
雪晴有些愕然,“娘怎么会这么认为。”
“你看他言行举止,多懂规矩,我们寻常家孩子,哪能有这么多规矩。”
“穷人家也有教的好的。”
“他能文能武,穷人家饭都吃不饱,哪能又学文,又学武?”
“可能是有机缘。”雪晴心里也有些迷惑,子容不管再累,每天只睡两个时辰,天没亮就在前头林子里练武,她虽然不懂武功,但看他打得极好。
除了练武,他还自己做了弓箭,练箭,他能在两百步外射中前方被风拂动着的杨柳。
她就懂箭术,也知道那叫百度穿杨。
跑货的货郎来镇子,他都会进山打猎,捕捉很难捉到的山貂,但并不卖钱,交给货郎,告诉货郎他想的东西,如果货郎带来他想的,他便会再给货郎山貂。
后来雪晴发现,他换的东西全是书,而且是兵书……
她曾打趣他,是不是想去参军打仗,他总笑着说,“哪能,只是觉得有趣。”
迷惑归迷惑,但她认得他时,他就是个叫化,打心里认为他就是个无家可归的叫化,也就没往心里去。
这时听母亲提起,这些不寻常便越加显得不寻常。
“你听他说起过去的事不?”陆太太白了女儿一眼,她平时这么聪明,到了子容这儿就迷糊。
“他……”雪晴答不上来了,除了刚醒那回,说了家里的事,再没提过。
“他不提,你也别问。万一那是人家心头的疤,你一问,就生生把人家的心头的疤给揭了。”
“嗯。”雪晴盯着顺服烧水的子容,恨不得过去踹他两脚,张师傅那点破手艺不学就不学,何必忍着受这气。
转念又想,如果母亲说的这些都是真的,他能文能武,又何必在这里受张师傅的窝囊气。
怎么想,都是母亲多心了。
“你赶紧吃吧,吃了去摆摊子,别在这儿看着。”陆太太知道女儿性子急,怕她再看出火来,万一按捺不下,又不知要惹出什么事。
“不吃了。”雪晴看着子容受气,心里堵得难受,哪里还吃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