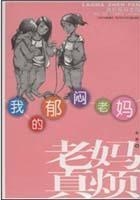所轻视的是中性以及阉割了的事物,所表彰的是机能完备的男人 以及妇女,
还将那号召叛乱的锣鼓敲起,与亡命徒以及密谋造反的人们共同逗留。
二十四
沃尔特·惠特曼,宇宙,曼哈顿的儿子,
肥壮,狂乱,酷好声色,能喝,能吃,又能繁殖,
他不是感伤主义者,从来都不高高站在男人以及妇女们的头上,或是同他们脱离,
不放肆,不谦虚。
将加到门上的锁拆下来吧!
甚至将门也自门框上拆下来!
如果有谁侮蔑别人便是在侮蔑我,
不管什么言行都最终归结到我。
灵感通过我汹涌澎湃,潮流以及指标也通过我。
我将原始的口令说了出来,我将民主的信号发了出来,
天啊!假如不是全部的人也能够相应的在同等条件下得出的东西,我绝对不会接受。
借助我的渠道所发出的是许多长久以来都很喑哑的声音,
历代囚犯以及奴隶的声音,
绝望的、患病的、盗贼以及侏儒的声音,
“准备”以及“增大”轮转不息的声音,
连接着星群的线索,子宫以及精子的声音,
被其他人践踏的人们对权利进行要求的声音,
畸形的、渺小的、愚蠢的、平板的、受人鄙视的人的声音,
空中的浓雾,转动着粪丸的甲虫。
通过我的渠道所发出的是那些被禁止的声音,
两性以及情欲的声音,被遮盖着的声音而我却将遮盖揭开了,
猥亵的声音则被我予以澄清并且转化。
我没有用手指将我的口按住,
我保护着腹部令它同头部以及心脏四周同样高尚,
对我说来性交同死亡一样并不粗俗。
我对肉体以及各种欲念都表示赞同,
视,听,感觉全都是奇迹,我的每个部分每个附件都是奇迹。
我的里外全都是神圣的,不管是接触到什么或是被人接触,我都令它成为圣洁,
两腋下的气味是比祈祷更为美好的芳香,
头颅胜似教堂、圣典以及一切信条。
如果我的确崇拜一物胜过另一物,那将会是横陈着的我的肉体或是它的某一局部,
你将会是我半透明的模型!
你将会是多阴凉的棚架以及休止之处!
你将会是坚硬的男性犁头!
在我地上帮助进行耕种的也将会是你!
你是我丰富的血浆!你那乳白色的流体是我生命中的淡淡奶汁!
贴紧其他的胸脯的胸脯将会是你!
我的头脑将会是你进行神秘运转的地方,
你将会是雨水冲刷过的甜菖蒲草根!怯生生的池鹬!看守着双生鸟卵的小巢!
你将会是那蓬松而又夹杂着干草的头,胡须以及肌肉!
你将会是那枫树的流汁,那挺拔的小麦的纤维!
你将会是那非常慷慨的太阳!
你将会是那照亮而又将我脸遮住的蒸汽!
你将会是那流着汗的小溪以及甘露!
你将会是那用柔软而又逗弄人的生殖器摩擦着我的风!
你将会是那宽阔而又肌肉发达的田野,是那常青橡树的枝条,流连在我的羊肠小径上久久不去的游客!
你将会是那我握过的手,亲吻过的脸,我所唯一进行过抚摸的生灵。
我溺爱自己,我包含很多东西,并且都非常香甜,
每时每刻,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令我欢喜得微微发抖,
我无法说清自己的脚踝是如何弯转的,也不清楚自己最微弱的心 愿来自哪里,
也不清楚自己所散发的友谊起因在哪儿,我为什么又重新接受了友谊。
我走上了自己的台级,停下来对它是否真的是台级进行考虑,
我窗口的一朵牵牛花所给予我的满足已胜似图书中的哲理。
竟然看到了破晓的光景!
庞大而又透明的阴影被小小的亮光冲淡了,
空气的滋味真是美好。
转动着的世界主体在天真的欢跃中悄然出现,汩汩地放射出一片清新,
起伏着倾斜着疾驶而过。
某种我无法看见的东西将色情的尖头物举了起来,
海洋一般的明亮流汁洒遍了天空。
大地同天空紧贴着,它们每天都连在一起,
那时候,在我的头上升起了涌现在东方的挑战,
用讽刺的口气笑着说,看你还能否做得成主人!
二十五
耀眼而又强烈的朝阳,它会多快便将我处死,
如果在此时我不能永远自我心上也将一个朝阳托出。
我们也要像太阳那样耀眼而猛烈地上升,
啊,我的灵魂,我们于破晓的宁静以及清凉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我的声音对我目力所不及的地方进行了追踪,
我的舌头一卷便将大千世界以及容积巨大的世界接纳了。
语言为我视觉的孪生兄弟,它无法对自己进行估量,
它永远向我挑衅,以讥讽的口吻说:
“沃尔特,你有足够的东西,为什么不将它释放出来呢?”
好了,我是不会接受你的逗弄的,你将语言的表达能力看得太重了,
啊,语言,难道你不清楚自己下面的花苞是如何紧闭着的吗?
在昏暗中等着,受严霜的保护,
污垢随着我预言家的尖叫声在退避,
最后我还是能够,能够将事物的内在原因摆稳,
我的认识便是我的活跃部分,它同一切事物的含义在不断保持 联系,
幸福,(请能够听见我说话的男女们今天便开始去寻找。)
我绝对不告诉你我的最大优点是什么,我绝对不泄露自己到底是 什么样的人,
请将万象包罗,但千万不要试图包罗我,
我只要看你一眼便能挤进你最为圆滑精彩的一切。
文字以及言谈不足以对我进行证明,
我脸上摆有充足的证据以及其他一切,
我的嘴唇一闭便令怀疑论者全然无奈。
二十六
我现在除去倾听之外不做其他的,
将所听到的注入这首歌,令声音向它作出贡献。
我听到鸟类的华丽唱段,成长中的小麦的喧闹声,
火苗闲嚼着舌头,正在煮着我饭食的柴枝爆炸着,
我听到了自己所爱听的人声,
我听到各种声音同时鸣响着,联合到一起,相互融入,
或是互相追随着,
城里城外的声音,白天以及黑夜的声音,
健谈的青年们同喜欢他们的人说着话,工人们在进食的时候放 声大笑,
友谊破裂之后的粗声粗气,病人的微弱声调,
法官的手紧紧攥着桌子,他那苍白的嘴唇在对死刑进行着宣判,
那些在码头上卸货的工人的哼唷声,那些起锚工人的合声哼唱,
警钟鸣响,大喊失火的声音,伴着警铃以及颜色灯光呼啸疾驶而来的机车以及水龙车,
汽笛声,列车渐渐靠近时所发出的隆隆滚动声,
在两人一排的行列前奏着慢步的进行曲,
(他们前去守灵,旗杆的头上还蒙着黑纱。)
我听到了低音提琴,(这是青年人内心的悲鸣,)
我听到了那装着键钮的短号,它快速地滑入了我的耳鼓,
它穿过了我的胸和腹,将阵阵蜜样甜的伤痛激了起来。
我听到了合唱队,这是一出大型的歌剧,
啊,这才是音乐——正合我的心意。
一个同宇宙一样宽广而又清新的男高音把我灌注满了,
他那圆形的口腔还在继续倾注,并且将我灌得满满的。
我听到那有修养的女高音,(我的工作又怎能和她相匹配?)
弦乐队领着我旋转,令我飞得比天王星还要远,
它自我身上攫取了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所怀有的热情,
它令我飘举,我光着双脚轻拍,感受着懒惰的波浪的舔弄,
我遭到了凄苦而又狂怒的冰雹的打击,令我无法透气,
我浸泡到了加了蜜糖的麻醉剂当中,我的气管受到了绳勒般的 死亡的窒息,
后来又被放松,得以体验这谜中之谜,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存在”。
二十七
“以随便的什么形式来出现。”那是什么?
(我们绕着圈转,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并且总是返回原地,)
假如发展仅止于此,那硬壳中的蛤蜊也便足够了。
而我身上的却并不是硬壳,
不管我是动还是静,我的周身全都是灵敏的导体,
它们将每个物体攫取,并引导它安全地在我身通过。
我只要稍动,稍加按捺,用我的手指去稍稍试探,便幸福了,
让我的身体同另外一个人接触便已够我消受。
二十八
那么这便是一触吗?我在抖颤中成为了一个新人,
火焰和以太向我的血管冲了过来,
我那靠不住的顶端也凑了过去帮助它们,
我的血以及肉发射电光来打击那同我自己没有多大区别的—个,
引发欲念的刺激自四面八方袭来,令我四肢僵直,
对我心进行压迫的乳房以求得它不愿给予的乳汁,
向我放肆地行动,不容抗拒,
就像是有目的地在剥夺着我的精华,
解着我的衣扣,搂抱着我那赤裸的腰肢,
令我于迷茫中似乎看到了平静的阳光以及放牧牛羊的草地,
毫不羞耻地将其他感官排除了,
它们为了同触觉交换地位而加以施贿并于我的边缘啃啮,
丝毫都不考虑我那将被汲干的力量或是我的憎恶,
对周围余下的牧群进行召集来享受片刻,
然后联合到一起站在岬角上对我进行干扰。
我的哨兵全都撤离了岗位,
他们令我面对凶恶的掠夺者束手无策,
他们全都来到岬角眼睁睁地看着我受难,并联合起来对我进行反对。
我为泄密者出卖,
我说话粗狂并且失去了理智,不是别人,我自己才是最大的泄密者,
我自己首先登到了岬角之上,我自己的双手将我带去。
你这险恶的一触!你在做些什么?我喉头的呼吸早已特别紧张,
快打开你的闸门吧,你已经令我无法经受。
二十九
盲目、蜜甜的,挣扎着的一触,藏在鞘内和帽内有着利齿的一触!
离开我时你竟然也会如此痛楚吗?
离去之后紧跟着的便是再来,不断积累下的债务必须被不断地偿还,
丰厚的甘露紧跟着便是更加丰厚的酬报。
幼芽将根扎下便能够繁殖,在路边生长得茂密而又生气勃勃,
那种伟然男子气概般的景色,壮硕而又金黄。
三十
全部真理都在所有事物内部静候,
他们不急于促使自己分娩但也不抗拒,
它们不需要医生的催生钳,
对我来说,极微末的也和任何事物同样巨大,
(比一次接触少或是多一些的又是什么呢?)
逻辑以及说教从来都不具有说服力,
黑夜的潮湿更加能够深入我的灵魂。
(只有能够在每个男子以及妇女面前对自己进行证实的才是实证,只有无人能够否认的才是实证。)
我的刹那和点滴令我的头脑清醒,
我确信湿透了的泥块将成为情侣与灯光,
一个男子或是妇女的肉体便是要领中的要领,
他们对于彼此的感情是顶峰也是花朵,
他们会自这个教训当中无限滋生,直到它可以创造一切,
直至一切的一切都令我们欣喜,我们也令它们欣喜。
三十一
我相信每片草叶都是星星创造的成绩,
一只蝼蚁,一颗沙粒以及一枚鹪鹩产的卵都同样完美,
雨蛙为造物者的一件精心的杰作,
蔓生植物悬钩子可以装饰天上的厅堂,
我手上的一个最狭小的关节可以令一切机器都暗淡无光,
任何雕塑都比不过母牛低头嚼草的形象,
一只老鼠这个奇迹足以令亿万个不信宗教的人愕然震惊。
我发现自己的身体里面包含着片麻岩、煤、果实、谷米、长须的苔藓以及可口的根芽①,
遍体粉刷着的走兽以及飞禽,
满有理地将身后之物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但在愿意时又能够召回任何一物。
超速奔跑或者羞怯都是徒劳的,
火成岩因为我的来到而将它们那古老的烈焰喷射是徒劳的,
爬虫缩避在自己已被碾碎的骨粉下面是徒劳的,
事物远远站在边上以千变万化的形体来出现是徒劳的,
海洋在深渊里潜伏,怪兽藏起来是徒劳的,
秃鹰以及苍天住到一起是徒劳的,
蛇在藤蔓以及木材之间滑行是徒劳的,
麋鹿躲藏到树林深处是徒劳的,
有着利喙的海鸟远远北航至拉布拉多是徒劳的,
我急忙跟上去,直上到悬岩裂缝中的巢穴。
三十二
我想自己能够转而同动物生活到一起,它们是如此淡泊而又自满自足,
我站着对它们进行了很久的观察。
它们并不因为自己的处境挥汗并且哀号,
它们并不因为自己的罪过哭泣而是在黑暗中通宵不眠,
它们并不议论自己对上帝应尽的责任令我生厌,
没有谁感到不满,没有谁犯有严重的占有狂,
没有谁向另外一个屈膝,也不向生活在数千年之前的同类屈膝,
地球上没有哪个是体面或是愁苦的。
它们如此向我表明了同我的关系,我接受了,
它们为我带来的是我的各种代号,并且很明确地告诉我已经在它们的掌握之中。
我很惊讶它们是从哪里得到那些代号的,
莫非我曾经很早走过那地方,还漫不经心地将它们丢下了?
彼时此时甚至永远,我自己总是在向前移动着,
一直都在以高速度收集并且展示着更多的东西,
没有穷尽,无所不包,它们中间也有同它们类似的,
并不过分排斥自己的记忆所及,
还于这里选中了我自己所喜爱的一个;这个时候同他像兄弟一般 共同行动。
一匹雄壮而又健美的骏马,精神矍铄,对我的抚爱作出了反应,
它额骨高耸,两耳中间非常宽广,
肢体光滑又柔顺,尾巴扫地,
两只眼睛闪烁着机警,耳朵轮廓俊美,很灵巧地抖动着。
当我的两踵抱紧它的时候它张开了鼻孔,
我们飞跑一圈还归的时候它那匀称的肢体因为喜悦而微微颤抖。
我只用了你一分钟便即刻将你交出,骏马啊,
如果我自己能够超出你的速度又何须请你代步?
即便是我在站着或是坐下的时候也比你更加快速。
三十三
空间以及时间!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
我在草坪上逍遥的时候所猜想的,
我单独睡在床上的时候所猜想的,
还是在清晨那些渐渐暗淡的星星下面、在海滩散步的时候所猜想的。
我的羁绊以及压力都离开了我,我的双肘倚着港湾,
我围着锯齿形的山脉在走,我的手掌覆盖了大陆诸州。
我的目力伴随着自己周游。
在城市里面列成方形的房屋旁边——在木屋里同木材工人共同 露宿,
沿着关卡的车辙和干涸的峡谷以及河床,
铲除着我葱头地内的杂草或沿着一排排胡萝卜以及防风根锄松土地,跨过草原,于森林中寻路而行,
去探矿,掘金,将新购进的树木全部剥去一圈树皮,
齐脚踝受到了热沙的烫伤,将我的小船拖到了浅浅的河流当中,
那里,豹子在头顶的树枝上走来走去,那里的牡鹿回过头来怒气冲冲地对着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