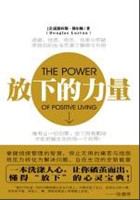小伙子在赶着快车,(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我爱他;)
混血儿将他的跑鞋系了起来,准备参加赛跑,
老人和青年们为西部射火鸡的活动所吸引,有的倚着枪,有的坐到了木料上,
射击手自人堆里面走了出来,站好了位置,举枪瞄准;
刚到的一群群的移民将码头或是大堤都站满了,
鬈发的人在甜菜田里面锄地,监工的在马鞍上对他们进行着监视,
舞厅里面的喇叭响了,男的跑过去寻找他们的舞伴,跳舞的彼此 朝对方鞠了一躬,
青年人睁着眼睛躺在松木顶的阁楼上面,听着那音乐般的雨声,
陷阱被密歇根人布在了注入休伦湖的小河湾那里,
裹着黄色镶边布围子的那些印第安妇女在兜售鹿皮便鞋以及珠子 串成的钱包,
鉴赏家们沿着展览厅的长廊在仔细进行观看,他们半闭着眼,哈着腰,
水手们则拴牢了轮船,将一块厚实的木板为上岸的乘客们搭了起来,
妹妹伸手将一束线撑开,姐姐将它绕成团,不时停下来将疙瘩解开,
结婚仅一年的妻子在恢复体力,因为在一周前生了头胎而感觉幸福,
头发干净的扬基女孩操作着缝衣机,或者在工厂还是车间里面干活,
筑路工人倚着自己那柄双把木槌,而新闻记者的铅笔则在顺着笔记
本飞驰,画招牌的人在用蓝金双色对字母进行着涂写,
运河上的少年踏着步在拉着纤索走,会计员在桌子旁坐着算账,鞋匠在为他的麻线打蜡,
指挥在为军乐队打着拍子,全部演奏员都跟随着他,
孩子接受了洗礼,新进教的人正在宣讲自己的初步心得,
比赛的船只满布海湾,比赛已经开始,(白帆上的金光闪闪发亮!)
赶牲口的在看守着自己的牲口,哪几只走散他便张口吆喝,
小贩的背上扛着包,身上流着汗,(买东西的人在对那一分钱的零头 斤斤计较;)
新娘抹平了自己的白色礼服,时钟的分针在慢吞吞地移动,
吸鸦片的人的头僵直着,微张着口,斜躺着,
妓女们胡乱地披着围巾,她的软帽颤悠在她那醉醺醺且又长满小瘰疬的颈脖上,
众人对她的下流咒骂进行嘲笑,男人们也嗤笑她,还互相挤眉弄眼,
(可耻!我绝对不会笑话你的咒骂,也不会对你进行嗤笑;)
总统在召开内阁会议,他的身边是那些部长大人们,
广场上有三个庄严而又友好的中年妇人彼此挽着臂膀在走路,
一群小渔船上面的捕鱼人在船舱里面一层层地铺放着比目鱼,
那个密苏里人跨越了平原,携带着自己的货物以及牛羊,
收票员走过车厢里的时候,让手里的零钱发出响动来吸引注意,
地板工人正在铺地板,钳铁工人正在盖屋顶,泥水匠正在吆喝着要灰泥,
工人们都各自肩扛着灰桶鱼贯而行,
岁月如梭,难以形容的拥挤人群已经集合起来,这是七月的四日,
(听那礼炮以及轻武器的鸣响声!)
岁月如梭,耕田的在耕田,割草的在割草,冬天的种子落到了土地里面;
在大湖的那边,捕捉梭鱼的人守候在冰洞旁边,
新开辟的土地上面到处都是密布的树桩,开地的用斧子大力地砍伐着,
临近黄昏的时候,平底船的船夫们将船在那些白杨或是胡桃树 的附近拴住了,
寻捕浣熊的人走遍了红河地区或是阿肯色河地区或是那些被田纳西河所汲干的地方,
在恰塔胡支或是阿尔塔马哈,四周的黑暗当中照亮着火炬,
长辈们坐在那里用晚餐,儿子、孙子以及曾孙们陪在他们身边,
在土坯墙内,篷帐下,经过一天的追逐之后,猎户们以及捕兽者都在休息,
城市入睡了,乡村入睡了,
活着的,该睡的时候睡了,死了的,该睡的时候睡了,
年老的丈夫睡在妻子身旁,年轻的丈夫也睡在妻子身旁;
这些全部内向进入了我的心,而我则是外向脸朝向它们,
按照目前的光景,我争取多少同它们一样,
我为了其中的每个以及全体在编织着这首自己的歌。
十六
我年老而又年轻,愚昧无知而又大贤大智,
不关心别人,却又永远在关心着别人,
是慈母也是严父,是孩子也是成人,
塞得满是粗糙的东西,又塞得满是精致的东西,
是由许多民族所组成的民族中的一分子,最小的与最大的全都是—样的,
是北方人的同时也是南方人,是一个漫不经心且又好客的种地人,居住于奥柯尼河畔,
是个准备照着自己的方向行商的扬基人,有着世界上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关节,
是个腿上裹着鹿皮绑腿行走于艾尔克洪河谷的肯塔基人,是路易斯安那人或是佐治亚人,
一个航行在湖上,海湾或是沿海的船夫,一个“乡巴佬”,
“七叶树”,“钻地獾”①;
习惯于脚穿加拿大雪鞋或是在丛林地带活动或是同纽芬兰附近的渔夫们在一起待着,
习惯于在—队冰船里面同其他人共同航行,随风势去转换方向,
习惯于在位于佛蒙特的丘陵地带或是在缅因的树林里面或是在得克萨斯的牧场上,
都是加利福尼亚人的朋友,自由自在的西北人的朋友,(热爱他们魁梧的体格,)
撑筏人以及运煤工的朋友,所有共进酒肉、握手言欢的人们的朋友,
最为质朴的人的学生,最有头脑的人的导师,
一个初学步的学习者,又是个历经了无数个寒暑的行家,
我隶属于各类不同色彩以及不同等级,各种级别以及宗教,
是个庄稼汉、技工、绅士、艺术家、水手、贵格会②教徒,
拉客者、囚犯、鲁莽汉、医师、律师、牧师。
我抵制那些可能会将我自己压倒的多样性的一切,
吸进空气,不过还为人们留下许多,
我并不自负,而是将自己的位置占着。
(飞蛾以及鱼子安于自己的位置,
我看得清的明亮星球以及我看不清的昏暗星球占着它们的位置,
可捉摸的占着它的位置,无法捉摸的占着它的位置。)
十七
这些其实是每个时代、每个地区、全部人们的思想,并不是我的独创,
如果只是我的思想而不是你的,那便没有任何意义,或是等同于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不是谜语也不是谜底,它们也便将会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它们不是既近又远,也便毫无意义。
这便是在有土有水的地方所长出来的青草,
这便是沐浴着全球的共同空气。
十八
让雄壮的音乐伴随我前来,响着的是我的号与鼓,
我不仅为公认的胜利者演奏进行曲,也为战败以及被杀者演奏。
你曾听说过大获全胜是好事,是吗?
我说溃败也同样是好事,战役的失利以及胜利出自同一种精神。
我替死者击鼓奏乐,
我用管乐器的吹口为他们吹奏最为响亮欢畅的管乐。
万岁,失败的人们!
战舰在海里沉没的人们万岁!
自己也同样在海里沉没的人们万岁!
在战役中失利的所有将军们以及被征服的英雄们万岁!
无数的无名英雄以及最伟大的知名英雄绝对是完全平等!
十九
这顿饭分配得很平均,这些肉是为饥饿的人们准备的,
不仅是为正直的人,也是为恶毒的人,我同所有的人都订下了约会,
我决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受到怠慢或是被遗漏,
在此,我特别邀请了那被人供养的女人,白吃饭者,以及窃贼,
那个厚嘴唇的奴隶和性病患者都受到了邀请;
他们将同其他人之间毫无区分。
这是—只害羞的手在进行按捺,这是头发在散发着香味,在飘动,
这是我的嘴唇同你的相触,这是充满了爱慕的低语,
这种非常遥远的深度以及高度将我自己的
面庞映了出来,
这是深思之后我自己的化
入以及再输出。
你猜我有什么复杂目的吗?
是,有的,因为四月里的阵雨是有目的的,岩石旁的云母也有。
你觉得我有意令人惊奇吗?
日光令人惊奇吗?红翼鸟一早就在树林里面鸣啭又会怎样?
我比它们格外令人惊奇吗?
此刻我说出了一些知心话,
我并不一定对每个人都说,但我要对你说。
二十
谁在那里来回走动?如饥如渴,神秘,粗野,而又赤身裸体;
为什么我能够自我所吃的牛肉当中摄取力量?
人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
一切我标明属于我自己,你就该用你自己的来把它抵消,
否则听信了我便是浪费时间。
我不会同有些人那样四处抽鼻子,
感觉岁月空虚,地上仅有污泥以及粪垢。
啜泣以及献媚同药粉包在一起是用来给病人吃的,恪守陈规只适用
于非常远的远亲,
我是否戴着帽子出进,全靠我自己情愿。
我为什么祈祷?我为什么虔诚而又恭敬?
对各个层次进行了探索,分析到了最后的一根毛发,向医生们进行请教,
计算得不差毫厘,
我发现仅有贴在自己筋骨上的脂肪才最香甜。
在全部人身上我能够看到自己,不多也不少,
我所讲到的自己的好坏,也都是指他们所说的。
我知道自己结实而又健康,
宇宙间自四处汇集拢来的事物,都在不断朝我流过来,
全部都是写给我看的,我必须要理解它们的含义。
我清楚自己是不死的,
我清楚自己所遵循的轨道是不能为木匠的圆规所包含的,
我清楚自己不会像一个孩子自夜间所点燃的一支火棍画出的花体字那样转瞬即逝。
我清楚自己是庄严的,
我不去耗费精神替自己申辩,或是求得人们的理解,
我清楚基本规律是不需申辩的,
(我估计自己的行为实在不比盖自己那所房子的时候所用的水平仪更高傲。)
我就按照自己这样存在足矣,
假如世上没有其他人意识到此,我不会有异议,
假如每个人都意识到了,我也不会有异议。
有一个世界意识到了,并且对我来说也最博大,那便是我自己,
不管我今天是否能够得到应得的报酬,还是需要再等万年或是千万年,
现在我便能够愉快地将—切接受,也能够同样愉快地继续等候。
我的立足点便是同花岗石接榫的,
我嗤笑你那所谓的消亡,
我清楚时间有多宽广。
二十一
我既是肉体的诗人还是灵魂的诗人,
我既占有天堂的愉快还占有地狱的痛苦,
前者我将它嫁接到自己身上令它增殖,后者我将它翻译成为一种新的语言。
我既是男子也是妇女的诗人,
我这是说作为妇女以及男子都同样伟大,
我这是说再没有谁比人们的母亲更伟大。
我歌颂“扩张”或是“骄傲”,
我们早已低头求免得够了,
我这是在说明体积也只是发展的结果。
你早已远远超越了其他的人吗?你是总统吗?
这些微不足道,每个人都会越过此点继续前进。
我是那同温柔而渐渐昏暗的黑夜共同行走的人,
我向那被黑夜掌握着一半的大地以及海洋呼唤。
请紧紧靠拢,将胸脯袒露的夜啊——请紧紧靠拢吧,富于力以及营养的黑夜!
南风的夜——带着巨大疏星的夜!
寂静而又打着瞌睡的夜——疯狂而又赤身裸体的夏夜啊。
啊!微笑吧,妖娆而又气息清凉的大地!
生长着饱含液汁而又沉睡着的树木的大地!
夕阳已经西落的大地——被雾气覆盖了山巅的大地!
满月的晶体稍带蓝色的大地!
河内的潮水掩映着光照黑暗的大地!
为我而更加明澈的灰云笼罩着的大地!
遥远的高山连着平原的大地——开满苹果花的大地!
请微笑吧,你的情人到了。
浪子,你给了我爱情——所以我也给你爱情!
啊,无法言传的、炽热的爱情。
二十二
大海啊!我已将自己托付给了你——我猜透了你的心意,
在海滩边,我看到了你那屈着发出邀请的手指,
我确信你没有抚摸到我是不会回去的,
我们必须在一起进行一次周旋,我脱下了衣服,急急地远离了陆地。
请用软垫托着我,请于昏昏欲睡的波浪里面摇撼我,
将多情的海水泼到我的身上吧,我能够报答你。
有着无边无际巨浪的大海,
呼吸宽广而又紧张吐纳的大海,
大海为生命的盐水,也是不待挖掘便随时可用的坟坑。
风暴的吹鼓手以及舀取者,任性且又轻盈的大海,
我为你的组成部分,我也同样:既是—个又是全部方面。
我分享你潮汐的涨落,对仇恨以及和解,
情谊以及那些彼此睡在对方怀抱里的人们进行赞扬。
我是那个同情心的见证者,
(我是否应该将房屋里的东西列出一个清单却单单将维持这一切的房屋漏去呢?)
我不单是“善”的诗人,也从来都不拒绝去做“恶”的诗人。
有关美德以及罪恶的这种能够脱口而出的空谈是怎样一回事呢?
邪恶和改正邪恶都在推动着我,我不偏不倚,
我的步法表明自己既不挑剔也不否定什么,
我将所有已经成长起来的根芽湿润着。
你是害怕长期怀孕的时候得淋巴结核症吗?
你是否在对神圣的法则还要重新研究并且修订进行怀疑?
我发现一面是某种平衡,同它对立的一面也是某种平衡,
软性的以及稳定的教义都肯定有益,
当前的思想以及行动能够令我们奋起并且及早起步。
经历了过去的亿万时刻而来到我当前的此时此刻,
没有比它和当前更为完美的了。
过去行得正或是今天行得正都不是什么奇迹,
永远永远令人惊奇的是天下竟然会有小人或是不信仰宗教者。
二十三
历代所留下的词句都不断展现在眼前!
我的是“全体”这个现代词。
这个词所标志着的是坚定不移的信仰,
此时或是今后对于我都是一样的,我会无条件地接受“时间”。
仅有它无懈可击,仅有它能够圆满地完成一切,
仅有那神秘而又令人困惑的奇迹才能够完成一切。
我接受“现实”,却不敢对它提出异议,
唯物主义贯彻始终。
为了实证的科学欢呼!精准的论证万岁!
将掺和着杉木以及丁香枝的景天草①取过来吧,
这是辞典的编纂者,这是化学师,这个人编写出了—部有关于古文字①的语法,
这些水手令船只自危险的无名海域安全驶过,
这是地质学家,是手术刀使用者,是数学家。
先生们,最高的荣誉永远是属于你们的!
你们的事实非常有用,而它们却并不是我所居住的地方,
我只不过是通过它们进入了自己所居住的区域。
我的词汇里面涉及属性的较少,
更多的是涉及那些未曾揭晓过的生活,自由以及解脱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