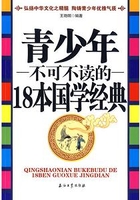雪雁摇头,说道:“我不敢说,每次王爷来,我都吓得不敢露面。王爷那张冰山脸吓不死人也冻死人了。”
紫鹃依然笑道:“可我刚才却瞧见王爷对姑娘陪着笑脸说话,那样子很是小心呢。”
雪雁不信,笑道:“姐姐可不是糊涂了?王爷又不是宝玉,怎么可能给姑娘赔笑脸呢。”
紫鹃抬手捏了雪雁的脸蛋一把,笑骂:“死蹄子,我何时骗过你了?”
雪雁方半信半疑,问道:“真的?”
“嗯,真的。”紫鹃点头,笃定的看着雪雁,又问,“雪雁,你觉得王爷和宝玉比,哪个更好些?”
“姐姐果然是痴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别说如今的宝玉,就是之前的宝玉,恐怕也难以跟王爷相比。只是姑娘心里的人是宝玉,那么纵然是天王老子来了,姑娘都不看一眼,又如何呢?”
紫鹃听了这话也是重重的叹了口气,谁说不是呢?这些年别人不懂,紫鹃却是懂的。林姑娘心里只有宝玉,心心念念的想着他,两个人吵归吵,闹归闹,却从未曾生分过。之前听着凤姐儿话里话外的意思,亲上做亲是必然的了。可是如今那边一败涂地,而林姑娘又被北静王救到了这里。如今这情形,北静王未必就肯放手,若是姑娘再执意拧着他的意思,将来结果怎样还真是不好说。
一时间,紫鹃又觉得愁闷起来,脸上的笑容一丝也无,尽变成了悲戚之色。
雪雁见了,忙拉了紫鹃的手问道:“姐姐刚才还好好地,这会儿怎么又变了模样?”
紫鹃叹道:“你说的有道理,咱们只在这里说这些都是没用的,若是姑娘心里一直放不下宝玉,任凭王爷是个天仙似的人,她只瞧不上他,我们又能怎样呢?”
雪雁听了这话,也跟着发愁:“按理说,王爷此等身份,肯对姑娘屈尊降贵,姑娘也该明白些才好。只是,这种事情咱们又不好去相劝,说的浅了姑娘只当没听见的样子,劝得深了,恐怕姑娘又要恼了。”
紫鹃点头,默默无语,心中却是百转千回,暗暗祈祷姑娘千万别太死心眼儿了,宝玉虽好,虽是从小的情分,只怕这会子老太太一去,老爷已经不是原来的老爷,太太也已经不是原来的太太了……
紫鹃暗暗地感慨着,如今的老爷太太若是见了林姑娘出现在北静王的身边,还会提及姑娘和宝玉的婚事么?恐怕他们满心攀附都来不及吧?
想到这个,紫鹃又忍不住哀叹一声,之前大家都以为三姑娘被南安太妃认作干女儿会拉他们一把,却没想到抄家之后南安王府连面都没露,如今若是让他们知道了林姑娘在北静王府,那天还不知怎么翻过来呢……
第二日一早,黛玉换了一身素白的衣衫,月白色挑金线暗绣竹叶梅花的长袄,袖口领口皆是珍贵的水獭皮子出的风毛,软软的浅灰色,无风自动,颤颤的触摸着黛玉颈子上白玉般的肌肤,微微的痒,比小婴儿的小手还柔嫩。里面是石青色弹墨绫子百褶裙,裙角上绣着金线五彩蝴蝶,行动处裙角摆动,那蝴蝶便如要飞了起来。
水溶依然是睡在东暖阁,早起过来瞧她,见了这身打扮的黛玉,心中隐隐的泛着痛楚。转头看见翠羽手里捧着的一件石青色织锦凤尾纹的狐皮斗篷,便吩咐道:“换一件斗篷来,这个颜色太过素净。”
黛玉刚要说什么,紫鹃忙冲着黛玉摇了摇头,轻着声音劝道:“姑娘,北边儿有句俗话,叫爷爷奶奶花花孝。老太太是您的外祖母,姑娘穿的太过素净了也不好。况且姑娘原本就病着,身上的气势也弱,太肃静的衣服容易招邪气。姑娘珍重自己的身子,就听王爷的话吧。”
黛玉迟疑的看着紫鹃,心道这丫头怕不是被人家收买了吧?如何会在这种时候劝自己这种话?
水溶听了紫鹃的话,咳嗽一声说道:“这丫头说的很是有理。想来史老太君也不希望你太过悲伤。你能健康的活着,她在天之灵也是欣慰的。”
黛玉便不言语,只凭着翠羽又取了一件藕紫色的大毛斗篷来给自己穿好,雪雁又拿过一个白狐皮的暖袖来把她的双手拢在里面,另有翠羽又抱了手炉脚炉放到车里去。
水溶原是命洗墨备了一辆特大的马车,因为不得张扬,所以他也不骑马。和黛玉一起坐进了车里,捡着僻静的巷子往宁荣街方向而去。
紫鹃等人都留在了院子里,跟来的除了一个赶车的老家人之外,便只有墨风和雪空两个绝世高手。如今他二人一个如影随形的跟着水溶,另一个则寸步不离的跟着黛玉。
今日水黛同行,他们两个自热都跟了出来。
贾母的丧礼不是一般的简单,不说之前和宁荣二府有来往的官宦世家都没来,就算是贾家族中之人都没有来全,再加上贾赦,贾珍和贾琏尚在牢中不能出来陪灵送葬,这丧礼更加荒凉。
水溶的马车到了原荣国府的大门口时,挑车帘一看,心中便觉一阵凄然。想当初贾蓉之妻的丧礼是何等的奢靡,如今老太太没了,却是此等景象。
轻叹一声,水溶看着坐在对面的黛玉,提前叮嘱:“带回见了你舅舅舅母他们,你只管说这些日子是住在我那里。他们说什么话你且先听着,一切都瞧在已故老太太的份上莫要跟他们计较。还有……莫要过于悲伤,于死者和生者皆无益处,明白么?”
黛玉鼻子一酸,已经红了眼圈儿,只是她多少也能听明白水溶的话,所以默默地点点头,并无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