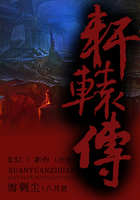紫鹃便笑着看了雪雁一眼,笑道:“又来一个玉,倒是跟咱们姑娘的名字重了一个字儿呢。”
洗玉忙道:“姑娘的芳名里有这个‘玉’字?可是我该死了,服侍了姑娘这几日连这个也不知道。亏了他们还只管这样叫我,都不知道避讳。这可怎么办好呢?”
雪雁便道:“按道理应该是主子给改了才好。只是不知道咱们姑娘这会儿是什么意思。”
洗玉点点头,暗香这位姑娘的性子孤僻的很,她一直都不肯多说话,定然是没把自己当这里的人,这院子里里里外外一共四五个奴才,哪一个也没能跟这位姑娘说上话。再说,想必王爷也是不知道她的名讳的,若是知道,断然没有不给自己改名的道理。
一时间洗玉很是犯难,知道自己进去请林姑娘给改名定然会碰个软钉子,索性这会子先忍一忍,回头王爷来了,回明了王爷再说吧,于是便拉着紫鹃说道:“多谢姐姐提醒,家里的规矩,断没有奴才的名字犯着主子的名讳的,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娘总叫我二丫,姐姐不如暂时叫我二丫吧。回头姑娘得了空闲,再请姑娘赐名也是一样的。”
紫鹃便很是喜欢这小丫头的伶俐懂事,索性拉了她的手笑道:“二丫是妹妹的娘叫的名字,我们是什么人,岂敢跟妹妹的母亲相比?索性这屋里的人也不多,我叫紫鹃,她叫雪雁,你比我们两个小几岁,我们便都叫你妹妹好了。”
洗玉忙欠身,对着紫鹃和雪雁叫了两声:“姐姐。”
紫鹃,雪雁和洗玉三个人开心的把手握在一起,点点头,雪雁又悄声问道:“刚才听妹妹说王爷,不知这里是哪位王爷的别院?”
“咱们这儿是北静王爷闲时读书的别院,外人一律不曾来过。”
紫鹃和雪雁二人听了这话,方知道当日把黛玉带走的人乃北静王的人,当时她们只当是姑娘被人家掳走,如今想想,竟是姑娘被人救到了这里。若不然,凭着那几日囹圄般的日子,林姑娘恐怕早就香消玉殒了。于是二人立刻点头噤声,不再有任何异议。
饭后,雪雁跟着洗玉去料理黛玉的药饵,紫鹃便在黛玉身边,把宁荣二府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都细细的说了一遍。后来说道贾母病逝,黛玉少不得又掉了些眼泪。
说道无话可说之时,紫鹃便忽然问道:“姑娘,你怎么不问问宝玉如何?”
黛玉便惨淡一笑,说道:“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他自然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了。问又怎样,不问又怎样?”
紫鹃也跟着叹了口气,说道:“姑娘这话是有道理的。宝二爷再不济,还有老爷太太呢。老爷虽然没了官职,但终究能够留在家里。太太把家里的丫头卖了,总能得些银子凑活着过日子。大老爷,珍大爷和琏二爷他们这些流放三千里的,家里都已经过不下去了。”
黛玉便奇怪的问道:“她把家里的丫头仆妇都卖了,得了银子不是要给外祖母办丧事的么?”
紫鹃便冷笑道:“老太太之前是有些体己的,抄家时并没被弄走。听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把那些东西都拿了出来,一房一房的都分得很清楚,还留了自己后事的银子。哪里用的着卖奴才的银子?若不是那日太太着急上火的把鸳鸯等人都卖出去,老太太或许还能多活几日呢。姑娘知道,老太太如何离得开鸳鸯?”
黛玉听了这话,便哀叹道:“之前听人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还觉得太过薄情。如今看来,事实也不过如此。只是外祖母好歹也是疼我一场,如今她没了,我竟不能过去送她一送,真天不怜我!”
紫鹃便劝道:“姑娘的心思老太太自然是明白的。只是如今姑娘这身子又是这副模样,这里乃是王府别院,又哪里是咱们能说了算呢?不过……听说北静王之前和宝玉很是亲近,姑娘何不求求王爷?或许王爷能念在旧日的情谊上,帮咱们一把呢。”
黛玉深深一叹,幽幽的说道:“一家子亲骨肉尚且那种情形,又何必指望别人如何?官僚之家相交,素来讲究一荣俱荣。如今的舅舅家风光不再,众人能够做到不落井下石也就不错了,又何必去奢求谁能够雪中送炭?再说,我又有什么资格去求王爷?我又不是这王府的什么人。”
紫鹃听了这话,也只能是哀声一叹。她也明白,黛玉说的没错。别说北静王府这样尊贵的人家是如今贾家攀附不起的,听说二姑娘的夫家孙将军家这样的正经姻亲,都没去牢里看过大老爷。史家和王家如今也没了来往,还指望什么北静王府?
一时间主仆二人皆沉默不语,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熏笼里的红罗炭哔哔啵啵的燃烧着,橘色的火苗突突的往上窜,氤氲的热气在屋子里扩散开来,床前淡紫色的阮烟罗纱帐悠悠的飘荡着,映着火光流光溢彩,宛如傍晚时分的漫天云霞。
晚饭时分,水溶又过来瞧黛玉。洗玉便趁机回了自己的名字泛着林姑娘的忌讳之事。水溶便低声问道:“可曾问明白林姑娘的闺名是哪两个字?”
洗玉忙福身回道:“回主子,奴婢问过紫鹃姐姐了,她说是‘黛玉’二字。奴婢不识字,不知道是哪两个字,只知道那‘玉’字是奴婢的名字犯着忌讳的。”
水溶点点头,说道:“既然这样,你的名字便改为翠羽吧。”
洗玉忙福身行礼:“奴婢谢主子赐名。”
水溶点了点头,抬脚进了房门,转过屏风恰好看见一个穿着茄紫色小毛坎肩的大丫头靠在床上喂黛玉吃药。便不言不语的走过去,坐在旁边的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