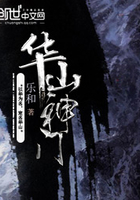雪空最后一个从屋子里迎出来,躬身请罪:“王爷恕罪,属下无能,林姑娘昏厥,一直难以清醒。”
水溶心中重重一叹,这个时候却是最要紧的时候,决不能让人知道她在这里,所以万不可去请了大夫来。然这个人,一直是离不开药培着的,这会子昏厥,自然旧疾又犯。若不请大夫恐怕性命不保。
可怎么办呢?
水溶进了房门后隔着屏风借着闪烁的烛光看着里面纱帐内音乐的身影,心里像是塞了一把乱草一样的难受。
雪空见水溶站在屋子里沉默不语,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虽然是女子,但却是他的护卫。不是那些紧身服侍的丫头小厮,哪里知道那些端茶送水的事情。
这小别院一直闲着,里面只有两个老婆子和一个看门的老头子看门打扫,平日里水溶偶然过来也是自带着丫头婆子等人收拾服侍的。这会子连王爷也是孤身前来,哪里去找丫头服侍呢?索性连一杯热茶也没有,好带着有婆子端了一杯滚滚的热水进来,歉然说道:“这里没有王爷用的茶,奴才万死,请王爷喝杯热水驱一下寒气。”
水溶摆摆手,让众人都退下去。自己却转身坐在一旁的椅子上,依然是隔着那扇镂花雕刻的六扇屏风看着床上娇弱的身影。
若是大张旗鼓的打发人过来伺候,定然引起诸人的怀疑。别人不用说,母妃那里就先不依。刚刚她还把自己叫了去单独嘱咐,说如今皇上在气头上,叫自己别去撞枪口。宁荣二府的事情也是他们自己招来的祸事,如今众人都想着如何自保,让他这几日少出去招摇。
这分明就是警告了。
水溶皱着眉头暗暗地叹了口气,别人如何此时已经顾不得了,可是她……是决不能送出去的。忠顺王世子当时一看属下送来的犯人名册上没有投靠来的林家女,便已经用追捕逃犯的名义借用了太后的烈虎骑。想来他若是得不到她,亦是不会罢休的。这种时候,她还跟贾家牵扯在一起,纵然一个请白女儿家也难逃悠悠众口。何况贾家今日所犯的罪恐怕还不止是纸面上说的那些。
怎么办呢?
水溶眉头紧锁,目光紧紧地盯在青色的绡纱帐子上,许久未曾移开。
纱帐内传来低低的哭泣声把纠结的水溶惊扰,他僵直的身子猛然动了一下,才发现自己坐的太久了,双腿酸麻连腰也有些僵直了。
黛玉在床上翻了个身,便咳嗽起来。初时不过是轻轻地咳,水溶不以为然。谁知却逐渐的剧烈起来,咳到后来水溶都觉得自己胸口里闷闷的不透气,便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那股冲动,起身越过了屏风走到了床前。
黛玉已经被自己咳嗽的从昏睡中半醒过来,莫名其妙的感觉到帐子外边有人时,她吃力的转身,便看见了一身鸦青色锦缎黑狐长袍的水溶。恍惚中她还以为是宝玉,于是低声叹道:“这是……什么时候,你……又来……做什么?咳咳……”
水溶便猛地掀开帐子坐到床边上,伸手把她扶起来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
黛玉咳嗽的昏天昏地,却终究是感觉到了身边的人不是宝玉,他身上有陌生的味道,那味道寒冷的如三九严寒的冰凌,一经吸入便直接渗入心肺溶入血脉,再也摒弃不掉似的。于是她狠命的挣扎着推开那只扶着自己手臂的手,喘息着说道:“放开……我……”
虽然黛玉从散花寺住了一些日子,身上的病大有好转,但仍然脱不了病弱的底子,此时她虽然有些竭斯底里,但那力气对水溶来说轻如抚摸。只是她那话却如一把冰冷的钝刀,缓缓地刺进了水溶的心口,他的手果然赌气的松开拿了回去。
然黛玉原本就没什么力气坐起来,本就是他扶着起来的。此时他的手臂一拿开,她便腰身一软摇晃着往地上栽去。
他低吼一声抬手把她扶住,生气的说道:“这是赌气的时候吗?你若是真的牵挂着贾家的人,就应该打起精神自己先好起来。你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连你自己都照顾不了,又能顾得了谁?”
黛玉在懵懂之中被这一声断喝唤醒,她睁开红肿的眼睛侧脸去看身边的这个人,却见他面带怒容愤愤的瞪着自己,那愤怒却没有掩盖他的光芒,反而越发的丰神如玉、怡然天下。
他清新俊逸面容夹杂着不可一世的冷漠,如墨色的眸子晶莹剔透、深不见底,让眉宇间的高贵优雅且不可抗拒。沉重的鸦青色织锦缎以其特有的奢华光晕勾勒着他的消瘦却硬朗的肩膀,华贵逼人。
“你是谁?”黛玉看着这样的人却忽然忘了恐惧,不像是看见雪空时那般无助。好像这个人身上天生就有一种令人沉静的气质,越是看着他的眼睛,黛玉便越是觉得自己的心智益发的空明起来。
“水溶。”
“水溶?”黛玉再次仔细的打量着他,想了又想,然后摇头说道:“我不认识你,你为何救我?或者说,你根本也是要囚禁我?”
“你怎么会不知道我?”水溶一愣,心想你又不是天外之人,荣国府的那个人不知道我北静王水溶?哦,是了,她是不知道这名字,于是他漠然一笑,说道:“那你知不知道北静王?”
“呃……”知道。黛玉清澈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惊慌,‘北静王’三个字是宝玉的嘴里常提到的,比如那年的鹡鸰香珠,比如那个秋雨天地斗笠和蓑衣……
看到她眼神里的慌乱,水溶的心情莫名其妙的好起来,心底的那股隐隐的怒气便消散了大半,长出了口气后,他扶着她坐直了又拉过一个靠枕来垫在她背后,扶着她歪过去,用他以为最温柔的声音问道:“饿不饿?我叫她们给你弄点吃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