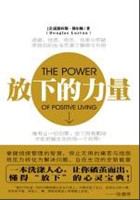“好了,”安西娅说,“你现在看见了!”
可是现在从窗户里看不见印第安人的影子了。
“好吧,”罗伯特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唯一能想到的,”安西娅——现在是今天公认的女英雄——“就是,我们尽可能地打扮成印第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去,甚至走出去。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是一个旁边部落的首领,而且——而且不会对我们做什么,你们知道的,他们害怕可怕的报复。”
“可是伊莱莎和厨子怎么办?”简问道。
“你忘了——他们什么都注意不到。”罗伯特说,“他们什么都注意不到,剥头皮或者用慢火烤也不例外。”
“可是太阳落山后他们会恢复原样吗?”
“当然了。你要是注意不到的话,你就不可能真正地被剥头皮或者被烧死,不然就算你当时注意不到,第二天早上也会被发现的,”西里尔说,“我觉得安西娅说得对,但我们需要很多羽毛。”
“我去鸡窝,”罗伯特说,“那儿有只火鸡——它状态不是很好。我剪掉它的毛它也不会太在意。把剪刀给我。”
急切地侦察一番后,他们肯定鸡圈周围没有印第安人。罗伯特去了。五分钟后他回来了——脸色苍白,但带来很多羽毛。
“听着,”他说,“这很严肃。我剪掉了羽毛,正要出来的时候一个印第安人从旧鸡笼子里斜看着我。我挥舞着羽毛叫起来,在他把鸡笼从头上取下来之前溜了。黑豹,把我们床上的彩色毛毯拿来,快点好吗?”
用羽毛、毛毯和围巾把自己打扮成印第安人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当然了,这几个孩子都没有长长的黑发,但他们有包教材用的黑棉布。他们把布剪成一条一条的,就像流苏一样,然后用女孩儿们最好的衣服上的琥珀色绸带将布片绑在头上。接着他们把火鸡毛插在绸带里。布条看起来很像长长的黑发,尤其是当流苏有点卷以后就更像了。
“可是我们的脸呢,”安西娅说,“颜色根本不对。我们的脸很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西里尔的脸是油灰色的。”
“我才不是。”西里尔说。
“外面真正的印第安人看起来是棕色的,”罗伯特赶紧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红色的——如果是印第安人的话,有红色的皮肤看起来更加高等。”
厨子涂厨房砖头用的红赭石粉看起来是屋里最红的东西了。孩子们在一个碟子里把它和牛奶混合起来,就像他们看见厨子涂地板时做的那样。接着他们仔细地把这个涂抹在各自的脸和手上,直到他们看起来和印第安红种人一样红为止。
当他们在走廊看见伊莱莎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看上去一定很可怕,因为她尖叫了起来。这个意外的测试让他们很满意。四个孩子急急忙忙告诉她别犯傻,这只不过是个游戏,然后就披着毛毯,插着羽毛,带着真正的红皮肤勇敢地出去面对敌人了——我说他们是勇敢的,那只是因为我想礼貌点儿——不管怎么说,他们出去了。
隔开花园和荒野的篱笆那儿有一排黑色的脑袋,上面都插满了羽毛。
“我们只有这次机会,”安西娅小声说,“这比等着他们可怕的攻击好多了。我们必须疯狂点,就像打牌的时候没有拿到王牌但要假装拿到那样,他们把这叫做装腔作势。现在开始吧。喔喔!”
随着四重战斗号角打响——对于之前没有练习过的四个英国小孩来说,已经足够好了——他们冲出大门,冲那一溜印第安人展现出战斗的姿态。他们都差不多像西里尔那么高。
“我真希望他们能讲英语。”西里尔悄悄说。
安西娅知道他们会讲,虽然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知道这一点。她把一条白毛巾系在一根手杖上。这是休战旗,她挥舞起来,希望印第安人能明白他们的意思。显然他们明白了——因为一个比其他人棕色要深一点的人走上前来。
“你们要讲和?”他的英语讲得很棒,“我叫金鹰,来自伟大的岩居者部落。”
“而我,”安西娅灵光一闪,“是黑豹……是……是……是马扎瓦特部落的首领。我的兄弟们——我不是这个意思——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部落——我指马扎瓦特人——正埋伏在那边山脊的后面。”
“那这些伟大的战士是谁?”金鹰说着,转向其他人。
西里尔说他是伟大的首领松鼠,属于莫宁刚果部落,当他看见简正咬着大拇指,明显想不出自己的名字时,他补充道:“这是伟大的战士野猫——我们这里叫普西费洛克斯——庞大的费兹奇部落首领。”
“那您呢,勇敢的红皮肤?”金鹰突然问罗伯特,事发突然,他只能回答说自己叫鲍伯斯,是好望角的首领。
“现在,”黑豹说,“我们的部落只等我们吹哨召唤,人数会远远超过你们弱小的队伍,抵抗是没有意义的。回去吧,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哦,兄弟,带着贝壳项链,与你们的妻子和医生们一起抽和平的烟斗吧,穿上最鲜艳的棚屋,高兴地吃刚捉到的鹿皮鞋吧(安西娅用错了不少印第安词汇)。”
“你都说错了。”西里尔愤怒地小声说。可金鹰只是怀疑地看着她。
“你们的风俗跟我们不一样,哦,黑豹,”他说,“把你部落的人都带过来,我们在他们面前谈判,这才符合伟大首领的身份。”
“我们会把他们带过来的,”安西娅说,“还要带上弓箭、战斧、剥头皮的刀,还有你能想到的任何东西,如果你们不放聪明点马上离开的话。”
她说得非常勇敢,但孩子们的心都跳得很快,呼吸也越来越急促。因为这些小个子印第安人正向他们围过来——愤怒地说着话,离他们越来越近——把他们围在一圈黑色冷酷的脸中间。
“没用的,”罗伯特悄声说,“我就知道。我们必须冲出去找沙精,它可能帮得上我们。如果它不帮忙的话——好吧,我觉得我们在太阳落山以后会再复活的。我怀疑剥头皮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么疼。”
“我要再挥挥旗,”安西娅说,“如果他们向后退,我们就跑去找沙精。”
她挥了下毛巾,那个首领让他的部落后退。于是,四个孩子跑起来,冲向印第安人人群最薄弱的地方。他们的冲击撞倒了六七个印第安人,孩子们跳过他们的身体,直接冲向沙坑。没时间从大路上下去了——孩子们直接从边缘下去,在黄色和淡紫色的野花和干草中,在小沙燕的洞口前,跳着,爬着,蹦着,踉跄着,最后终于滚了下去。
当他们正好到达早上找到沙精的地方时,金鹰和他的族人追上了他们。
可怜的孩子们气喘吁吁,心力交瘁,只能听天由命了。尖锐的匕首和斧子在他们周围闪闪发光,但更糟糕的是金鹰和他族人眼中残忍的光芒。
“你对我们撒谎了,马扎瓦特的黑豹——你也是,莫宁刚果的松鼠。还有你们,费兹奇的普西费洛克斯和好望角的鲍伯斯——你们都对我们撒了谎,不是用舌头,就是用沉默。你们打着白人的休战旗来骗我们。你们没有跟随者——你们的部落在远处,还在打猎。该如何处置他们呢?”他问道,残忍地笑着转向其他印第安人。
“用火烧!”他的族人说。于是立刻有十二个现成的志愿者去寻找柴火。四个孩子每人被两个强壮的小印第安人抓着,绝望地望着四周。哦,要是他们能看见沙精就好了!
“你们要先剥我们的头皮,再用火烤吗?”安西娅绝望地问。
“当然!”红皮肤人向她望去,“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印第安人在孩子们周围围成一圈,坐在地上盯着他们的俘虏。这是一阵可怕的寂静。
接着,去找柴火的印第安人三三两两地回来了,手中空空如也。他们找不到一根可以生火的树枝!事实上,在肯特郡那个地方,没人能找得着。
孩子们长长地松了口气,可立刻又被恐惧的呻吟取代了。因为他们周围正挥舞着闪亮的匕首。下一秒钟每个孩子都被一个印第安人按住,紧闭上了眼睛,努力不尖叫出来。他们等着匕首带来的尖锐的痛苦,可迟迟没有等来。接着他们被放开了,颤抖着倒做一团。他们的脑袋一点也没有受伤。他们只是感到奇怪的凉爽!野蛮的战斗吼叫声在他们耳中响起。当他们鼓起勇气睁开眼睛时,发现四个敌人围着他们疯狂地又跳又叫,并且四个人手里各自舞着一张长着黑色长发的头皮。他们摸摸脑袋——自己的头皮安全了!这些可怜的野蛮人只剥下了那层黑色棉布!
孩子们抱在一起又哭又笑。
“他们的头皮是我们的了,”首领吟唱道,“他们罪恶的头发生根于罪恶的头中!他们屈服在胜利者手下——没有挣扎,没有抵抗,他们向胜利的岩居者交出了头皮!哦,这样赢来的头皮真没意义!”
“他们马上要剥我们真正的头皮了,你们看是不是?”罗伯特说着,试着把一些红赭石粉从脸和手上抹到头发上。
“欺骗我们,我们就要狠狠地报复,”首领接着吟唱,“但除了剥头皮和火烧之外还有其他惩罚。那就是用慢火烤。哦,这个陌生的反常的国家连烧死敌人的木柴都找不到!——啊,我的家园在无边的森林里,数千英里的大树正是为我们烧死敌人而生。啊,多希望我们能再次回到原来的森林!”
突然,像是一道闪电,围在孩子们身边的重重人影变成了金色的砂石。等首领的话一结束,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消失了。沙精一定一直都待在这儿,它实现了印第安人首领的愿望。
玛莎带回了一个上面画有鹳和水草的水壶,也带回了安西娅给她的钱。
“我的表姐为了讨个吉利,把这个送给我了。她说原来和它配套的脸盆打碎了。”
“哦,玛莎,你真好!”安西娅叹了口气,抱住玛莎。
“是的,”玛莎咯咯笑道,“你最好在我还在的时候好好使唤我。等你妈妈一回来我就要走了。”
“哦,玛莎,我们对你没那么坏吧,不是吗?”安西娅吓呆了。
“哦,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小姐。”玛莎笑得比任何时候都开心。“我要结婚了,跟那个叫比尔的猎场守门人。自从那天你们被锁在教堂塔楼里,他把你们送回来以后,他就不停地向我求婚。今天我答应了,把他高兴坏了。”
安西娅把那七先令四便士放回了捐款箱,并在烧火棍捅坏的地方蒙上了纸。她很高兴能这么做,而且她至今不知道砸开一个教会的捐款箱会不会被判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