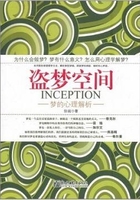顾姨娘并未由此释怀,“她如今哪还用我调教?每日习字作画做绣活,这不,又嫌自己身宽体胖,连荤腥都不沾了。我只怕时日长了,她的身子禁不住这么折腾。”
大老爷脸色微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她胡闹什么?”对上顾姨娘忧虑的目光,思忖片刻,又道:“去找个名医来给她看看,若无妙方,就让她死了这条心吧。”
顾姨娘立时觉得心里敞亮了不少,“可不就是,我只顾着心急,却忘了这一条路。”
睡前,管家遣了一名粗使婆子来通禀顾姨娘,说是请顾姨娘转告大小姐,大小姐吩咐的事已有了眉目,过两日就来后院禀明实情。用意不言而喻,是认定了蝶舞已将此事告诉了顾姨娘。
顾姨娘赏了婆子些银钱,回到寝室,几次想告诉大老爷,又几次把话咽了回去。空口无凭不如有实有据,现在说了,说不定还会帮倒忙。
两日后,是寒烨昭与四郡主大婚之日。
当天,将军府处处张灯结彩,如果忽略掉个个愁眉苦脸的下人,才是一派喜气祥和。他们习惯了府中的清静,习惯了只服侍将军一个人。如今添了一个主母两个姨娘,主母之父又是将军深恶痛绝的人,他们同情将军的同时,少不得也要担心日后自己的差事难做。由此,如果只看下人的脸色,寒府就像是在办丧事。
随着四郡主钟离薇的喜轿入门,另有两顶小轿从侧门抬进后院,里面坐着寒烨昭的两房妾室。
寒烨昭穿着大红色喜服,除了面无喜色,态度还算配合。依着规矩拜堂、掀盖头。
肃亲王及其王妃很明显是强颜欢笑,看着寒烨昭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条毒蛇,厌恶且恐惧。
礼成之后,寒烨昭去和同僚开怀畅饮。由于婚事是邵以南一手操办的,宴请的宾客就来自四面八方。满朝文武齐齐到场,另有京城商贾,江湖豪客,风流雅士。有四郡主十里红妆在先,今日的场面又声势浩大,不能不说,这是京城这两年来最风光的一门婚事。
问题出在宴席中途。
寒烨昭应付到中途,萌生倦意,去到书房院躲清静。途中,看到管家正和二十余名奴仆交涉着,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寒烨昭问:“怎么回事?”
管家气呼呼地,道:“将军,这些人是随送亲的队伍一起过来的。属下问起,他们说是要留在府中服侍四郡主。属下劝了多时,他们非但不走,还冷嘲热讽的。”
对于一度把“违命者杀无赦”当做口头禅的寒烨昭来说,事情就简单的多了,“召集侍卫,撵出去。”
若是寻常奴仆,的确是很简单,侍卫往他们面前一站就算了事。但这些奴仆在肃亲王府中是有头有脸的,平时又听多了自家王爷对寒烨昭的百般诋毁谩骂,硬是把盖世英雄当成了草包一个,此时非但不走,反倒用皇帝赐婚、王爷劳苦功高来威胁寒烨昭。
寒烨昭心里怒了,脸上却笑了,转身之际,温声吩咐:“今日大喜之日,就每人赏二十板子吧。”
正喝得酒酣耳热的宾客们,忽然就听到了连声惨叫。
宾客中不乏好事者,多人离席,一窝蜂涌出门去看热闹。
肃亲王沉下脸来,道:“成何体统!”随即命随从去查看缘由。
随从回来时脸色发白,哆哆嗦嗦地道:“王爷,事关王府体面,您还是亲自走一趟吧。”
肃亲王赶到的时候,几十名侍卫行刑已毕,王府众奴仆已经动弹不得,血迹浸透了衣衫,有的已经昏死过去,神智清醒的见到肃亲王就开始嚎啕大哭。而原来愁眉苦脸的寒府下人则眉宇含笑,一个个神采奕奕。
有人哭,有人笑,有人看热闹。抄手游廊上的大龙灯笼柔柔地映照着这奇怪的场面。
大喜之日见血光,大忌。
“寒烨昭!”肃亲王勃然大怒,“寒烨昭在何处?叫他来见我!”
没人应声。
肃亲王扫视在场人等,厉声道:“寒府管家何在?”
“属下在。”管家笑呵呵走到肃亲王面前,“禀王爷,我家将军稍后即到。”又转身吩咐小厮,“快去给王爷搬把椅子来。”
肃亲王恨不得把管家那张笑脸撕个粉碎,怒吼道:“叫他即刻来见我!”
管家转头望了望远处,笑道:“来了,来了。”
众人引颈望去,见夹道上一道颀长人影负手缓步走来,落步无声无息,黑色锦袍衣摆在洌洌寒风中飘拂。
喜宴未散就除了喜服,又一个让肃亲王火冒三丈的理由。他抖手点着寒烨昭,“你到底是在做什么?”
寒烨昭看了看一旁的太师椅,语声温和醇厚,“先坐吧。”
肃亲王真就坐下了。自己最钟爱的女儿的婚事,转瞬间变成了让人贻笑大方的局面,他早已气得簌簌发抖,站立不稳。
寒烨昭给出了选择:“是留两房妾室,还是留下这些下人,请王爷定夺。”
肃亲王一拍座椅扶手,恨声道:“你在今日把我的人赶出门外?你好大的胆子!”
寒烨昭不理他,转头吩咐侍卫:“把他们拖出门外。”
“我看谁敢动他们。”肃亲王霍然起身,“小心你的项上人头!”
侍卫们把肃亲王的话当做耳旁风,把王府奴仆或拖或抬带离寒府。寒烨昭在朝或者出征,他们都跟随左右。在他们心里,寒烨昭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令,不可违背。
寒烨昭的神色转为凉薄,“王爷惦记我这颗头颅已久,谁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