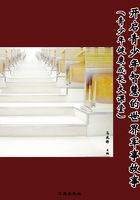她便一直闭口不言,却是日益担心。只是,养心殿与世隔绝,而本可与她通信的人已到了河南。
这一年的暑天异常的长,直到八月初七的处暑那日,依旧热浪滚滚,却莫名其妙的让人毛骨悚然。
皇帝一早便依着天朝往例到京处五金山上祭天,而梧心怀胎八月,妊娠犯重,整天累如病恹恹的病怏子,在榻上睡了又醒,醒了又睡。
缠绕二十载的噩梦似乎暂时离她而去,静寂暗夜下更沉重的噩耗,却蠢蠢欲动。
仿佛心有灵犀,又仿佛有更多的是一种不祥的预感,梧心忽地跳下床榻,隆起的肚腹让她行动甚是不便,却没有阻止她走往窗边那焦躁的脚步。
那里,正是一卷纸条。
而空中,一只苍鹰气喘吁吁的盘旋着。
是他!非……派鹰送信来了,由河南飞到了河北帝京。
梧心平静无澜的脸上,在那一刹之间,竟散发出了一种异样温柔的光芒。
那一刻,他仿佛感觉到,他的心,就在咫尺,虽触手不能及,那温暖却全数导进了心房最深之处。
不祥的预感,却在眨眼之间取代了那幻梦般的温暖。
仿佛在害怕什么一般,手指颤抖着,竟是不敢去打开那卷成一团的纸条。
梧心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那莫名其妙的恐惧却在四肢之间漫开游走,再也不复平静。
纤纤玉指止不住的颤抖主,轻轻的,轻轻的,打开了纸条……
“很好,你连每一刻私通的机会也不肯放过!”
梧心如人偶一般的木无表情,回首,毫不惊讶的看着那人一身还没来得及换下的明黄天子祭服,风风火火的踏进殿中。
相较于梧心平静得可怕的脸色,他那阴沉的脸上,写满了赤果果的怒火。“说!这人又是谁!”
在他伸手要夺下那纸条之前,梧心却幽幽笑了,笑声,没有往日的嘲弄讽刺,空空的虚寂得让人心惊。素手一挥,纸条被撕成了两半,再两半,再两半……
凤泠还未回过神来,她的声音却已在空寂之中响起:“皇上不是应该先说么?”
凤泠一僵,看向那一脸似笑非笑的少女,双手不由自主的攥起了虚弱的拳头。
那张清秀可人的脸,现今……竟是如此的空洞,仿佛最后一丝的美,最后一丝的丑……甚至是最后一丝的灵魂,都被抽走了,从此再无半点光亮,甚至再无人性。
他却很快定下了心神,高高在上的睥睨着她,阴冷道:“朕有什么应该说的?你背着朕私通他人,不打算给朕一个交待么?”
梧心的表情飘忽似梦,仿佛随时会消失一般,别样的不真实。“那……他呢?他死了两个多月了,皇上还打算瞒奴婢一世吗?”
凤泠终于重重一震。她终归是知道了!
梧心冷然看着那张泛着怒气的脸渐转铁青,再转赤红,最后变得苍白。
从一开始,他以亲生儿子的安危来迫她就范,两个月前,他设局把亲生儿子推向了张牙舞爪的敌人刀下,却若无其事的过了两个月。
撕碎的纸片随风飘舞,白色的纸碎恍如冥纸,撕得粉碎的“太子薨”三字,哀悼着棋子的废弃。
凤泠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竟是手足无措,不知从何开口。反是梧心,淡淡的笑了:“恭喜皇上,达到了皇上的目的。”她的笑,恍惚如鬼魅,空洞洞的,没有喜怒哀乐,甚至没有一丝人的感情。
他忽然有种想要向她解释的冲动,却终是死死的忍住了。
她凭什么,她凭什么让他放下自己的尊严,去作卑微的辩解,她不过是一个红杏出墙勾三搭四的小女人。
他却是下意阉的避开了那双空无得让人僵住的眸子。
“这下是皇上一直想要的么?如今做到了,不是天大的喜事么?”梧心轻轻的笑了,笑声中再无往日的嘲讽忿怒,清脆澄澈恍若毫无心机的浅笑,明明没有一丝半缕的冷意,却让人不寒而栗。“既有如此令人兴奋的消息……为何不告诉奴婢,好让奴婢死了这条心去?”
她明明是笑着的,唇畔还残留着那一丝纯净如孩童的微笑,却反而让他一阵心虚似的,侧过了身去,负手伫立,却不再看向他的方向。“你既已知道了,朕又有何可说。”
听着他不含感情的漠然冷语,梧心只觉心中好像涌起了一种名叫“悲凉”的东西,那如木偶般机械式的跳动着的心房,却早已麻木。“皇上不愧为旷世霸主,太子也不知是哪里对皇上构成了威胁,也被皇上借突厥之手,除个一干二净,还不忘加上一个冠冕堂皇的‘为国捐躯’。”她的声音,如那双眸子一般的冰冷空洞,一切的淡然早已卸下,仿佛最重要的东西早已被抽走,只剩下了一具虚壳之中的一片虚无。
凤泠只觉心头一颤,声音却依旧是奋力压抑着的平静。“你还是不明白么?只有朕,才配得到你。”
梧心没有说话,亦没有动,只是那片空虚显得更为冰冷了。
一朝帝王,竟道出了如此荒谬的话来,有谁会相信?他本来就是不会为女色所动之人,在顶着至高皇权之时,他对女人活脱脱的就成了一个“柳下惠”。以她为借口,也亏他想得出来。
梧心低下了头,张了张嘴,却吐不出一句满腔想好了的冷嘲热讽。心中,竟如脸上一般,成了一片空洞。仿佛,此刻,无论露出什么感情都成了伪装,而此刻的她,却什么伪装出做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