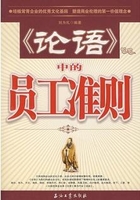愕然的瞬间,却没有看见那双无星如夜的眸子中,闪过了一抹异样的精光。
正常的生活。如果她真能放得下,那也不用以身涉险,夜夜与君同寝了。如果真的放得下,那她早就在梨落殿庸碌一生了。只是……又怎么可能真的放得下?十七年前的地狱之火,煎熬的,不是身体,是灵魂。身体的痛在灵魂脱壳的那一刻消失殆尽,灵魂的痛,却随着灵魂的飘浮,永远的残留在了灵魂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烙痕,无时无刻的侵噬着自己的本性,人性的善良。
“皇上,奴婢恕难从命。”梧心低低
一笑道。“奴婢与皇上之间,跨不过。”说罢,盈盈一福,躺到榻上,合上了眼睛。
她却没有看见,那一支朱笔停了下来,高傲的头微微转向榻上的人儿,那双深邃如幽夜的眼睛,是一片了然的透彻,还有那一点悲悯的凄凉。
正当她昏昏欲睡之时,却忽听那人道:“不想听听太子北伐的消息吗?”
梧心蓦地睁眼坐直,却直直的对上了那双暗黑无际的眼眸。
那一刻……她仿佛感到了一丝的害怕。
那双眸子,非愠非怒,却仿佛要把人吞进去似的,那幽深无边的眼眸让人望而却步。
“你对他……果真事事关心。”他的声音幽幽的,有些不太真实的感觉。
梧心低下了头,竟是不敢与他平视。“请皇上告诉奴婢,殿下北伐的消息。”
凤泠定定的看着她,饶有趣味的一笑,亲生儿子的消息竟是成了逗弄眼前少女的工具。“太子北伐,突厥大可汗阿史那烈云派出大王子应战,那大王子……”
梧心却已从床上跳了下来。“阿史那烈云?不是阿史那木罕吗?”
凤泠低头看着奏章,让人看不见他此刻的表情,只能听见他低沉的声音。“阿史那木罕已在影德十九年出使帝京后心疾死亡,据说是行至边送瞎坠马,之后便一病不起。”他的声音平淡如白水,却让她狠狠的一震。木罕!
震惊,已然掩盖了一切,包括理智。梧心霍地直立,大步流星的走到那一朝帝王跟前,忘了身份的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木罕死了?早就死了?你在骗我的是不是?他好端端的,又怎会就这样死了?”凤泠也一把站了起来,挣脱了她,脸上,依旧是平静如水,不喜亦不怒。
梧心低道:“奴婢逾越了,请皇上恕罪。”
那个人却似没有听见亦没把她的激动当成一回事般,淡漠道:“木罕大可汗死了,又有什么稀奇的呢?难道,你还会怀疑朕不成?”
梧心低低道:“奴婢不敢。”
她不敢怀疑他,其实,更是不敢去相信他!
那个人的神通广大,她不是没有见识过,也绝对不曾有疑,却是不敢去相信。
木罕死了!这让她如何敢去相信。
木罕死了,在他儿子死前半年已经死了!这让她如何愿意相信。
与其说是不敢相信木罕心疾而死,不如说是不愿相信木罕在摩耶行刑前早已死去。
难怪!难怪,摩耶死的时候突厥竟没有动静!难怪,突厥本来已然收敛却又突然猖狂起来。原来,在景德十九年末,突厥已然易主!新任的大可汗,怕是不愿摩耶回国争夺汗位,故意封锁了突厥大可汗阿史那木罕的死讯,不让传到中原去。
凤泠,却总有办法知道一切;他却瞒过了所有人。
梧心软软瘫倒在太师椅上,脑中一片空白,只觉很想哭,却已是欲哭无泪。
他早已死了,以一代大可汗的英名,因病驾崩。至死,他依旧是那个不可一世的大可汗,没有苦痛,没有义自己的罪付上代价。
她的报仇,竟都成了徒劳。连他爱子的性命,也是夺得如此的毫无意义。
设计拿工摩耶的性命,本就只是为了让木罕痛苦一世,怎料,他早就死了,死得一干二净,连丧失爱子之痛也没去尝尝!
那,她做了这么多,意义又在哪里?这场复仇的游戏,她布置了很久,用尽心机,只为让他一朝崩溃;怎料,他却先撒手而去,而加,却连一腔的怨气也无处发泄。
梧心死死咬住下唇,只觉无名的痛,游走在经脉活络间,蔓延着,渗入了骨髓。
此刻,是什么感觉,她已形容不出,只觉本来欲加诸木罕身上的痛,反噬其身。
当一个人恨到了极点却无处去泄恨,仇恨,是否会在身体里爆发?
直到这一刻,她才蓦然醒觉,世间最痛,并非肩负血海深仇;而是,肩负着血海深仇却无处发泄!
直到这刻,她才发现,最痛苦并非看着亲者痛仇者快,而是亲者痛而仇者却已矣!
死亡,当真是最大的解脱,死了,连仇也报不了,一了百了,连自己的罪也归于黄土去也!
梧心闭上了眼睛,眼前恍惚之门出现了阿史那木罕那张狂傲的笑脸,他死了,把她独个儿扔在了没有报复的仇恨之中,独自闷在恨的痛苦之中。
跨过了一个年头了,也许,他已经喝过孟婆汤,过了奈何桥,投胎到了什么人身上,忘记了前世的一切罪恶……
为何!为何老天偏偏要如此耍她?犯了罪的人,都把一切的罪恶消零,只剩下她孤身一人,满腔的怨恨只能一个人吞下。
梧心忽然笑了,轻轻的笑声在空寂的偏殿中回响着,莫名的空洞,莫名的寂寥,让大鼻子一酸。
凤泠没有说话,良久,却忽地轻轻道:“一个人死了,他的一切都带进土下去了,什么责任也不用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