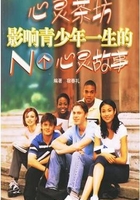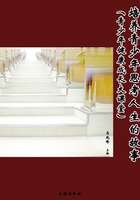木罕……我该拿你怎么办呢?拳头,蓦然攥起,梧心冷冷一笑。我已给了你警告,可你还是不听!
中原之事,不是你所能插手的!梧心闭上了眼睛。十八年前的大仇,我还没有和你算账呢,新仇旧恨也就一并解决好了!也好,快点理清了你这笔帐。
阿史那木罕,你既不仁,就不要怪我不义!
是夜,那个人第一次没有驾临偏殿。据工人说,他首次驾临了郑妃新赐的紫霞殿。
在紫霞殿……那便好!梧心冷冷一笑,是夜却没有上塌。
反正,要睡觉的话,日间有的是时间。夜黑风高,要做一些更重要的事。
偏殿中灭了灯,殿外的守卫换了更,一切恢复了原始的寂静。
梧心却是不复寂静的那一个。熟练的钻进床底,在地上一阵摸索,开启了地洞的门,跳了下去。
纵便有人在地道中,那又如何?该知道这地道的人都不可能现在出现在地道之中,即便是出现了的人也是见奋得光的,她怕他作甚?
深深吸了一口气,梧心在墙上摸索了一通,关上了地洞口。
独自一人往前走着,更加的小心翼翼,惟恐有什么变卦;她忽然不习惯独自一人。
是沉溺在他的同行避荫下太久了吗?梧心一怔。她是……真的,习惯了和他同行,所以独行才变得这么别扭吗?
倚赖,是一样行可怕的东西。习惯了,沉迷了,有可能便是万劫不复。
往前不缓不急的走着,走到了那间石室里,稍为鉴定了自己的方位。
石室四周的墙都是幻觉,而她只能根据方位来判断出口的位置。估摸着记得,那次自幕府出来是那棋盘机关的对面,便顺着这条路摸了过去,却果真是一条地道的入口。
梧心淡淡一笑,穿过了那堵“墙”。
这地宫应该是根据某种阵法而布成的,故此能制造出幻觉以及这许多的机关,然而这些都不是她现在要顾及得了。她现在只能回到相府去,借此路出宫。
她必须得问凤非几个问题。那纸条上的问题。小心……
地道不长,她却感觉好像走了好几个时辰。来到了尽头,正要在墙上摸索那洞口开关,却倏然听见了微弱的人声!
“你怕什么,他们都已经死了,死了十八年了!”一把压抑的男声隐隐约约自上面传来,听不清楚是发自何人,却竟有一点点的熟悉。
女子低低的啜泣之声传来,地板却隔了一半的声音,听不清楚是谁人的声音。
那把压抑的男声却又道:“他们都死了!挫骨扬灰,洒在了乱葬岗上,不会回来了,你瞎担心什么?”
那是什么人?梧心只觉心快要跳出了胸膛。十八年前,挫骨扬灰,乱葬岗……那人还在幕府里说话!
那是谁?他说的一切……为何,竟生生似是在说十八年前的幕府灭门之案?
不会回来了……这,又是何意?
梧心只觉莫名其妙的恐惧袭来,那藏抑已久的许多疑问又如潮水般上涌!
地面沉稳的脚步声传来,梧心一凛,脱了脚下的花盆底鞋,提着鞋子往回路无声的奔去。
那脚步声……似是要往地洞口而来。上面那两个人,是什么人?他们……是从地道而来的吗?
他们是宫中的人么?半夜三更,鬼鬼祟祟的,又在幕府商讨着什么?谋划着什么?
梧心只觉满腔的疑问与莫名其妙的恐惧往自己砸来,竟有一种窒息一般的感觉。
脚下再也不停步,匆匆奔回了石室,穿过幻想的石墙,奔上了往养心殿而去的地道。
有人在幕府之中私会,本来借幕府出宫的计划已然泡汤,还平添了这许多谜团。
凤非的密函内容没有着落,而幕府中的那一对男女,还有那把有点熟悉却压抑的让人异常不舒服的男声……
钻出地道,钻出塌底,梧心站起来,环视四周,依旧一片漆黑,是掩盖了一切的夜色。
长长舒了一口气,梧心把本来提着的鞋子放到榻边,径自上了榻,盖上了绣花被。
心事重重如她,满腹疑惑如她,却没有看见殿门边那道如夜幽邃寒凉的目光。
被梦魇惊醒之时,已是卯时,日头已微露崭角。
梧心穿好外衣下了床,那个人已上了朝,养心殿中又剩下了她一人。
望向窗外,竟有苍鹰在外盘旋。
凤非,他,果然聪明!待那个人在朝上之时送信给她,那个人……至少,一时半刻之间是不会回来的吧?
那信鹰竟是很有灵性,见她把头伸了出来,便飞到了窗边,爪子不知怎地一踢,便扔下了一封信。
这次,他的信,很长,很多字,让她不得不坐到榻上,静下心来看。
“地宫布局行两仪阵,已向师父讨教。”那熟悉的笔迹只有两句,下面则是一行行的蝇头小楷。
他竟知道她心中所想!这些蝇头小楷,便是凤非向清杨老人讨教,清杨老人所书的吗?
但见那纸已变黄,凤非的那两句是新干的墨迹,看下去更像是清杨老人从前所写而凤非不过送来了给她看看而已。
不再去追溯那一纸的来源,梧心匆匆阅了一遍,叠好了那一张纸,放入怀中。
有了上次被那个人撞破的教训,她不敢研读太久,等下次下地宫再行慢慢研究那阵法罢。
地宫……对了!忽然想起一事,拿笔纸匆匆一书,正要让信鹰回给凤非,却发现信鹰早已成了半空中的一个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