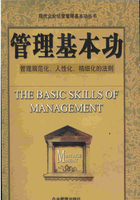“你……”涨红了脸,梧心结结巴巴的吐出了一个字。
“我什么?”凤非似笑非笑,深沉稳重的眸子里充满了狡黠之色。
不待她发难,快速的按了墙上的开关,暗门虚虚而开:“回去吧!此地不宜久留。”
梧心敛了正神,点了点头,攀了上去。洞门在身后缓缓合上。
这地道,若已被人发现……里面的那个人,却是谁?
凤非有武功在身,才能探得那人的气息,那人必是在较远处。那个人,却为何会出现在地宫之中?
这地宫,只有近三十年前被灭族的叶国公一族、嫣语和那一朝天子知晓。那地宫中的那人……是谁?
皇帝还在南方,嫣语已渐入疯癫状态,那么……那地宫中的人,有可能是谁?
而,当初,那个人和嫣语为何会知晓地宫的存在?她只觉越想越乱,如雾里看花,怎也看不清。
许是因为地宫中出现了神秘人物,那支暗号的白梅便一直没有出现在养心殿中。
如是者,便又过了数日,离凤泠返京之期只剩下了十天。
这日,梧心拆了如意结又编,一缕阳光自窗外射入,却带来了一声鸟鸣。
梧心愕然望向窗边,只见一只苍鹰在空中盘旋,而窗台上则是多了一卷纸条。
信鹰?
外面的侍卫依旧纹丝不动,似是不疑有诈。梧心淡淡一笑,拿起了纸条,坐到榻边,只见那苍鹰已经往无边天际而去。
梧心浅浅一笑,卷开了纸条。这小子好样的!不用信鸽而用信鹰,那些侍卫却竟也没有生疑。
看见那卷纸条上的字,神色,却立时凝重了下来。
“京军投诚,突厥连秦,小心……”
“尚御好兴致!”
梧心重重一震,手一松,还未看完的纸条在两双眼睛的注视下落入地上的火盆,顷间烧成了灰烬。
“奴婢参见皇上。”她的声音平无波澜,却是暗暗心惊,仿佛有一种被人抓在床的感觉。
那个人……心情好的时候,只会喊她“梧心”而非“尚御”,现在,看来他的心情不是很好。
凤泠是笑着的,只是那笑却远远不到那一片冷寒的眸底。“尚御可悠闲得很!悠闲得不甘寂寞,互通情信了吗?”
梧心闻得此话,却反而是暗暗松了一口气:他并没有见到纸条上的字,还以为那是“情信”!
他的皇弟的情报在他眼中成了他的皇儿的情信,当真有趣。若不是面临着他如此压抑欲爆的气场,她当真要哈哈笑了出来。
见她仿佛整个人轻松了起来一般,凤泠的面色更为不善,冷然道:“你就是如此不甘寂寞的吗?”
梧心浅浅而笑,从容自若:“奴婢本来就是不喜欢寂寞的人。”心中却已暗自焦急:凤非的纸条还没看完,就已被自己一不小心的“毁尸灭迹”……他说,小心什么?可恨,自己被那个人吓的连小心后面的两个字也没有看进去!
凤泠却哪知道她此刻心中的思量,轻轻笑道:“若朕不是早了十天回来,便看不到你和别人私通款曲的景象了吧!”
梧心一凛。“皇上,有些事……有很多事,非是皇上见到或以为见到的,便为准。”
凤泠却显然没有思考这话的深意。“是么?那就由朕来告诉你吧,朕看到了什么!”
梧心微微一怔,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凤泠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她,一脸的冷然:“朕不过才离京二十日,这京中都不得安宁了!”
梧心却忽然想起纸条上的那句:京军投诚!
京军,常驻京城的京营,由骠骑大将军率领,左将军为随军。凤非所云的“投诚”……却是何解?
左将军……对了,左将军!左将军为前人的太子少傅,莫非……他,竟能让京营的人投向太子一方?
还是,京营中,早已不平静?诚如这眼前的九五天子所说,离京二十日,京中各方势力已是暗流汹涌?
见她一脸深思的样子,凤泠没有发怒,只是依旧以不咸不淡的语气道:“怎么了,在为你的殿下担忧么?”
看着他倨傲冷漠而略带嘲讽的样子,梧心只是暗自思量:这个人,真当自己能掌控一切,京城势力不稳,他也只道是太子监国不力,竟不疑是那个一向“软弱”的太子也有参与其中!
梧心淡淡笑了,面色平和而淡然:“太子殿下尚为年少,没有监国经验,而这一月之间,恰也暴露了太平下的暗流汹涌。”
一句话,既洗脱了太子的“监国不力”的“过错”,又暗示了眼前这皇帝开创的太平盛世不过是一个假象,一箭双雕,却也让他难以反驳!
凤泠也是聪明人,又怎会听不出她这许多的弦外之音?
随意脱下明黄的外袍,凤泠慵懒的坐卧在贵妃椅上,淡淡道:“你当真以为这皇帝好做么?你当真以为,朕不想开创真正的太平天下么?”
梧心一怔,低首,在他看不见的唇边,漫起了淡淡的冷笑。
他为了自己,为了想要得到的至高皇权,杀戮战争无所不用其极;他做的一切,与其说是要开创太平盛世,不如说是要稳固自己手中的帝业皇权罢了!他的眼中,哪有太平天下,有的不过是自己的如画帝业罢了!
见她不语,仿佛知道她毫不信服一般,凤泠竟是低低叹了一口气。
把身体往后靠了靠,凤泠缓缓合上了眼睛,轻轻道:“你以为,当一个皇帝是如此简单不过的事吗?不信的话,问问你的太子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