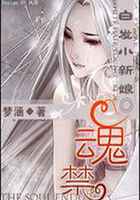仿佛过了很久,梧心转身,强行咽下了鼻子的酸意,往房门的方向走去。“我要的感觉,已经找到了。此地再无可恋,我们走吧。”
她要的感觉,是痛苦,刻骨铭心的痛苦。只有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彻骨痛苦的人,才能坚持着自己的初衷,才能把痛苦转化为施予仇人的恨。
回首,却见凤非呆呆的环视四周,一脸的若有所思。
“走吧!”梧心幽幽一叹。
凤非恍若未闻,怔怔地望着一尘不染的檀木桌子,呆呆出神。
“不好!”倏然回过神来一般,凤非低低道:“有人来过!”
“有人?”梧心心下一惊,忙问:“和解?”
慕宅已空置了十七年有余,何以凤非却说有人来过?
“门牌上灰尘仆仆,显是十七年间已积尘甚久,只是房中的一切,皆是清洁得没有一丁点的尘埃,一定有人清理过,还是不久之前的事。”
“什么?”梧心骇然。“还会有谁进来过?”
废后与“叛贼”一家的宅子,还有谁会进来?朝堂上的人,皆是人人自危,还有谁敢来?
而且,慕氏一族已消失了十七年,还有谁,时至今日,仍会来慕宅,进来“她”的闺房?看房中的整洁程度,那人的确是走了不久。
“对了!”梧心忽地想起一事,一个激灵,低低问:“今日是什么日子?”
凤非深深的看了她一眼:“你不记得了吗?今日是十一月初八。”
“是啊!十一月初八。”梧心忽地低低笑了起来,笑声轻轻的,浓浓的凄绝却让人不由得一震。“我怎能忘记的呢?”
十一月初八。十七年前的这一天,是她的大婚之日,她如愿以偿的嫁给了最爱的男子。第二日一早,又被爱了一生的男子休掉、灭门。
这样的一夜,她怎能忘记,又怎会忘记了的呢?
除了她,却是谁记住了这一个日子?她几乎能肯定,那来过不久之人,是为了她而来。
凤非若有所思的端详着室中的一饰一物,仿佛过了很久,眸中一片了然,却似是不想多生事端一般,轻轻道:“走吧。”
梧心心中虽有疑惑,却点了点头,收敛心神,正欲随凤非走出去,却徒然听见了一阵清亮的脚步声。
有人折返!
梧心心下一惊,一把扯过了凤非的手,低低耳语:“到床下去!”
凤非是当朝九王爷,虽是换了民装,却不曾易容,与皇家有关系的人必会认得出来。私闯禁宅,若被有心人落下把柄抓住,凤非随时不保。
明知是兵行险着,她却不能害了凤非,脚步声已至房外,她唯有出此下策。
梧心万万没有想来,床底下竟是如刚刚才打扫过一般,一尘不染。
心下愕然之时,却已听有人推门而入。
沉稳的脚步声传来,门“曳吱”一声的合上,一双皮靴向房中的檀木桌椅走去。
梧心匆匆往后挪移了一分,深怕被那人发现。一挪,却是退进了一人的怀中。
差点溢出的惊呼被理性咽下,梧心只觉自己的脸颊像被火烧着一般的滚烫。
背上,温暖的触感传来,她知这是凤非的安慰,脸上却不争气的滚烫了几分。
仿佛过了很久,室内依旧毫无动静。
就在梧心已习惯了一动不动、凝息静气的冰雕状态时,却听见了又一人推门而入的声音。
脚步声轻轻的,似盈盈而进的一个女子。
从床底下的缝中看出去,只见一双素白的绣花鞋,正往那双靴子之处走去。
“是你让人收拾了这里的吗?”
那把熟悉得可怕的声音,差点让梧心惊呼。
梧心紧抿着嘴唇,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着,似是快要爆发一般。
为什么,是他?
强而有力的手从身后伸过来,轻轻按住了她颤动不已的嘴唇。淡淡的温暖传至唇间,仿佛平复了心中汹涌的涌的波涛。
只是,那只温暖的大手,也仿佛轻轻颤了一下。
只是,为何来人竟会是那人?他不是恨死了她,恨死了她一家的么?为何,十七年后,“驾临”慕家废宅的人竟会是他?
女子的声音却让她心中的波澜更汹涌了几分。
“嫣语知道,你今日会来。你每一年的十一月初八都会来……”
梧心的身躯又是一震,再次忍住了呼之欲出的惊呼。嫣语!为什么,她会出现在这儿!
“谁准你自作多情了?”那个人的声音,淡淡的,不带一丝感情。
梧心心中却已充满了疑惑,还有……那一丝连她自己亦不曾察觉的苦涩。
皇后不是被罚永久禁足了吗?为何,她却会和那个人“成双成对”的出现在这里?
这里是“废后”的闺房,她的两个最大的仇人却齐齐出现在这儿。如此的可笑。
她做这一切,只为把皇后逼上绝路。皇后却浅笑盈盈地在宫外与自己的夫君逍遥。如此的可悲。
却是谁自作多情了?为何,那个人却说皇后自作多情?
“嫣语自作多情了吗?”皇后的声音如少女一般的清脆明亮,却是夹杂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十七年了,嫣语还是连与皇上分担的资格也没有吗?”
一片死寂。梧心屏息等待着,只觉自己的胸膛也要爆炸了,只是死死的忍住,只想尽快逃离。
室中男女却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
仿佛过了很久,梧心只觉一阵烟雾的味道扑鼻而来,一呛之下让她几乎要咳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