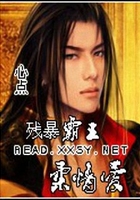是害怕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吗?还是……是有别的原因?
却,是有什么原因可言?她是梧心,她命由她不由人,现在却竟连自己的心思也看不清。
心中异常的烦闷,梧心眉头紧锁,直直的往宫门而去,“我想出宫,可以……送我一程吗?”
这一刻,不知为何,她忽然不想失去他。
仿佛……当一个人习惯了另一个人的存在,便不愿让他从自己的生命里消失。
习惯,是一样很可怕的东西。
习惯了并肩,习惯了倚赖,便再也不能心无旁骛。
皇城外,大街之上人烟旺盛,两侧贩子吆喝叫卖,大道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
午时,正是京都繁华的时段,街头巷尾皆是一片热闹。
梧心缓缓在街道上走着,只觉仿佛与这京都的一切格格不入。
明明,周围皆是一片热闹,她的心中,却是静寂得孤独,仿佛遗世而孤立。
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耳中却只有唏嘘。
墨色的眼眸,忽然变得迷离起来,仿佛,茫然了,惘然了,一切都在忽然之间失去了意义。
“非。”梧心忽地幽幽开口,“有时候,我真的怀疑,我是不是错了,也许地狱更适合我。”
凤非不语,只是把她一把扯进了一家服装店。“宫里的衣服碍眼,先换掉了再算吧。”
走出店子之时,凤非已成了一个蓝锦长袍的中年儒生,沉稳儒雅。而梧心,则成了素白衣裙的年轻少妇,浅笑盈盈,笑意却远远未及混沌的眸子深处。
并肩走上大街,良久,默然无语。
仿佛过了很久,却忽听凤非道:“姐姐,你没有错。既然天不绝你,你就没法回头,注定了,只能走下去。”
那一声“姐姐”,触动了最深处的那根心弦,久久未散。
侧首,静静凝望着他沉静儒雅的侧面,忽觉心好像平复了,清明了,如湖水明静清澄。
“非……”梧心轻唤一声,声音犹似梦中,“可以,带我到相府去看看吗?”
相府,自十七年前的灭门后,一直不曾入住过任何人。当今丞相另设府第,慕相府便一直空了十七年。
踏入空无一人的相府,静寂恬宁恍十七年前的任何一个下午。
冬梅绽放,落英缤纷,如此的美,美得凄冷。
梧心一步一步的走进相府,仿佛步步维艰。
每一步,皆如踏在针尖上一般,痛入骨髓,苦沁心脾。
府中死寂一般的宁静,皆在提醒着她,自己的错误给至亲带来的痛苦、毁灭。
明明,整座相府中没有一丝血迹,梧心却仿佛看见了遍地的殷红。
仿佛,她的血,慕氏九族的血,溅了一地,炽热而寒凉。
“为什么……这么静?”她的声音,如云雾当中,疑幻疑真。“每一刻钟的宁静,都似对我的罪的惩罚。”
冰凉无温的小手,忽地抓住了身侧男人的大手,恍若一个遇溺的小孩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般,死死的不愿放手。
凤非僵住,不敢动弹一分,仿佛在害怕吵醒此刻脆弱的少女。
他,从来不曾见过她如此受伤、脆弱的一面。十七年前的她,淡静宁怡而纯真明净;十七年后归来的她,满怀一腔仇怨藏于心底,明明近在咫尺却无法接近。这一刻的她,却是如一只受伤的小兽,满满的痛苦,却用伪装的坚强保护自己。
当保护墙在那一刹那间倒塌,他看见了她的痛苦,那一霎,他只想用自己仅有的温暖,去暖和她冰冷的身体。
眨眼之间,柔弱的小手却已挣脱了他的大手,脸上如处幻境之中的表情已自不见,混沌的眼眸重复清明,阴冷的恨如寒冷的深潭,幽邃迁见底,只是多了一丝坚毅的寒凉。
罪恶,终会得到惩罚。天没有惩罚那个人,却把自己召回人间,那是天意,天不去行的,就该由她来做。
若是错,那从一开始便已是错,又有什么好回头的?
沉静,良久。
“可以……陪我去一个地方吗?”梧心的声音,不再迷幻,却是夹带着丝丝的沧桑与苍凉。
凤非默然点了一下头,不再言语。现在的她,已不需要有人为她挡在身前,所以,他只能默默的站在背后。
已有十七年不曾踏足这个地方,梧心却似是出于灵魂深处的本能一般,熟练的在回廊之间穿插,直到停在了一间屋子前。
屋子的门牌已被重重尘埃覆盖得迷糊不清,只有两个字依稀可辨:“梨落”。
大气而温润秀雅的两个字,一如藏书阁中的“梨落散曲”四字。
往事,点滴回涌,梧心一片漆黑的眼眸染上了悲凉,与深深的愤恨幽然。
梨落。那一年,她央着他为自己题一副字,那个人微微一笑,题下了“梨落”二字。
她问,为何是梨落。她说,梨花飘落,太伤感。
他说,梨花在飘摇的时候最美……
他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他给了她一个最美丽的死法,何样的讽刺。
眼中一酸,梧心不欲再看,匆匆移开视线,推门而入。
典雅的檀木桌椅,淡碧色的垂幔软塌,墙上悬挂的山水墨画……一切皆是如此的熟悉,熟悉得让她眼中一湿。
一切的一切,恍如十七年前的大婚前夕。
思忆如潮,让她忽然很想哭,却已哭不出来。她已不能再哭,她已失去了软弱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