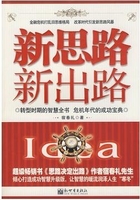他叹气:“你怎与别人提我们的事?你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我说:“我与他现在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没有想到他会找你撒气……”
他继续叹气:“我想不到你这么聪明的人,也会做这样的蠢事。再聪明的女人,终究也是女人哦……”
我几乎流泪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可否告诉我?”
他缓缓地说:“那个林,花一千元钱请了白粉仔来我家淋红油,后来白粉仔已把一切都承认了。现在派出所的人已到林的居住地找他回来问话。”
我泣不成声:“此事会不会对你有影响?想不到林会做出这种事,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的……”
他打断我:“现在说这些于事无补,就算我不想追究,现在也轮不到我决定,常委那里需要一个交代。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
我头痛欲裂,颓然伏在桌子上。
为什么会这样?林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与我分手后,事业有成,婚姻幸福,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临下班时,吴明再次致电我。
他说:“问清楚了,事情确实是你初恋男友林做的。”
我默然,且听他说。
他继续说:“我也如实向常委汇报了,说确实认识林的前女友,但关系并非他想象的那样。常委表示,鉴于没有造成多么大的损失,由我自行处理。”
我低声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他说:“按我的脾气,非要揍他一顿,再关他十五天不可。现在算了,我也不想再生事端,叫他找人来清理干净便算完结,不然搞大了对谁都没好处。”
我叹气,确实如此。
末了,吴明说:“找个时间出来见面吧,有些事情想与你说。”
我脱口而出:“今晚吧!”
他说:“今晚我必须回家,不然这事对家里人说不清楚。”
我暗暗叹气。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首要顾及的,自然是最重要的人。哪怕他曾经为我跳进淤泥中摘荷花,也不过是一时之兴。
可是有多少女人,因为男人曾为她摘荷花,便以为男人可以为她摘星星。因为男人叫了她一声宝贝,便以为自己真的成了珠宝。殊不知对男人来说,你是珠还是猪,完全取决于他的心情。
他感觉到我的失落,好言相劝:“没事了,好好睡一觉,一切都过去了。”
真的是一切都过去了么?我抚抚欲裂的额头,想哭,却无泪可流。
晚上,我接到林的电话。犹豫再三,我还是按了接听键。
从话中,也可听出他的沮丧。他说:“你现在能出来一下吗?”是该做个了断了,我强忍满心的厌恶,说:“好,立即过来接我。”
仍然是市政府后花园,清幽依旧。一墙之隔的迎宾馆旧址,已建起了富丽堂皇的购物广场。面对面站立的两个人,却形同陌路。
所谓沧海桑田,不外如此。
林叹气,说:“事情估计你已经知道了。”
我说:“是。”心想:你还有脸问我。
静默良久,他接着说:“对不起。”
我终于发作,说:“不是所有的对不起,都可以换回一句没关系!”
他再说:“对不起。”
我恨极,一脚踹在他脚上,他毫无防备,跪倒在地,狼狈地爬起来,忙不迭地拍裤子上沾上的泥土。
我冷冷地看着他,像看着多年的仇敌。他哀声说:“冰冰,不要对我这么残忍。”欲过来抱我。
我狠狠地双手推开他,流泪并大声地说:“我当年向你认错,是你不要我。等我死心了,你还不肯放过我。我到底欠了你什么?我与谁在一起关你什么事?我恨不得你死,也不想你再纠缠我……”
他流泪:“我根本不知道你当年曾经等待我。我提出分手的时候,你那么冷淡,我根本不知道你不想分手……”
我冷冷地说:“就算我当年说不愿意分手,你依然会心里不平衡,觉得我对不起你,事后免不了再三提起。你不是一个宽容的人,不管你有多喜欢我,你都不愿包容我。”
他说:“不是这样的。我与你分开之后,才知道与你在一起的日子,有多幸福多快乐。我都不知道,如果再也见不到你,我的日子怎么过……”
每个人在感情上,都有一座过不去的火焰山。明知火势汹汹,也有人心甘情愿毫不设防地靠近,失控,直至葬身其中。
这样的表白,放在数年前,我定感动万分,重投他怀抱。
可是事过经年,我再无波澜。如同隔岸观火,哪怕对岸叫声震天,也与我无关。
我看着林:“不管你怎么想,我都必须告诉你,我现在不想与你来往,与别人没有任何关系。就算没有吴明这个人,我也不会与你在一起。”
林说:“我们曾经相处得那么开心,没有人比我与你相处得更加默契。我知道你的想法,我知道你的需要,只要你给机会,我们是可以在一起的。”
我冷笑:“那么你知道我现在需要什么?”
林充满自信地说:“一份稳定的感情,一段安定的婚姻。如果你愿意,这些我都可以给你。”
我说:“你打算离婚?”
林说:“为了你,我愿意离婚。老婆当年对我好,我可以把钱和房子都给她。孩子我舍不得,就让孩子跟我,你那么善良,一定会对孩子好。”
我打断他:“你根本不了解我,如果你离婚娶了我,我一定不会对你的孩子好。”
他不甘心地说:“你故意这样说的,你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我正色告诉他:“你错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喜欢小朋友,但我不喜欢别的女人与我丈夫生的小朋友,我不但不可能对你的孩子视同己出,说不定还天天打骂,以泄心头之恨。”
他沉默,无言。
我看着他,沉声说:“你最大的缺陷,是根本没有想清楚要不要,就轻率地决定放弃或接受。当年对我如此,现在对你老婆也是如此。”
他犹自在分辩:“不是的,我与你,感情深厚。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
我正色道:“我们分开这么久,你现在还知道我的想法么?那么,我告诉你,我现在想给大弟谋一份好工作,你有能力吗?我想一直往上爬,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吗?我想让乡下的爸妈在城里养老,你可以做到吗?我与吴明在一起,就是这个目的,你可以吗?”
林张口结舌地看着我:“你变了。”
我没好气地回他:“你以为你没变?你现在是孩子爹了,还想像当年一样与我携手花前月下,还想让我帮你照顾你与别的女人生的孩子,你不感觉自己可笑又可耻?”
林痛苦地抱着头蹲在地上。
我大声说:“你还敢叫人跑去人家门口淋红油。如果人家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你还得治安拘留十五天!你惹不起的,别以为挣了几个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半晌,林终于站起来,佝偻着腰爬上车,好像一瞬间老了几十岁。
我朝他挥挥手,示意他先走。我不想与他再有任何交流,所有的所有,到此为止吧。
直到他的车完全离开,我才默默地坐在夜合花下的草地上。
刚才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吗?如果是,为何我说出来的时候,会感觉这么累,好像体力不支?难道我说的都是假话?那么我为何要说假话?
我不知道,我统统不知道。
我只知道,有的人,有的事,是有保质期的,该结束的时候,便该当机立断地结束。如果舍不得,它迟早会像食物一样变质,危害你的健康。
这是我与林的最后一次见面。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
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不管是爱,还是恨,我们彼此都不曾留过余地,所以从此以后,我与他都不好相见了。
所谓分手后做朋友,做亲人,都是骗人的鬼话。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你还想让熟饭再变回生米,就算你愿意,饭也不愿意。
不是没有遗憾的,只是我本凡人,哪能事事如意。
整整一夜,我倒在床上,翻来覆去。
这几天,我终于知道失眠的滋味。以前,我是一个闭上眼便能睡的人,我曾经奇怪为什么有些人会失眠。原来有一天,我也会。
第二天醒来,我照照镜子,看见一张暗淡无光的脸,还有一双疲惫的眼睛。我依然快速起床,循例走到楼下的办公大厅视察一番。
楼下的人正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看见我下来,立即自觉作鸟兽散。我心里一惊,莫非他们此刻议论的,正是我?
我微笑,以若无其事的表情走近他们,说:“说什么说得这么兴起?”
那几个人却支支吾吾,说正在谈论天气。
我又不是气象局长,谈论天气用得着见我迅速作鸟兽散?我正想反问,猛然想起怀疑周围的一切,乃妄想迫害症的前期表现,只好扫兴地闭上嘴巴,微笑着与他们聊了几句闲话才上楼。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再加上我与吴明属同一系统,有男人因我而争风吃醋跑到吴明家淋红油的事,想必已全城皆知。我长叹一口气:我该做最坏的打算了。
自小到大,我便不是一个乐观的人,凡事必做最坏的打算,最起码,当事情不可收拾时,自己还懂得一切都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
埋怨自己,总比埋怨别人来得舒服,最起码你不会想到与别人算账,这样你会少些怨恨。
次日下午下班前,吴明约我吃饭。我在司法局的后门上了他的车,他不待我系好安全带,便发动车迅速离开,像一名急着逃离现场的逃犯。我惴惴不安地看着他,百感交集。
曾几何时,我也是别人的白雪公主,几时试过被人如此漠视过。
直到车子驶到远离市区,与邻市交界的地方,他才偏头看我,解释道:“刚才忙着赶路,没顾得上说话。”我点头表示理解。不理解又如何,他自然有他的理由,问题是他还需不需要我理解而已。
所谓理解,实在是男女间说得最多但又最无用的东西,当一个男人已经无须你理解的时候,你理解与不理解,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默默地叹了口气,心头如被大石压着。
依然是邻市的那家田园饭店,我们来过很多次,连服务员都认得我们了。她们依然热情地打招呼,再把我们安排在栏杆边的位子上,然后依然泡上一壶菊花茶。
毕竟已是秋天,没有荷花,甚至连荷叶都谢了。坐在栏杆边,风很大,阵阵吹来的寒意迫人,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我突然想起,就是在这个地方,吴明曾经为我跳下荷田,摘下两朵荷花。那时候的我,心情如盛开的荷花般怒放。
吃饭的时候,彼此都没有说话。他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把我喜欢吃的菜挑到我碗里。我也懒得吃菜,默默地吃白饭,像一个无端被家长责难的孩子,心中的委屈压得心底发酸。
我甚至连抬起头来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唯恐一抬头,满眼的泪水夺眶而出,把自己满心的酸楚和无助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