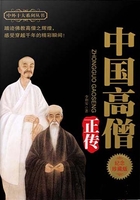“回皇上,当真。臣观大皇子面容丝毫不见疯症,此时由侍女艳儿领着已去了锦福苑,娘娘故意瞒住皇上恐怕……不只是怕皇上责罚大皇子。”严文庭伏地叩头,声音渐渐转小。此语极重,连皇后也牵连在内,常贵立时惊出一身冷汗。
仁帝猛的抄起手中杯盏:“真是朕的好儿子,竟欺瞒到朕的头上来了……皇后竟也帮衬着,简直是目无纲法,眼里还有朕这个皇上没有!”
一盏茶在空中掠过一道弧线映着烛火溅起一串晶莹,最后白瓷杯盏铮然迸裂一地,一阵刺耳厉响响彻整个沉寂的黑夜。“常贵,摆驾锦福苑!路上不必通传!”
跪在地上的严文庭赶忙起身随仁帝步出御书房,全然无视常贵瞥来的满眼怒气。
常贵一路缓慢跟着,静静观察仁帝神情,只觉宫中立马要有一阵狂风骤雨将至,仁帝故意不通传可不正是要去锦福苑抓个现行?这若真是人没疯,欺君之罪再加上夜宿烟花之地,两罪并罚罪名可真是不轻!不免担忧起来。
常贵是个念旧的人,常日里这些个皇子公主待人最和蔼的便是楚云铎,每每见到总是挂着温柔的浅笑从未出现过因为心中郁结而拿奴才宫女出气的事儿。此时常贵只盼着仁帝到时,锦福苑早已空空不见人迹或者是这条去锦福苑的路突然变长,永远走不到头。转念一想,常贵这才恍然大悟。刚刚皇后派人来过一回儿,嘱他定要劝说皇上好生休息,现在严文庭这一闹,莫说强行拦下严文庭惹恼了皇上,就是皇后也定要责怪他办事不利,严文庭呀严文庭你可真是个祸害!常贵忽然脚下一顿,人呆呆的僵在原地,身旁小太监见他如此怪异,赶忙提醒。转神之后,瞥见仁帝投射来的冷厉目光,立时一惊赶忙紧随而至。
锦福苑外负责看守的侍卫远远见仁帝过来,立时奔入苑内,艳儿听闻通传,立时慌了神,左右走了几遍却还是没有主意。
莫菲雨却仍镇定自若,冷眼旁观着焦虑不安的艳儿和仍满目含情抱着红绣的楚云铎,兀自摇了摇头,上前拉了楚云铎一下,“太子若还这个样子恐怕皇上见了会更加气恼。”
楚云铎也没多说话,只是抬眸看了看莫菲雨,声音悲戚,道:“只怕父皇一会儿来了,我与红绣便是永别,现如今没了这太子的枷锁,我倒也没什么顾虑了,只盼着能与红绣早日做一对阴司鸳鸯,永不分别。”
“太子如何这般悲观?人活一世不易,你只顾着两情相许,倒是负了太子妃的一片真心。”莫菲雨手搭在楚云铎肩上,一脸沉静。
“我已不是太子,蕙兰自然也不是太子妃,再者我早已写下休书放她自由,勿要多劝!”楚云铎只觉被莫菲雨如此看着心中顿时生了怯意,片刻间心跳的也有些微急,目光飘忽在红绣与她之间,最后定格在莫菲雨处,仔细端量,突然间有些莫名慌乱,吞吐道:“你……”
莫菲雨笑得会意,随之口中轻哼起一段小调,只待这如莺婉转的声音渐渐停歇才朗声道:“正如太子所料,那么可否先将红绣放下?”
楚云铎定定然的看着莫菲雨笑得如此释怀,那雨中扫楼的女子真的是今日眼前的雨公子?未有犹豫的缓缓放下怀中的红绣,楚云铎只紧紧凝住莫菲雨。仿若在这顷刻间时间停住,朝夕相念的人近在咫尺,为何却总觉仿若隔了千山万水,永远也难触及,只有红绣,现在唯一牵挂的女子便是红绣了,楚云铎这样不断在心中提醒自己。
仁帝一行刚行至苑外,便听得一段他未曾听过的曲子随风轻缓飘来,令人听之格外清心,听严文庭说随太子去往锦福苑的是个男子模样的人,这调子也绝不可能是艳儿哼的,难道是严文庭眼花,但这想法随即便被仁帝否决,御前侍卫人人一身好功夫,皆是百里挑一难得的人,专由皇上一人差遣,而严文庭自恃有百步穿杨的功夫,绝不可能会眼花。陪在一旁的严文庭在听得这声音之后也狐疑的皱起了剑眉,倒没吱声。
仁帝等人终于入内,进入房内却故意越过了众人直接投射在莫菲雨身上,楚云铎跪在地上偷偷看着仁帝,忽然心中悸动不已,跪行到仁帝身前:“一切都是儿臣的错,请父皇莫要难为母后以及无辜之人。”
仁帝冷哼一声,目光冷然渐渐转向楚云铎:“这时候你倒能担当了?”楚云铎垂目不语,更是激怒了仁帝。“朕苦心栽培你二十几年,你竟为了个女人忘了江山社稷祖宗基业,你说,她到底用了什么法子能将你媚惑到如此昏庸地步?告诉朕,你心中究竟哪个更重?”
楚云铎闻言在地上连磕三下:“父皇既已废了儿臣,便不要再问儿臣哪个更重,现在莫说红绣已去,就是红绣未死,儿臣心中也只有她一人!”
莫菲雨听闻后眉头皱了皱,此语无异于火上浇油,看来楚云铎是报了必死之心,可恨她刚才苦言相劝,果然看到仁帝气的来回踱步。“啪!”的一声,仁帝的掌风已经猎猎袭向楚云铎,楚云铎也未躲闪,殷红的血顺着唇角缓慢流出,滴在地上格外刺目。
就在仁帝的第二掌即将袭来时,一阵猛烈的咳声霎时响起,常贵赶忙抱住仁帝,随即又胆战心惊的松了手,一时无措失了主意:“皇上,您可要保重身子!”楚云铎忽然眼底一清,看到仁帝咳得厉害,身子微颤。瞬间便扑至仁帝脚下,“父皇,都是儿臣的错,还请父皇息怒!”
仁帝气的不耐,又要抑着喉中不断窜上的阵阵麻痒,手指冷冷指着楚云铎,道:“你眼中可曾有过我这个父皇!真是辜负了朕,辜负了百姓以及兰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