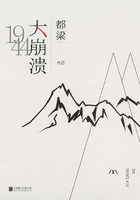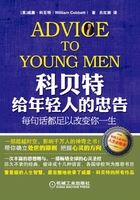阿荨闭上了双眸,对近在眼前的危险气息有种享受的态度,她轻轻勾唇,淡淡的浅笑。
“唰……”数箭齐发,破风的声音直刺耳膜。
阿荨痛苦地捂着小腹,站在雪里里,仿佛只要那么一眨眼,她就会烟消云散一般,感觉有温温的血液从自己的身体里流了出来,原来死,也不是想象中的那般痛。
平地落下的人影,长袖一挥,浑厚的内气将射上女子身上的寒箭震碎,眼前的男子蹙眉,静静地站在她的身边。
慢慢地似乎有一双大手,一点点地握紧自己,那样的温暖,三哥,你来了吗?
上官景鹰眸一片阴沉,看着挡在阿荨身前的祁钰,冷冷地说道:“齐江东王殿下也想管我梁国之事吗?”
“你们为何要杀她?”祁钰淡淡地说道,扶住女子摇摇欲坠的身子。
“是她自愿请死的!”
“是吗?难道不是你们在逼她?”祁钰眸子在此刻淡无光彩,漆黑沉沉中,唯余见不到底的深邃。
“祁钰哥哥,姐姐被他带走了。”怀中女子的声音如蝇,仿佛随时都可能消逝。
“什么姐姐?”祁钰一怔,垂眸望着她。
阿荨拧紧秀眉,感觉身上的力气被慢慢地抽空掉,女子站着的脚下,已经鲜血淋淋,像极了一朵盛开极致妖娆的红莲,刺目刺心。“就是祁钰哥哥的绛儿啊。我帮你找到她了,可是又被我弄丢了,对不起……”
“阿荨……”祁钰看见阿荨苍白的唇,血色全无,女子身下的血流得更多了。刹那觉得有什么恶魔一点一点地在吞噬着他的思想。而她对他说的话,却是一句也没有听得进去。
“我带你去看大夫。”祁钰面色沉静,抱起女子,抬眸看了看上官景,眼底却渐渐冰寒。仿若所有情绪化作了利剑上犀利凌厉的锋芒。
“站住。”上官景暗道,他没想到突然出现的祁钰会对眼前的女子如此的关心,想不到这个小丫头还真是有些本事的。
“青衣侯是想从本王的手里把她杀了吗?”祁钰蹙眉,冷冷地看着上官景。
上官景怔了怔,本来杀这丫头也是不能张扬的,却不知道祁钰是怎么知道的,想来祁钰也不可能单独一个人过来救这丫头,四周肯定还有不少的人。
而上官景也深知,梁公主与棠成亲,棠能强忍自己对阿荨的情意,大殿上没有失态,如果他知道阿荨遇到危险,自然会抛下一切,甚至与梁皇反目为仇。
上官景淡淡地挥了挥手,一阵窸窣兵器摩擦的声音,他身边的武士纷纷放下了手里的箭,退出一条道来。
祁钰抱着身前的女子,感觉女子的身体越来越轻,仿佛就要消失一般。鲜血一滴一滴地从女子的身上流了下来,落到素白的雪地上,刺目诡谲。
梁宫殿堂,荆少棠握紧的酒樽突然一颤,掌心处一片殷红,酒樽壁处雕刻的繁纹已经被他握碎,尖锐的碎片刺破了他的掌心。
梁成君,抬眸看得心惊,赶紧递上一块丝布,担扰地说道:“世子,你没事吧?”
荆少棠手里的酒樽落地,看着掌心的肌肤处缓缓渗出来的血水,眼神跳跃不停,阿荨今天很反常,表面明明是漫不经心,豪无所谓。可是那琴声里的伤,琴声里的悲,琴声里的怨,他听得清清楚楚。听得他身心欲裂。
公子顿时推开了梁成君,狂跑之间,绯色流纹的喜服,翻飞似狂云。
他要去找她……
阿荨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不然她的眼神怎么会那般的绝望与留恋,仿佛他们再也不会相见一样。
他跟她说过,要等着他!丫头,不要做傻事,纵使天下不要,他也不会不要她。
白茫茫的一片,绯红刹时翩然如火云,荆少棠见到站在殿门外的无落,朝她吼道:“丫头去哪儿了?”
“公子……属下……不知。”无落语气闪烁。
“不知?你会不知?她跟你说过些什么?送走荆绛蓉是她请你帮忙的,可是荆红绛蓉突然不见了,难道跟你没关系吗?无落,你是我的手下,还是叔叔地手下?你为什么要替叔叔做那么多的事情?阿荨,她到底哪儿去了?”公子扼着她的喉咙,往日凤眸里的神采飞扬已经不见,转而的是一片火红的怒气,还有失落的面容。
“公子,主上……”
“主上把她怎么样了?她不是同意离开吗?”为什么还要如此做。
“在哪里!”荆少棠吼道。十指的指甲已经渗入无落脖子处的肌肤里,流着淡红的颜色。
“城隍东。”无落说完,整个身子已经被荆少棠甩落在了地上。女子缓缓的从地上起身,望着荆少棠远走的身影,脸上一个黯然之色,希望公子不要怪罪她才好。
城隍东郊一片空旷,不见半个人影,空气里弥漫地是淡淡的血腥气息,荆少棠觉得全身发凉,地上的血如一张巨大的爪子,一点一点地撕开着他身体。
阿荨?是她吗?
她又跟叔叔达成了什么协议,她总是这般任性,做了什么事情,不愿意告诉他。等到他发现的时候,他就得替她收拾烂摊子。
公子站在那里,愣愣地。许久,许久……任风吹起身上大红的喜服,如血般妖娆。
阿荨迷迷糊糊地跑着,她想追上走在她前面的三哥,可是永远也追不上,她又害怕一旦停了下来,三哥的影子会离自己越来越远,最后什么也没有。
风呼呼地刮着,雪峰里的苍鹰飞得极底,辇车慢慢地行驶着,生怕惊动着躺在车内的女子。
祁钰见诸葛流云眉色微蹙,急急地问道:“她怎么样?”
诸葛流云摇着头,面色平静不起波澜,祁钰让他随行,并不是因为一时兴起,诸葛流云先前也见过自己的师父宣婵,知道了些阿荨的事情。只是此时,他的心里矛盾至极,不知道应不应该将阿荨的身体情况说出来。
“失血过多。”诸葛流云平静的说道。
“仅仅如此?诸葛流云,这次出来,本王可不是带你出来游山玩水的!”祁钰说道。
“这个我知道。”诸葛流云淡笑。“我只是暂时保住了她的性命,到了武丘之后,你再找间好一些的客栈让她住下来好好静养。而且你到了武丘,也要做一些事。”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祁钰眸间渐暗,幽芒隐隐。阿荨都已经这样了,而诸葛流云却还这样淡定,肯定有什么话没有说出口。
诸葛流云抬起阿荨毫无一丝血色的手腕,放入锦被里。抬眸,眼睛里黯淡无光,却让人莫名地觉得寒冷:“孩子没了。”
“什么?”祁钰一怔,愣愣地看着晕迷不醒的女子,眸里有惊愕,有幽怨,有痛苦。
孩子?谁的孩子?是上官棠的?她竟然……
“她腹中的孩子有一个多月了,已经没了。不过也是好事,身中恶毒,就算那孩子生出来也必定夭折。”诸葛流云明明感觉到了祁钰身上那种冷冽的寒气。还有欲暴发的怒火。
“可恶!”祁钰低吼。上官棠太卑鄙了,居然如此伤害阿荨。
“钰,你也不必这么生气。我想这件事,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包括这个丫头。”
“不要告诉她。”祁钰的声音很低,很沉,很暗。凌厉的眸光此刻不知怎的有些黯然的幽深冰凉。难怪她会如此痛苦,面对上官景的箭,眼神是如此绝然。
阿荨醒来之时,一睁开眼,呈现在眼前的是淡绿色的青纱帐顶。她伸出手来,摸了摸自己还在跳动的胸口。感觉仿若隔世。
女子伸出瘦长的手指,慢慢地在自己的眼前晃动着,指尖蓦然被人握住,阿荨抬眸,祁钰的面容出现的自己的眼前。
阿荨正想张嘴,却只是吐出如蚊蝇般细小的声音,轻得自己都听不到。
“这是客栈,你没事了。”祁钰淡淡的说道,温和地看着她。面色憔悴,明日里犀利凌厉的双眸里布满了血丝。
“我……”她想起身,却没有一点儿力气,手掌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只记得三哥和梁公主成亲,她气急攻心,走出殿门之时,吐出大口的鲜血,感觉肚子隐隐地作痛。
慢慢地全身好冷,越来越痛……
“你要起来?”祁钰问道。
阿荨点了点头,刚伸出的另一只手也被他握住。祁钰倾身,扶起阿荨的头,慢慢地扶她坐了起来。
“我睡了很久?”阿荨抬眸打量着四周的一切。
一间不大的客房内,简简单单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这也太简单了,桌上的青花瓷碗还冒着白白雾气,有种清素的药味传了过来。
“不多久,几天而已。我发现你很能睡,而且很喜欢弄伤自己。”祁钰看着阿荨,轻轻一笑,入室的暖阳轻盈地跳跃在他墨黑色的睫毛上,细微的光芒,使他本就明亮的眼睛更添上了一种和谐的色彩。
阿荨一愣,本能地回答了他一句:“谢谢你救我。”
当时糊里糊涂,只知道有人握住了她的手,把她从死亡中拉了回来。现在又好好地活着,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而守在自己的身边的人又是祁钰,她当然明白是他救了自己。
祁钰挑眉,眸光微动,声音一下子变得淡淡轻轻的,如羽毛拂上脸时的柔软,极具诱惑。“怎么,你还打算要报答我?”
“是啊,我当然要报答你。”阿荨认真的说道,水眸轻盼,灿灿生辉。
祁钰沉默了半天后,忽地咳嗽一声,开口说道:“那你就一辈子跟着我吧。”
阿荨心一怔,抬眸:“做跟班,还是奴婢。”
祁钰笑,叹口气道:“你只想做跟班和奴婢吗?也好,等你身体养好了,你就好好地报答我。我是怎么照顾你的,你以后也这么照顾我。”
“好。”阿荨说道,她知道他很用心地照顾她,所以在没有把姐姐找回来之前,她就代姐姐照顾他好了。
“你离开梁宫的时候,没有拿解药。我替你拿了。”祁钰说道,将一个暗红色的药拿放在了阿荨的面前。
解药?梁成君在殿内的时候告诉她,她给了上官景,等梁公主与荆少棠成亲之后,上官景自然会将解药给阿荨,可是上官景最后的目的是让自己死。
祁钰居然从上官景手里拿到的解药?“你是怎么拿到的?”阿荨问他。
“总之,你不应该死。”祁钰怔怔地看着她,眼中的清澈依然粲如星辰低垂。
阿荨张了张嘴,欲言又止,姐姐事情,还有庄儿的事情,她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他,荆绛蓉不见的日子里,她也仔细想过,如果不是有人故意要劫走姐姐,而是姐姐自愿地跟人走呢。
姐姐难道不愿意见到祁钰,每次阿荨在荆绛蓉面前说到祁钰的时候,荆绛蓉总是闪烁其词,赶紧将话题引开。
“你想说什么?”祁钰细细打量阿荨一眼,淡淡地问道。
“没什么?”阿荨垂眸。
等抬起头来之时,一只药碗已经在她的眼前了。女子秀眉一皱,语气微嗔,将面前的药碗推开,咬唇想半天才问道:“有没有药丸?我不喝药汁,太苦了。”
“这些天,你都是这么喝的,也没听你说苦。乖,喝吧。”祁钰哄道。
阿荨定定地望着他,有片刻的失神,三哥也是这般哄她吃药的。可是现在三哥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些天她咽到肚子里的药原来都是祁钰一点点地喂进去的?一想到自己浑然不知,肯定也知道了祁钰喂药的方式,原本苍白的脸色一红,淡淡的红晕染上脸颊,看起来明亮又柔美。
见祁钰拿起手里的药碗往自己的唇边放去。阿荨赶紧道:“其实也没什么?我自己能喝。”
他对她好,她承受不来。
深夜,房内的烛灯被点亮,阿荨动了动身子,感觉到有些力气了,起身下了床。盯着桌上的药盒看了许久,缓缓地走过去,拿到了手上,打开了盒盖。
这就是解药吗?女子唇边浮现一丝苦涩的笑意,三哥都已经不要她了,她一无所有,就算活着又能怎么样呢?
耳边突然又响起了宣婵的话:“活着总有会希望的。”
可是阿荨却觉得希望是如此的渺茫,她真害怕等不到,她真害怕不能信。
一阵风吹,吹得阿荨的身子依着桌沿软软下滑,思绪凝滞,心不知所想,似是害怕和无助,又似是钻心的酸痛难耐,种种情绪压满胸口,堵得快要窒息,抱膝抱臂,整个人蜷缩躲在了桌台的阴影下,瑟瑟发抖。
手心里的药丸渐渐滑落在地,慢慢地在地上滚动着,突然停在了门口。
祁钰推门而入,望着蜷缩在地的阿荨凝视许久,眸色一瞬似有些恍惚。男人慢慢地蹲下身子,捡起了滚落在他脚边的药丸。
她竟然将解药扔了?她就这般绝望,这般不想活吗?
祁钰叹了一口气,走近阿荨,依着她的身子也跟着慢慢地蹲了下来,柔声问道:“为什么?”刚才还说会报答他的救命之恩,这会儿就不愿意活了?
“祁钰哥哥,三哥把我丢了……他不要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我竟然什么也没有……”阿荨抬眸,深深呼吸了一口气,明明伤心欲绝,却是强忍着眼睛里的泪水。
她终于是说了过来,他以为她什么都不说,便是什么也不在乎了。
“我既救你,就说明你的命不该绝。”祁钰抬起她的脸,朝她低低地吼道。眸间流转着一种痛苦的色彩。
“不要……管我,求你……”不要管她,让她就这么安静的呆着好吗?
“乖,心里难受就哭出来,好不好?”他的眼里似乎满是心疼和着急,眸子已不再明亮,而是盛满了无止境的晦涩深沉。
阿荨拼命的摇头,不哭,不哭,三哥说不喜欢她哭,不喜欢她伤心,他希望她永远都是开开心心的。可是却是三哥亲手将她的梦想夺去的。
“阿荨……我不管他对你做过些什么,可是从今往后,你要忘记他!他一个卑鄙的小人。”
“住口!”阿荨突然吼道,“不许这么说他!”
“怎么说他?我没说错,一个抛妻弃子的人,难道不卑鄙吗?”祁钰紧紧地抓着阿荨胳膊,认真又霸道地凝视着女子憔悴痛苦的脸庞。
阿荨突然揪着他的衣襟,眼神冷锐异常,如一只崩溃至极,面临死境的豹子般,“什么抛妻弃子?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祁钰侧眸,掩掉眼里的不自然,放轻了声音说道:“没什么意思?如果你有怨,有恨,你就应该活着去报仇!”
“祁钰哥哥,你说得清楚一点。”阿荨何等的聪明,那天在雪地里鲜红的血水慢慢地从身体里流出,而她身上并没有被上官景射上的箭伤,那温温热热的感觉,她记得。虽然当时已经到了半昏迷的状态。
“如果你答应我好好地活着,我就会告诉你!”祁钰开口道,她难道就宁愿沉浸在无边的悲伤下麻痹自己,再不醒来吗。
阿荨抬头,蓦然,唇上忽地一热,有湿润的柔软在那里轻轻地磨蹭。
女子目光却落入那双再熟悉不过的眸子,而那双眸子此刻正担心地盯着她,与她相对不过勉强一丝空气可流动的距离。
祁钰紧紧抓着阿荨的手臂,轻轻地吻着,细致缠棉,男人的舌尖慢慢揉抚过她的双唇后,轻易地便抵开了她紧咬的牙关,不紧不慢地挑豆勾引着她闪避逃躲的舌尖,一点一点地纠缠上来。舌尖相触时,一股微微的苦涩慢慢地融化在阿荨的口腔里。
阿荨瞠眸,看着他,那解药已经被他就这么轻易的喂了下去。
慢慢地血腥的味道涌了上来,祁钰微微地蹙眉,原来解药的毒性也是这般大,一时觉得一股内力在体内冲撞,任血水流下唇角,却不愿意放开阿荨。
他狠狠吻了过来,动作霸道狂暴。这一次不复温柔,唇舌相触狂野热情,诉尽着无边的痛苦和相望的无奈。
阿荨的脑子里一下轰地炸开,回神,忙急得伸手推他,终于哭了出来:“为什么,连你也要欺负我!”
祁钰离开了她的唇,抚上女子的后背,轻轻地,一下一下。男人低低地说道:“哭完了,就乖乖地给我养好身子做我的贴身奴婢。”
“嗯……”阿荨放开了心,在他的面前放任自己哭得厉害,一直哭到停不下来,扶在他的身上睡着过去。
这日,天气虽寒,却是阳光和煦。
诸葛流云只是淡淡地看了祁钰一眼,说道:“你也没什么事,她身上中了红颜错的毒,是因为你而中的,解药也是巨毒,本是以毒攻毒。你身上还有红颜错的余毒,所以那药对你没什么伤害。”
祁钰负手而立,任寒风吹起身上的墨色长袍,沉默不语。
“看来你对她也是用尽了心。”诸葛流云抬头,开口道。
“流云,你说看到她痛苦,我的心也会痛,是为什么?”祁钰扭头,望着他。
“那绛公主呢?”诸葛流云不怀好意的问道。
“我也不知道,可是一想到绛儿,我也会心痛。”却不及亲眼见到那个丫头,心痛得那般深。
“你看到那丫头痛苦,你也难受是因为,那红颜错的毒无意之中让你的心牵上了她的心,好像中蛊一样。不过绛公主可是你守在心里十多年的女人,你要一下子将她忘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只是个大夫,管治病,不懂你们感情的事。”诸葛流云淡淡地说道,站了起来。
祁钰扬了眸看向诸葛流云,脸色冰寒似雪清冷。
倏地,彦三急急地走了过来。见到诸葛流云之时,脸色一怔,正想开口说话,顿时,停了嘴。
诸葛流云耳力极好,听到脚步声,便知道是谁,开口说道:“彦三有什么事就直说,难怪还怕我是奸细不成?”
祁钰抬眸看了一眼彦三,点了点头。
彦三站在原地开口:“梁皇突然病倒,梁宫大夫已经被处死十几个了。”
“梁皇好好的,又怎么会病倒?”祁钰锐利的眸子里锋芒隐隐。
“这个属下也不知,据说毒王和药王都不在梁国,青衣侯世子已经派人四处去寻找,皆无消息,似乎是知道梁皇会病倒,故意在之前就已经离开了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