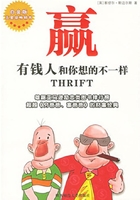“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被你们蒙在鼓中,墨渊就算真的想要致鸾儿于死地,也该给鸾儿一个理由,不是吗?”鸾歌一双凤眸流转,目光紧紧逼视着眼前的阿寂,“身为受害者,我难道没有理由知道真相吗?”
“你想要知道什么?”阿寂冷哧,“你所谓的真相,就是你一次次将主人往绝路上逼!”
“阿寂……别这么说。她只是个孩子,这并不关她的事。”少年在睡梦中挣扎了一番,手指蓦地动了动,紧接着他的眉头微不可查地蹙了蹙,随即狭长的眼眸微微睁开,望了一眼身侧的鸾歌,右手无力地抚了抚她的掌心,纤长的手指冰得刺骨,“鸾儿,有些事情是墨渊做得不好……咳咳……或许让你有所误解,但是绾依是南北两朝的和亲公主,你抓她来逼墨渊现身,于法于理都不合。”
鸾歌感觉到握在掌心的生命稍纵即逝,一时间竟舍不得厉声质问,而是伸手柔柔地抚了抚少年蹙起的双眉,目光清冷道:“那些事情等墨渊养好身子再说罢,但在墨渊养好身体之前,不可以再随意将鸾儿丢弃。鸾儿并不是件物品,说丢就丢,墨渊你无权这么做。鸾儿没有什么能力,但甄绾依服了我下的毒,需要按时服用解药,若是墨渊离开,鸾儿便断了她的药!”
“郡主,你这么做,对主人不公?”阿寂愤恨地拔剑,直指鸾歌纤细雪白的脖颈,“主人真是白救了你!”
“叔父要致青鸾丫头于死地,青鸾丫头不过是想要个答案,有什么不公?觉得不公的应该是青鸾!”墨弘得知墨渊归来,匆慌赶到,见阿寂咄咄相逼,自然忍不住帮着鸾歌出头。
鸾歌清眸扬起,傲然反视:“弘哥哥说的不错,如果墨渊有什么苦衷,阿寂不妨说出来。鸾儿不是不讲理的人,如果答案我能够接受,我自然不会责怪墨渊。”
“责怪……呵!”阿寂的嘴角挂着讥讽的笑意,“青鸾郡主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也配在主人面前提‘责怪’两个字吗?你凭什么责怪他?就凭他三番四次救了你吗?”
“咳咳……阿寂。”僵直着身子躺在轿撵上的少年急于阻止两个人的争吵,一口气不来,急急咳嗽出声,洁白的手帕瞬间染成了血色,妖冶的一片,触目惊心。
“墨渊!”
“主人!”
两个人冲到少年身边,阿寂从轿撵上将墨渊背起,一面向着里屋冲去,一面急切嚷嚷:“快让开!主人吹不得风!”
鸾歌自然知道大局为重,忙吩咐红鸢替甄绾依松绑,趁着大伙儿都关注宁王归来注意力被引开之时,偷偷命人将昏迷中的甄绾依送回了无人关注的西苑。
阿寂一进屋,便将房门反锁。
“郡主好生在外面呆着,属下怕放你进来,主人最后半条命也会被你要了去!”
墨弘的双拳早已紧握,阿寂居然锁门,他更加不满,怒道:“丫头,不用理会那个奴才,找人来砸了这门!本王就不信,这屋子我们进不得!”
鸾歌点头,故作气势汹汹:“阿寂你快开门!你再不放我们进去,我命人砸了门窗!”
“青鸾郡主如果真的希望主人死,阿寂无法可说,要砸便砸!”屋内传来影守冷酷的回应,语声决绝,不给鸾歌半点希望。
“来人……拿斧头来!”墨弘愤怒地双眸泛红,蠢蠢欲动。
“等等……”眼见着墨弘手上的斧头就要落下,鸾歌又忙伸手扼住了他的手腕,长长叹了口气道,“算了吧。”
“丫头,你这么轻易就原谅叔父了吗?他招招相逼,都是要致你于死地……你还要维护他?”墨弘原以为鸾歌对墨渊已经死心,想不到她终究还是不忍。
是啊,她还是舍不得对墨渊狠下心来。
鸾歌急于掩饰自己的情绪,冷然一声笑:“弘哥哥,这里是赵府,我不希望别人说我们南朝人没素质。等他们半日又何妨?这屋中无水无粮,他们终归是要出来吃饭的。”
“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墨弘越来越摸不清这丫头的心思,似乎从崖底获救之后,她整个人都变得极度清冷,不易亲近。
“当然。”低头,她的目光不敢对墨弘对视,生怕他看出她心底的懦弱,慌张瞥向一边。
鸾歌原先是真的想按照墨弘的意思命人砸了门窗冲进去质问,但心中始终惦念着墨渊的病,这样做不过是惊扰了墨渊养伤,倘若墨渊一直不肯说出真相,她就算是冲了进去又有何用?于是她默默蹲在门口,静静守着。
“丫头,你好几日不吃饭了,多少吃些吧。你若是要看着叔父,我可以替你在门口守着,绝不让他无故离开。”墨弘眼见着那丫头这几日清瘦了许多,原先圆乎乎的娃娃脸变成了细长的瓜子脸,气色也大不如从前。
“弘哥哥,你觉得我吃得下吗?”鸾歌冷声反问,“如果我吃不下,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去吃呢?就算我吃下去了,也会吐出来,苦水在心中逗留的感觉,不是更痛苦么?”
墨弘恍然,这样的丫头让他觉得有几分陌生,虽然都是些歪道理,但听来也不是完全不对。“吃不下的话就不吃了吧,但是在这儿干等着也不是个办法。到院子里走走,散散心,也许想不通就都想通了……”
“不了,我想在这儿呆着,这样我会比较安心。”鸾歌忽而收了一脸正经,露出粲然笑意,两颗大门牙故意在墨弘面前一晃一晃,“你不知道,真相即将揭开,我有多兴奋。就像玩了一场悬疑推理,我已经抓住了凶手的尾巴,只等揭开他的真面目。”
墨弘知道她只是强颜欢笑,走近鸾歌身边,倚着门窗,贴着她身子一侧坐下:“不如就让我陪你一起揭开他的真面目吧?”
屋子里,一片死寂。
少年安然盘坐在床榻上,双眸紧闭,两颊微微泛出不正常地浅红色,指节苍白附于膝上。他一向都是那么安静,静得好似冷漠的玉石,可其中的精妙只有阅人无数的老手才能猜透。
阿寂正坐在他身后,耐心地替他运功疗伤。
从悬崖上坠下,少年身上有多处割伤,在寒潭中浸泡了好几个时辰,冰冷的潭水与残留在他体内的假红花同属凉性,两者相互作用,使得少年原本残破不堪的身体濒临崩溃,一直冷傲的姿态轰然倒塌。
“阿寂……别白费力气了。”少年的唇角翕动了一下,推了推阿寂,拒绝再接受他输来的真气。“我的体质就好似一个无底洞,你这么给我输真气根本毫无效果。”
幼时因为体质偏冷,总是大病连连,得母后疼爱,墨渊看了无数武学心法,用于强身健体,却不料自己天生就是武学奇才,七十二般武艺全都熟记于心、融会贯通,武功早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阿寂虽然身为他的影守,也仅仅是因为他身强体壮,加之武功拔尖,可以帮他做很多事,并不代表他真的需要阿寂来保护。
他的伤必须功力在他之上的人才能治,阿寂这样输真气,根本就是有进无出。
“唤鸾儿进来吧。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再也没有必要瞒她。她远比我想象中还要固执,若是我始终不说出真相,她怕是更伤心。”少年淡淡吩咐,褪去身上已然染血的衣衫,重新换上一件大红色的外袍。因为这袍子拥有着和鲜血一样的艳红色,那孩子就看不到他在流血,知道真相之后也不会那么伤心了。
“主人先歇下吧,属下出去跟青鸾郡主解释。”阿寂实在心存不忍。眼见着墨渊忍受病痛十多年,而今又是十多年来受伤最严重的一次,任人难以忍下心中的恶气。
“也好。”墨渊微微阖上眼眸。甄绾依还没有接受册封,南北两朝还未结成秦晋之好,他现在还不能死,他需要休息……他多想再见一面那牡丹丛中的女子,一眼就好。
阿寂扶着少年躺下,这才开了门锁,瞧见一直守在门外的女童,心中五味杂陈。
“你总算是出来了。为什么不见叔父?”见阿寂出门,墨弘冷眼相对。
鸾歌扬起眼眸,见阿寂没有拔出诩阳剑,明白他不是为了出来与他们争斗,于是好声问道:“墨渊的病,怎样了?”
不提墨渊的伤还好,一提起这个,阿寂对眼前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六岁女童是满腹的憎恨:“青鸾郡主,你不配知道。”
“我是他的亲外甥女,我不配知道,谁配知道?”鸾歌压低了声音反问,生怕惊扰了屋里病重的少年。他对她不仁,她却舍不得对他不义。
“郡主从来都没当主人是墨渊,不是吗?”阿寂不甘示弱,冷声反问。
“不错。”她确实没当他是墨渊,她希望他们的感情可以超越亲情,可如今连那么点微乎其微的亲情都快消磨殆尽,何谈爱情?
“我们出去说。”怕影响到主人休息,阿寂一手狠狠扣上了鸾歌的手腕,三两步翻上墙头。
“放开她……”墨弘见情况不妙,想要出手阻止时已经来不及,忙厉声斥道,“若是你不放开青鸾丫头,本王就带兵冲进屋里,到时候惊扰了叔父,别怪本王手下不留情!”
阿寂回眸望了墨弘一眼,冷冷威胁道:“皇长孙试着靠近这屋子一步试试,只要主人有什么三长两短,属下一定会拉着青鸾郡主,为主人陪葬!个中利害,皇长孙心里仔细掂量掂量!”
“弘哥哥,你放心,鸾儿一定能平安回来。”鸾歌朝墨弘微微一点头,墨弘这才不甘罢手。
兜兜转转,阿寂带鸾歌去了狩猎那日鸾歌坠崖的地方,也不知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鸾歌却越发觉得他是刻意为之。
“郡主认为,这悬崖高吗?”阿寂放开鸾歌,执剑指了指那无底的深渊,问得毫无头绪。
鸾歌那日因为慌乱中骑马逃至此处,并没有注意到那悬崖竟然高达百尺,站在悬崖边上,她渺小得如同蝼蚁,于是颤声答:“高。”
“若是凭白无故,让郡主只身跳下去,郡主敢吗?”阿寂似乎对鸾歌的答案比较满意,又抛出另一个问题。
“不敢。”当然不敢,即便是那日在绝境之下,若不是墨渊朝着她胸口补上一掌、推她坠崖,她是宁愿死在他的匕首下,也不可能纵身跳入这万丈深渊。
阿寂目光一黯,冷冷指了指鸾歌身后的深渊:“郡主不敢跳,可是主人敢。主人就是从这里跳下去,才落了满身的伤!为了救郡主,他几乎是本能的跳下去,不假思索!”
“可是……墨渊完全没有必要跳下来。”鸾歌想不通,墨渊为什么要跳下来,为什么要救她,他不是想要杀她灭口吗?他不是知道她杀了赵澈,怕她连累他吗?
“倘若主人不跳下去,郡主以为你还能活到现在?蜜菁虽然能妙手回春,可是对死人却是丝毫不起作用的。主人当初若是没有跳下去,青鸾郡主你现在就是一具冰冷的尸体。”阿寂冷冽的眸光射向鸾歌,“主人为郡主受伤,郡主又凭什么责备主人?”
“那日……救我的人不是东方楚吗?”怔怔望着阿寂,鸾歌几乎本能的问出来,“我活命与墨渊有什么关系?”
“呵……”阿寂冷笑,“东方楚?你出事的时候,东方楚还在林子里狩猎,倘若真的等他赶来救你,你恐怕早已血尽而亡。”
“这么说那日跟着我一起跳下来的人是墨渊,在我昏睡中,照顾我的人也是墨渊?可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所说的话。”鸾歌一脸质疑,东方楚为了救她受了重伤,那是她亲眼所见,还能有假?
阿寂似乎早料到她会这么问,从怀中掏出一柄匕首,递到鸾歌手中:“你仔细看看,这把是不是伤你的匕首?”
鸾歌接过匕首,眉头紧蹙,重重点头,“不错,就是它,它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中,它就算是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
“当日郡主坠崖之时,匕首并没有被拔出,但是获救之后,匕首已经消失不见,郡主不觉得奇怪吗?”阿寂反问。
鸾歌仔细回忆,东方楚确实带人入山谷寻找过这把匕首,但几番查探,都未能找见。
“因为替郡主拔刀止血的人是主人,匕首自然是主人带走的。主人带走了匕首,东方楚自然找不到!”
鸾歌被阿寂搞得晕头转向,“既然墨渊要救我,那他为什么还要刺我一剑,将我推入悬崖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主人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却说他所做的一切多此一举,真是叫人心寒。”阿寂不禁感叹,“属下曾经说过,郡主能够九死一生,那是经历过无数次刻意的演习的。不错,杀郡主的人是主人,救郡主的人也是主人,主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治愈你的左耳!”
“我的左耳……”鸾歌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耳朵,她的耳朵确实在蜜菁的治疗下重新听得见了,可是……这其中一些枝枝节节,她总是想不通。
“没有蜜菁,郡主的左耳怎么可能好得这么快?”阿寂冷声反问,见鸾歌无言以对,又接着说下去,“主人特意设了这个局,为得就是骗出东方楚手中的蜜菁。想必郡主不知道,郡主的容貌与东方楚失散多月的义妹木妮娜如出一辙,东方楚若是看到奄奄一息的你,自然舍不得你死。因为主人清楚东方楚对木妮娜的感情,那样的情感早就超出了兄妹,所以主人才出此险招。”
鸾歌怔怔地望着那一望无底的悬崖,想到墨渊那弱不禁风的身子曾经从这里坠落,心就止不住的颤抖,真相面前,果真如阿寂说的那样,她甚至连眼泪都流不出。
“当日在寒潭底下抱着郡主的人是主人,替郡主拔剑止血的人也是主人。主人趁着东方楚赶到之前离去,偷偷躲进树丛,直到确信东方楚喂着郡主吃下蜜菁,这才黯然离开。”阿寂回忆起那日的一幕幕,心中对鸾歌的厌恶感不是一点两点。主人受重伤躲进了树林,而那个丫头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居然是为东方楚“献吻”解渴……反反复复。
“那东方楚腿上的伤……”鸾歌还想问些什么。
阿寂似是出于私心,故意挑拨离间,“谁知道他是怎么受伤的?他是北朝尊贵的四皇子,怎么可能不顾忌自己的生死,为了个不知名的女童,从那么高的悬崖上往下跳?依我看,那分明是他使得苦肉计!”
鸾歌被真相击得节节败退,好不容易竖起的外壳,瞬间倒塌,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情感,她愤然指着阿寂,怒斥:“墨渊这么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阻止?你知不知道,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会要了他的命?”
“属下阻止过!原先演习的时候,都是有属下在做。属下功夫不如主人,但身体强健,从悬崖上跳下去除了皮肉擦伤,根本不碍事。可是正是因为属下的功夫不及主人,在最后一刻,主人才决定亲自出手!”阿寂双拳紧握,狠狠砸在地面坚硬的石块上,留下一道道清晰的血痕。“我只恨自己武艺不精!”
“为什么……”鸾歌双腿一软,跌坐在地面上。
“匕首要插入郡主的胸腔,又不能伤及心脉,造成致命的假象。用野马演习的时候,属下曾经失手过一次,凭白无故害死了一匹野马,主人担心我再次失手,所以便坚持要亲自出手……”阿寂缓缓解释,合情合理,让鸾歌不得不信。
“就算墨渊要亲手刺伤我,你还是可以代替墨渊跳入崖底的……”鸾歌迷离的一双凤眼,轻灵的眸子里蕴满了水汽,“这样墨渊就不会受那么严重的伤。他为什么要亲自跳下来呢……”
“崖底是寒潭,主人的水性也比我好。”如果可以,他当然愿意代替主人受伤,他能有今日,全靠主人一手提拔。
原来墨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好,她曾经也坚持过,曾经也想信任他,可终究她的心还是在令人绝望的假象下动摇。
“墨渊是什么时候想到这个计划的?”
阿寂略加思索,答:“未出南朝都城的时候。”
“这么说,墨渊早就知道我藏在他的马车内?他还佯装发怒,让我以为得逞,却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进他布好的棋局……”
“不错。主人同意让红鸢随行,其实是为了让她替郡主引路,诱惑郡主藏入车队。”
阿寂的话语重重击在鸾歌心头,每一句话看似漫不经心,那人却是幕后费了无数心血。
那样年轻的墨渊,弱不禁风的少年,他的心机究竟有多重,日日夜夜被这些琐事所困扰,他能够安眠吗?
鸾歌胸腔内紧紧揪着的一根弦,瞬间断裂,蕴满泪水的眸子定定望着地面,一眨不眨,深怕动一动眼睫,泪水就会似断了线的珍珠一般,不断砸下来。
良久,她平复了自己的情绪,漠然走到阿寂面前,平稳向他伸出手:“对不起,我不该失控,不该对着你胡言乱语,更加不该斥责墨渊。我为我的无礼向你道歉。请你告诉我,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墨渊?”
“主人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来北朝的,他唯一的愿望不过是希望看到甄绾依平安嫁给东方墨,促进两朝友好,免得陷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阿寂从未说过这么多话,作为影守,他一直就像是墨渊的影子一般,静默无声。
“我虽然任性,但也明白两国友好的重要,甄绾依只是中了我的迷香,没什么大碍,明日册封大典,可以照常举行。”鸾歌正了正衣襟,又道,“原先不是说用‘秋泽’入药,可以治愈墨渊的心疾?”
“凉性的潭水已经激发了主人体内假红花的药性,即便现在找到‘秋泽’,也无法根治主人的病,只能用来续命,除非……”阿寂的眼眸眯成一线,手下微微用力,锋利的诩阳剑狠狠刺入地下坚硬无比的巨石,发出绚烂的电光。
“除非什么?”只要有一丝丝希望,鸾歌都不愿放弃。
“除非有蜜菁,可是这世间蜜菁只有一粒,主人已经亲眼看到东方楚喂郡主服下。”阿寂愤恨地舞剑发泄,鸾歌则僵立在原地,惶然无措。
“墨渊为什么要这样……我的耳朵聋了无所谓的,他难道不知道我把他的命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么?”鸾歌狭长的指甲嵌入掌心,直到手心里有血红色的液体漫溢出来。
“主人一直在为郡主左耳失聪一事自责,若不是当初主人病发,未来得及向长公主解释小郡王一事,郡主的耳朵根本不会受伤。主人一直想要补救……”阿寂不再说话,鸾歌也能明白这沉默背后所暗含的东西。
“如今只有找到‘秋泽’,才能为主人续命。‘秋泽’在东方墨的宠妃李贵妃手上,可为了两国友好,主人是万万不可能开口向东方墨讨要‘秋泽’的。”
“为什么不能?东方墨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鸾歌不解,她是见过东方墨的。他气质不凡,高贵脱俗,有帝王之风范。
“‘秋泽’又名‘诞子’,可以调养女子的身体,李贵妃万千恩宠,却始终无法产子。东方墨特意将‘诞子’赐给她,是希望她早日为北朝产下小皇子。要知道君无戏言,东方墨又怎么可能向李贵妃要回‘秋泽’?”一想到主人病重,阿寂心中不好受,剑光飞舞,肆意发泄,砸得四周的碎石翻飞。
希望落空,鸾歌却始终不肯放弃,上前一步,也不顾迎面扑来的碎石,直直走到阿寂面前,紧紧握住他握剑的右手:“只要墨渊还有一口气在,我都不会放弃,你也不应该放弃。现在请你带我回赵府,能不能要到‘秋泽’,还得问一问一个人!”
“谁?”
“东方楚。”
东方楚是东方墨最疼爱的儿子,他一定有办法拿回‘秋泽’。如果东方楚此时病重,又只有‘秋泽’可以救命,东方墨自然会不顾李贵妃的感受,而选择救东方楚,到时候他们就可以拿到‘秋泽’。尽管鸾歌心如明镜,但她却没有十足的把握,东方楚会不会愿意帮她。
“阿寂,我问你,木妮娜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灵光一闪,计策心生。
“她会跳惊鸿舞,就是那日郡主在宫宴之上所跳支舞。”阿寂狐疑地打量着鸾歌,他从来都不相信六岁的女童能够跳出那样惊艳的舞蹈来,可怕的是鸾歌做到了,而据调查,擅长惊鸿舞的木妮娜也仅仅六岁。舞姿之柔美,非人能比,就好似天上的仙女。
“那么,就让我再为他跳一曲惊鸿吧。”鸾歌目光明亮。那日慕容青鸾的舞步,她早已默默记下,原本只是因为喜欢,如今看来,总算派上用场了。
“阿寂,你现在就带我回赵府,并派人帮我找一套鲜卑族的女子长裙来,我要改头换面。”鸾歌握紧了阿寂的手,目光坚定,“能不能救墨渊,就在此一举了。”
阿寂虽然不明白这个女童究竟要做些什么,但看她对主人的心意不假,于是迅速收剑,手臂在鸾歌腰间轻轻一带,两个人便飞檐走壁,很快回到赵府。
彼时,墨弘已经在墨渊门前守了半天,天色已经不早,黄昏将近,眼见着阿寂带着女童安然归来,他心中的焦虑终于消散。
“丫头,你可回来了,没事就好。”墨弘注意到鸾歌的眼睛红通通的,似是哭过,但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好出声安慰。在她面前,他就像个单纯傻傻的大男孩,见不到她的时候会十分想念,但是当她就站在自己面前,他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切都变了味,或许当日在南朝皇宫内六角楼前面的那方水塘前,他不该……
那天,他只是一如既往地在六角楼垂钓而已,却看到斜刺里冲出一个女童。那女童纯真的眸光中蕴满了坚定的决心,这寂寂深宫,几乎所有人的眸光都已经浑浊,而那个孩子的凤眸依旧清澈,那样特别,揪着他的一颗心。
他偷偷跟在那孩子身后,趁她手忙脚乱之际推了她一把,害她滑落水中,自己再上演一出英雄救美,成功结识了她。也许,到现在她都不知道,他遇见她的第一面就已经对她使坏。
正当他出神之际,鸾歌已经与阿寂一道进了墨渊的房间。
床榻上,少年微微阖着眼眸,一听到动静,便知鸾歌归来,他嘴角轻轻翕动了一下,唤鸾歌来到他床前。
“墨渊,鸾儿在。”鸾歌方才的清冷在少年面前褪得一干二净,温顺得像一只绵羊,倚着少年的手臂,将少年的右手温柔地贴上自己的侧脸,暖暖道,“墨渊真傻,鸾儿从来就没有在意过自己的左耳……”
“傻孩子……”墨渊清瘦了许多,侧脸的轮廓更加俊朗,脸上的那道疤痕经过良药的调理已经渐渐淡化,几乎看不到任何痕迹,他伸手下意识地探了探鸾歌的额头,强扯出一抹笑意,“墨渊又没有怪你,你哭什么……”
听他微弱的呼吸,鸾歌一直含在眼眶的泪水终于决堤,豆大的泪珠砸下来,一颗颗全都砸在了墨渊心上。
早知道这孩子知道真相会受不了,可为了甄绾依能够平安出嫁,他不得不现身,不得不将一切告知。或许,他这么做不值得,可至少心里对那孩子的愧疚会少一点……
“鸾儿不哭,鸾儿不哭……墨渊会长命百岁的,墨渊是南朝的储君,天之骄子,真龙传人,哪有那么容易……反正我不管,墨渊一定不能抢在鸾儿前面死。”鸾歌的声音哽咽住,再也说不下去。她的左手紧紧握住少年的右手,十指紧扣,就好像握着一生的希冀。
“墨渊有些累了。”少年叹息了一声,于鸾歌他已经尽力,不会再有愧疚感,可是于他自己,他却仍有遗憾。那副精美的洛阳牡丹图还藏在南朝宁王府的墨台之上,牡丹摇曳生姿,可种植那牡丹的女子却再无机会与他相见……
“墨渊你睡,鸾儿在一边陪着。”鸾歌贴心地替少年掖好被角,伏在床榻边上,怔怔望着少年微微闭上的眼眸,看他细密的长睫在阳光下一眨一眨,好似轻薄的蝉翼翕翕合合。
此时,她有一种冲动,想要吻他的冲动。
如果说第一次吻上他,是因为巧合,那么她希望认真地再吻一次,清清楚楚地闻一闻他身上的香味,碰一碰他薄薄的唇瓣。
星座运势上常说,唇瓣薄的人薄情,墨渊的唇瓣也很薄,可他怎么会薄情呢?不论亲情、爱情、友情,甚至是主仆之情,他都看得那么重。
“墨渊。”鸾歌低低喊了一声,没有得到回应,这才确信墨渊已经入睡。
她深吸了一口气,大胆伸出食指,微不可查地在自己的唇瓣上碰了碰,而后又迅速地附上少年的唇瓣。她指尖的温热感与少年薄唇之上淡淡的凉意瞬间融合,化作奇妙的触感,似有电流闪过。鸾歌贪恋这一刻的美好,可少年的眉头却微微蹙起,她惊得慌忙收回了手指,放在衣袖下,两手不安的搅动。
“发生什么事了吗?”匆匆进门,准备好鲜卑族服饰的阿寂觉察到鸾歌的异常,忙上前询问,“是主人出什么事了吗?”
鸾歌没想到会被人撞见,双颊羞得通红,口中只得支支吾吾道:“没什么事……我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阿寂像与她较真似的,想要问出个所以然来。
“我只是等这服饰等得急了!”鸾歌一把抢过阿寂手中鲜卑族长裙,朝着自己身上胡乱套。
阿寂忍俊不禁,待鸾歌的脑袋从袖口露出来,他才嗤笑出声:“郡主,你穿裙子的方式……”
“怎么了?”鸾歌瞪着一双轻灵的眼眸望向他。
阿寂干咳两声,伸手将她的脑袋从袖口按下去,又从领口拎出来,替她理好裙摆,才笑道:“也没什么,就是你穿裙子的方式,比较特别。”
鸾歌尴尬得望了望自己的衣衫,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方才阿寂突然进门,她真是吓了一跳,太紧张了,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连裙子都穿得乱七八糟。
“郡主……”阿寂的目光却一直落在她身上,久久不能离去,也难怪东方楚对木妮娜难以忘怀,这鲜卑族的长裙将鸾歌娇小的身躯衬得更为灵动,那民族风别致的花帽更是将鸾歌的圆圆脸修得细长,原先只能算得上清秀的一个人,瞬间变成了倾国倾城的小妖女,谁人不心动?
“怎么了?”鸾歌却一脸好奇地望着阿寂,目光直直地盯着那个一向寡言的影守,直到阿寂的侧脸也似火烧云般羞得通红。
鸾歌走到梳妆台前,仔细照了照镜子,对这样的改变颇为满意。换了件服饰,她整个人的气质都完全变掉,脱去了娃娃脸的稚气,别有一番风韵。
“阿寂,我要你收买的人,你做得如何?”鸾歌问。
“一切都已布置妥当。”阿寂默默低下头去,他也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小伙子,见了漂亮姑娘,谁人不思春?
“很好,我现在就去见东方楚!”鸾歌抿了抿唇,走到少年床榻边上,轻轻叹息了一声,双手合十道,“墨渊,你一定要保佑鸾歌,保佑鸾歌完全记下惊鸿的舞步!不要让东方楚看出破绽!”
说罢,鸾歌转身,推门出去。
墨弘正杵在门前赌气,也不知这丫头究竟是怎么了,居然对他不理不睬,是不是只要叔父一回来,他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
“丫头!”墨弘朝着鸾歌叫了一声,鸾歌却恍若未闻。
阿寂跟在她身边,撞见墨弘便笑道:“皇长孙定是认错人了,这位是姑娘只是与青鸾郡主长得相像而已。她是雪域的格桑花,木妮娜小姐。”
“木妮娜?”墨弘长臂一横挡在鸾歌面前,眼前的人分明与那丫头长得一模一样,阿寂为什么称她为“木妮娜”?
鸾歌朝着墨弘淡淡一瞥,清冷的目光令墨弘掌下一颤,忙收了手。眼前的女童确实与那丫头拥着极为相似的容貌,可两个人的气质却是天差地别。那丫头目光澄澈单纯,不会像她一样狠绝冷厉。那丫头从来都喜欢素朴的衣衫,不可能穿这种花花绿绿,全身集齐了五彩颜色的异族长裙。那丫头特别爱惜自己的一头黑发,怎么舍得将它们弯成发髻藏在那斑斓特别的花帽之中?
“皇长孙殿下,是吧?”鸾歌挑眉望了望他,用一种打量陌生人的眼光。
墨弘下意识得撇开视线,强自镇定问:“正是在下。姑娘有什么话要说?”
鸾歌一声冷笑:“我只是想请您让开,您挡了我的路。”
眼前的女孩给他一种莫名的压力,墨弘忙朝她笑笑,让开一条路来。
走开了几步,鸾歌才回头问阿寂:“弘哥哥,他认出我了吗?”
阿寂摇摇头。
鸾歌满意地点点头,伸手揽了揽遗落在花帽之外的几缕发丝,“如果连弘哥哥都认不出我,才与我相处几日的东方楚,必然也认不出我。”
阿寂却道:“东方楚确实与郡主只相处了几日,但他与木妮娜小姐却相处了好几个月!郡主当万分小心。”
鸾歌沉声:“我明白的。”
甄绾依已经失踪过一次,为了保护她的安全,东方楚也住在了西苑。他的势力遍布了整个西苑,相信连苍蝇都无法从他眼皮底下飞过。
鸾歌一番傲然姿态来到西苑,吩咐阿寂藏起来之后,才大大方方地走向东方楚的房间。在他门口犹豫片刻,故意踢翻了脚边的花盆,然后仓惶逃入院中。
院落之中是阿寂事先买通赵府侍卫为鸾歌准备好的琴师,鸾歌朝着琴师稍稍使了一个眼色,琴师便开始弹奏。
幽美的旋律响起,鸾歌的云袖轻摆招蝶舞,纤腰慢拧飘丝绦,随着音乐舞动曼妙身姿,似是一只蝴蝶翩翩飞舞,似是一片落叶空中摇曳,似是丛中的一束花。鸾歌随着风的节奏扭动腰肢,绽放自己的光彩,甜甜的笑容始终荡漾在小脸上,清雅如同夏日荷花,腰肢倩倩,风姿万千,妩媚动人的旋转着,连裙摆都荡漾成一朵风中芙蕖。那长长的黑发在风中凌乱,美得让人疑是嫦娥仙子,曲末似转身射燕的动作,最是那回眸一笑,万般风情绕眉梢。
琴音声声若泣,恰在此时,鸾歌灵敏的左耳感觉到有脚步声逼近,如她所料,东方楚果然被惊动,一路跟着她来到院落之中。
此时,天空中万里无云,就像是在云中以北的雪域,那种感觉让东方楚联想起与木妮娜在雪域嬉戏玩耍的日子。
鸾歌的目光时不时瞥向东方楚,见他看得入神,便跳得更加卖力。
琴声愈发急切,很快便进入了高潮。
她瘦小的身影引颈高歌,歌声清亮,杳然如空谷清音,足尖点花,翩然起舞,纤手微展,飞如惊鸿,大袖扬空,跃如游龙,长发如丝,半遮玉容……
这个无垠的天地是她一人的舞台,她长袖挥舞,踏云逐风,那般的潇洒无拘,如清莲临风,灵秀飘然。却似有千株紫芍纷纷绽放,灼灼妍华摄目。姿色绰约,莲步轻踱,举手投足间尽是柔情。轻纱随风而动,宛若花中之仙,夜间之灵。轻移莲步,纤腰扶风,凌波踏水,飘然而来。
再后来,鸾歌感觉到东方楚已经看得入神,她也慢慢体味了惊鸿舞每一个舞步之间的精妙,干脆朝着天空肆意地扔开了头顶的花帽。
她用她的长眉,妙目,手指,腰肢;用她髻上的花朵,腰间的褶裙;用她细碎的舞步,繁响的铃声,轻云般慢移,旋风般疾转,舞蹈出诗句里的离合悲欢。
一曲结束,鸾歌旋身来微喘,俏颜粉黛。
“木妮娜……”东方楚看得如痴如醉,怔然出声,伸手想要触及眼前那个似有若无的幻影。
眼见着他逼近,鸾歌冷冽的眸光怒目而视,随即推开了他伸过来的双手,想要往回奔,却没走几步,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木妮娜……真的是你,是木妮娜!你睁开眼看看,我是刘楚!”东方楚的生母贤妃姓刘,出门在外,为掩人耳目,他正常随母姓,遇见木妮娜的时候,他用得便是这个化名,以至于后来未能来得及告知她他的真名,两个人这才失散!
鸾歌事先服下了阿寂交给她的秘药,剧烈运动之后药性发作,正巧在东方楚面前晕倒。
“木妮娜,你说话?为什么不说话?”东方楚探了探她的脉搏,这才发现女童已然休克,瞬间一种惊慌感遍布了他全身,他将她仓惶地搂在怀中,一面往屋子里冲,一面高声喊着,“传太医!快传太医!”
鸾歌就好似一个没有生命地搪瓷娃娃,静静地躺在东方楚的床榻上。
东方楚守在她身边,一刻也不敢离开,直到太医匆匆赶来。
太医是前两日方才跟着东方楚进入赵府的,在宫中混了些年,治得都是风寒感冒那样的小病,每每遇到重症,他都束手无策,所以郁郁不得志。今日,有人为了指了条明路。
太医伸手为鸾歌把了把脉,故作深沉,朝着东方楚磕了一个响头道:“禀王爷,这位姑娘犯得是畏寒之症,并不好治。此病,时睡时醒,看似没什么大不了,但不经意中就可能要了她的性命。微臣开一服药,只能暂时压制她体内的寒性,王爷还要另想办法才是……”
“你快去!”东方楚急躁得很,一听木妮娜患了急症,心中极为后悔将唯一一粒蜜菁用在了素昧平生的青鸾郡主身上!
约过了半个时辰,太医带着丫鬟,将事先煎的药送进来,喂鸾歌俯下后,鸾歌果然转醒,皱眉望着东方楚问:“怎么又是你?”
东方楚的脸上终于微微露出了笑意,这确实是她的木妮娜,她对他充满了厌恶,并且喜欢将这个厌恶感发泄出来!
东方楚望了一眼身侧的太医,静默道:“我们出去说话。”
不用猜,鸾歌也知道他们要出去说些什么,大抵都是关于木妮娜的病情云云。
一出门,太医便伏跪在地:“王爷,那位姑娘的病老臣实在是有心无力,畏寒之症需要以‘秋泽’入药,放眼望去,整个北朝也很难找到一株秋泽啊!”
“秋泽……”东方楚默默念了一声,唇角抿成一线,旋即转身,“备马,本王要进宫面圣!”
待到东方楚走后,鸾歌这才松下一口气,迈出西苑,回东苑照顾墨渊。
走到墨渊的屋子门口,墨弘还干巴巴的守在那里。鸾歌心想自己用的还是木妮娜的身份,便不与他说话,兀自进了屋中。
墨弘静静地望着那个背影,嘴角微微勾起,方才的疑惑一扫而空。明明看着丫头进去,怎么可能出来的是木妮娜?那丫头还是一贯的古怪,可她爱搅手指的坏习惯总是改不掉。
既然她要玩,他也不拆穿她,配合着她演完整出戏。
鸾歌刚进屋子,红鸢已经等候多时。
红鸢手中拿了一副画卷,递到鸾歌面前,皱眉道:“有人将这幅画送到门口,指明了要交给王爷,可王爷还在昏睡,郡主觉得……”
不等她说下去,鸾歌接过那幅画,小心翼翼展开,美艳的牡丹图映入眼帘,却令鸾歌惊恐不已!
这画上的牡丹,红色的花瓣中夹杂着一点白,分明与墨渊藏在墨台的那副牡丹图上的牡丹是同一株……
虽然姿态各异,却看得出出自同一人之手。
“是谁送来的这幅画?”
红鸢不明白鸾歌望见这幅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应,如实答:“一个年轻女子,与我家王爷年龄相仿,生得极美,眼角还有一颗泪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