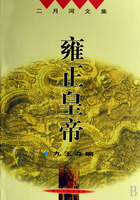金克斯的早间报道令人非常愉快。安德森先生想在休息室的沙发上打个盹儿,但是蟋蟀们的音乐大餐很快就把他赶了出去。他想去开车,可是用了半小时也没能把车发动起来,他只好打开车前盖查找原因。“弗莱迪,我还从来没听谁说过像他骂你的那些脏话。”金克斯说道,“他肯定这事儿就是你干的。今天早晨他要上这儿来,你最好先躲躲。”
“我们就在这儿等他。”弗莱迪问道,“他发动不了车,又去干什么了?”
“他困得连站都站不住了。他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最后几乎是瘫倒在走廊的椅子上。蟋蟀们在大声叫着,但我想他是太累了,不管大家怎么吵他他都睡着了。”金克斯不怀好意地咧嘴笑着说,“他看上去可爱极了——一副天真、无助的样子——我想要是给他唱首催眠曲,他肯定能睡得更香。哇,他气得简直都要蹿出天花板了!我自然是紧贴着他耳边唱——丝毫不让他错过我这洪钟般嘹亮的音色。
“他跌跌撞撞地进屋去取枪。不过霍莫和家鼠们昨天就在抽屉里发现了那把手枪,他们还找到一罐打开的木匠修理用的胶水。据我推测,他们把胶水倒在了枪上。”金克斯说着又大笑起来,“安德森在抽屉里摸索着,手很顺利地摸到枪了,可他费了大半天劲,说尽了脏话,才把粘在枪上的手拔下来。当时,胶水还没有完全凝固。”
“天哪!” 弗莱迪说,“这个晚上太糟糕了!我真替这个可怜的家伙难过!”
“嗯,我可不会可怜他。”猫说,“别忘了,他还想把我们的家骗走,让我们沦为乞丐呢!就像他对待可怜的菲尔莫尔夫人那样!而我们只不过是让他几晚睡不了觉而已。不过,现在你应该让雅各布出面接管这一切——因为噪声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那他现在在哪儿?”坎皮奥先生问。
“到处瞎逛,这儿走走,那儿走走。他踉踉跄跄、东倒西歪地走来走去,连霍莫和家鼠都不怕他。有一次,伊克咬他的耳朵,把他弄醒;他后来又睡过去了,霍莫便爬到他脸上把他弄醒。老兄,那还真管用!我想他怕蛇。他到林子里去,可是松鼠的活干得很漂亮,没让他闲着。”
“我听到他朝这儿走来了。”米纳瓦小姐说。千真万确,小路上走来了安德森先生。他在不远处停了下来,一手扶着树,身体斜靠在树上,他向前探着头,双眼布满了血丝,迷离地看着他们,看上去已经筋疲力尽了。
“早上好,安德森先生,天气不错呀!”坎皮奥先生打了声招呼。
安德森先生攥起拳头,强打起精神,大步向他们走来。“你这只猪,”他口齿不清地冲弗莱迪喊道,“你在我车上到底做了什么手脚?”
弗莱迪用询问的眼神看了坎皮奥一眼,坎皮奥轻轻点了点头。他们的神情表明,他俩都同意戏该收场了。因为他们都觉得尽管他们的计划是想让他气得发疯而做傻事,但他现在累得都不会发疯了。因此,事实上,他们完全可以利用他这种筋疲力尽的状态,这比利用他发疯的状态要好得多。
弗莱迪站起来。“是我扯断了许多东西。”他大胆地说道,“怎么了?”
“怎么了?怎么了?!” 安德森先生嘶哑地吼道,“因为我要送你去你该去的地方——那就是去监狱!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
“你凭什么能证明是我干的呢?”弗莱迪问道,“指纹吗?可我没有指头,只有蹄子。”弗莱迪说着扬起了他的蹄子。
“你已经在证人面前承认了。” 安德森先生叫道,“这就是最充分的证据!”
“但只有证人听到了才行。”米纳瓦小姐分辩说,“我们可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对吧,吉米逊?”
“绝对没听说过。”坎皮奥先生回答道。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安德森先生大叫着,“你们全是一伙的。”
“没错!”坎皮奥先生说,“这一切严重触犯了法律,如果你能证明的话。这就像你要得到这家旅馆,然后再霸占我的房子和比恩农场的阴谋一样,非常的不合法。我们也没有证据来证实你的非法性。不过现在,你雇用的老鼠都被赶跑了,你的鬼把戏也被戳穿了。该轮到我们了!你觉得怎么样?”
安德森先生怒火腾地就起来了,由于缺乏睡眠,他的自制力已荡然无存。“我现在就要让你看看我的想法!”他吼叫着,扑向坎皮奥先生。
但是,一直在旁边擦洗煎锅的米纳瓦小姐站了起来,挡住了他的去路。
“臭女人,让开!”安德森先生大吼道,“我可不喜欢打女人。”
“我不喜欢打男人。”米纳瓦小姐回敬道,“可我想那不会有什么危险。”他正要推开她,米纳瓦小姐举起煎锅,“当”的一声,重重地打在他的头上。
如果不是在这个时候,这一下对安德森先生来说算不上什么。可现在他已经被折腾得晕头转向,这一下就足以把他完全打蒙。他踉跄着晃悠了半圈,趴倒在地上。
“天哪!”米纳瓦小姐惊叫一声,吃惊地看看手里的煎锅,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地上。安德森先生甩了几下头,才慢慢地站了起来。
“你会后悔的,小姐。”他说着,“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是的。”她回答道,“我想我会后悔的。我会后悔刚才没再用力些。”
“坐下!安德森!”坎皮奥先生严肃地说道,“喝杯咖啡,我们想和你谈谈。”
“哼!我可不想和你们谈。”安德森先生说,“你这只讨厌的、愚蠢的红脸小猴子,还想和我谈条件!看我不打扁你……”他冲了几步,一看到米纳瓦小姐又拿起煎锅,马上收住了脚步。
“没错,我想我们能谈谈条件。”坎皮奥先生说,“听我说,我们这儿都已经写好了,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字就行。”
“哈!简直是笑话!” 安德森先生说。
“我们没和你开玩笑。我们只知道你不签字,就睡不了觉。你也清楚在‘湖边’旅馆你根本没法入睡,不过你肯定觉得晚上可以在森特博罗你自己的家里睡。你是可以回那儿去睡,可在那儿你会一样没法睡觉。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不择手段地不让你睡觉,蟋蟀能轻而易举地进你家,就像进这家旅馆一样容易。还有门铃的响声、半夜里的电话铃声,老鼠在家具上磨牙的声音——我们手头上有上百种法子。——喂,醒醒!”他话还未说完,安德森先生已经困得头都耷拉到胸前了。
“坎皮奥先生,看来你的声音有催眠的作用。”弗莱迪说道。安德森先生均匀的鼾声刚起,弗莱迪喊道:“雅各布!”
随着一阵嗡鸣声,胡蜂落到安德森先生的领子上。“伙计,谢谢。”雅各布说,“你想让我在哪儿开始打钻?——你想从哪儿开始?”
“你自己定吧。”
雅各布拔出刺,在安德森先生的领子上蹭了蹭,然后踏步走上了安德森先生的脖子,很专业地四处看了看。“通常情况下,我会选择耳朵正下方这个部位。”他说,“要是选择鼻子,场面要壮观得多。不过,从长远考虑,还是脖子的效果最好。好了,看刺!”说着,他就刺了进去。
效果果真非同凡响。安德森先生的鼾声顿时变成尖叫,他跳起来,使劲地抓脖子,狂乱地舞动了一阵子,最后两手抱着脖子倒在一块木头上,一双委靡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们。
“知道了吧。”坎皮奥先生愉快地说,“不签字,就睡不成觉。”他又拿出了那张纸。安德森先生犹豫了片刻,“哼”的一声接了过去看起来。刚读到一半,他就叫起来,“你们不会以为我是疯了吧?”他说,“嘿,这东西——凭这东西,你们随时都可以把我送进监狱?”
“非常正确!”坎皮奥先生回答道,“不过你如果规矩些,我们就不会那样做。只要你把旅馆还给菲尔莫尔夫人,我们就会把这张协议还给你。”
“哦?真的吗?”安德森先生冷笑着,脸有些变形。他现在的整个表情暴露了他有多么的虚伪,他现在累得实在是伪装不下去了,森特博罗的市民常看到的那个直率的、和蔼可亲的好人不见了。“什么?还回去?那家旅馆我可是花了大价钱的,还有……”
“还有就是菲尔莫尔夫人会把钱还给你。”坎皮奥先生打断他的话,说道,“当然,数目较小,说说修整这家旅馆花了多少钱,三千美元?”
安德森先生又瞟了一眼那张纸。“听听这句话,”他说,“‘我承认我犯了重罪,恶意蓄谋威胁、恐吓该店雇员,以达到吓跑他们的目的,后来确实吓跑了他们。此外,为实施这些罪恶的、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我还……’嘿,我都看不懂这些是什么意思!”
坎皮奥先生颇为自得地笑了一笑,“我想我的措辞是相当不错的。”他说,“嘿!”安德森先生的头又耷拉了下去。坎皮奥先生抓住他的肩膀使劲摇晃着:“醒醒,快签字!”
安德森先生微微抬了抬头,摸索着接过坎皮奥先生递过来的笔。他签完字,便向后一躺,从木头上滚下来,仰躺着睡着了。
坎皮奥先生把一份复印件塞进他的衣兜里,复印件的备注里写着,如果三天内菲尔莫尔夫人出三千美元买不回“湖边”旅馆,协议原件就会被交给地方检察官。“这就行了,” 坎皮奥先生说,“他醒过来看到这份协议,就会知道他自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归还旅馆,要么进监狱。”
“制伏他也用不了很长时间嘛!”弗莱迪说,“我还以为,我们得让他不睡觉一个星期才行呢。”
“就这些重要人物?”坎皮奥先生很不屑地说,“他们根本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