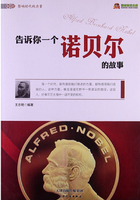解读这首诗的难点是“未生娘”,它通常可以表示圣洁的母亲、纯洁的少女、未嫁的姑娘和美丽的梦,而如果按照字根意思,还可以勉强翻译为“不是亲生的那个母亲”。在前文,我们分析这首诗是首“佛法诗”,那个“不是亲生的母亲”是指佛,但是,它也很可能是首“政治诗”。相应的,这个词指的就是桑杰嘉措,那个栽培他、给他第二次生命的监护人,而不是什么情人。
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吗?
我们可以看另一首诗,这首诗在通行的《仓央嘉措情歌》中是找不到的:
白色睡莲的光辉,照亮整个世界
格萨尔莲花,果实却悄悄成熟
只有我鹦鹉哥哥,做伴来到你的身边。
难道这首诗也要被理解为爱情诗吗?它的出处在一本叫做《仓央嘉措秘传》的书中。这本书涉及到仓央嘉措“死亡”的问题,在后文分析他的“死因之谜”时,会专门提到它。
仓央嘉措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呢?在该书的记载中,仓央嘉措听到了作者阿旺多尔济的哭声,听出他是桑杰嘉措的转世,后来写了这首诗,表达的是对他与桑杰嘉措重逢的欣喜和对他不离左右、始终相伴的感激。因此,这首诗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诗”。
那么,“东山诗”为什么不能是怀念桑杰嘉措的作品呢?
如果诗里的“鹦鹉哥哥”指的是桑杰嘉措,那么,通行本的《仓央嘉措情诗》中还有这样几首:
孔雀来自印度东,工布深谷鹦鹉丰。
两禽相去常千里,同聚法城拉萨中。
会说话的鹦鹉儿,请你不要做声。柳林里的画眉姐姐,要唱一曲好听的调儿。
我同爱人相会的地方,是在南方山峡黑林中,除去会说话的鹦鹉以外,不论谁都不知道。会说话的鹦鹉请了,请不要到十字路上去多话!
这些诗里的鹦鹉,指的又是什么呢?难道真是民间传说中泄露他私生活秘密的人吗?
实际上,仓央嘉措诗作中,有很多诗既可以理解为“佛法诗”,也可以被理解为“政治诗”。它们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但却不能理解为“情诗”,更不能作为他生活放荡的证据。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典型、也非常有趣的对比,仓央嘉措的诗中有这样一首:
邂逅谁家一女郎,玉肌兰气郁芬芳。
可怜璀璨松精石,不遇知音在路旁。
此诗于道泉翻译为:
邂逅相遇的情人,是肌肤皆香的女子,犹如拾了一块白光的松石,却又随手抛弃了。
从字面上看,这是写爱情情调的作品,似乎可以作为仓央嘉措生活放荡的证据。
可是,我们可以与另外一段话做个对比,对比的结果是比较好笑的。需要说明的是,这段文字原本不是诗,但简单地将它们分行,当“诗”读一读也蛮有意思的:
黄金是从铁砂中淘出来的
宝物是从芜杂中提取的精华
用筛子取出宝物时
又怎么能让泥沙也掺杂进来呢
如果在这首“诗”中加入“女子”、“佳人”等比喻,与仓央嘉措的诗还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这段话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的呢?它出于1603年四世达赖喇嘛剃度时,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六世活佛给他的“贺信”。当时,噶玛噶举对格鲁派是严重敌视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在贬低格鲁派教义,将他们比做泥沙。意大利学者杜齐在《西藏中世纪史》中认为,“贺信”事件“成了红黄教间不久猛烈爆发冲突的原因”,此后不久,两派的斗争果然进一步升级。
所以说,这段话不是在抒情讲道理,而是在政治挑衅。
由此看出,仅从诗作的字面上理解,便得出仓央嘉措生活放荡的结论,是有失偏颇的。不过,有几首诗确实不好解释,它们的文意很明显,描述很直白,似乎没有另外解释的方法。这几首诗在曾缄先生的翻译版本中是这样的:
为寻情侣去匆匆,破晓归来鹱雪中。
就里机关谁识得,仓央嘉措布拉宫。
夜走拉萨逐绮罗,有名荡子是汪波。
而今秘密浑无用,一路琼瑶足迹多。
布达拉宫之圣殿,持明仓央嘉措居。
夜访拉萨逐绮罗,宕桑汪波亦是彼。
这些诗的内容都十分浅近,说的是在布达拉宫的仓央嘉措,夜里偷偷溜出去,化名为宕桑汪波去幽会情人,回来的时候在雪上留下了脚印,秘密就此藏不住了。
如果这些诗是仓央嘉措所做,显然是他放荡生活的亲笔写照,但仔细阅读这几首,却会感觉到明显与其他几十首风格迥异,难道真是他的原笔原意?
有学者指出,目前仓央嘉措诗作中,有一些是拉藏汗为了给他捏造罪证而伪作的,这种说法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很明显的疑问是,如果这真是仓央嘉措的原笔,他留下自己的“罪证”干什么?岂不是授人以柄?再说,如果真有胆量赤裸裸地承认自己生活放荡,怎么不见其余记载?他本人都肯承认,难道外人还会为尊者讳吗?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明白,第一,文学作品的字面意义不适合当做实证;第二,这些诗作是否是仓央嘉措的原笔也未可知。
那么,将它们作为他生活放荡的证据,能有多大的说服力呢?
然而,在民间,这些诗作的流传范围太广、影响太大,人们不愿意去细究诗作的含义,而是喜欢通过字面意思对它们进行“再加工”。
“再加工”的结果是什么呢?比如,“东山诗”中音译的“玛吉阿米”,便被认定为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她也就成为仓央嘉措的情人。现在,在拉萨帕廓街东南角有一座土黄色小楼,这就是著名的“玛吉阿米餐厅”,招牌上用藏、汉、英文赫然书写着店名——“未嫁娘”。民间传说,仓央嘉措就是在这里幽会他的情人玛吉阿米的。
同时,在其余的诗中,人们还猜出了玛吉阿米的身份——酒店的女店主,证据是“少年琐碎零星步,曾到拉萨卖酒家”,“空女当垆亲赐饮,醉乡开出吉祥花”;继而,在很多试探、彷徨、定情的诗句之外,人们找出了他们最终的结局——被玛吉阿米的姐妹告发,“已恨桃花容易落,落花比汝尚多情”,“情人更向情人说,直到仇家听得真”,最后,玛吉阿米只好另嫁他人,“深怜密爱誓终身,忽抱琵琶向别人”,或者是神秘失踪,“盗过佳人便失踪,求神问卜冀重逢”,只留下长相思的昔日浪子。
这些故事,肯定都是典型的附会。
在字面意思上猜测,这还倒无所谓,对作品如何理解是每个人的自由,读出什么东西来也都是一家之言,非但无可指责,也还值得尊重。
但通过他的诗作添枝加叶、恶意中伤,就太过无耻了。这种情况直到现在还层出不穷。比如以下文字:
他特意在布达拉宫外盖了一栋单门独院的房子,名叫魔宫。据说,性喜饮酒的仓央嘉措在做了达赖活佛后专门去过一次扎日山,返回时带来了藏雄酒酿酒人家族中的一名少女和她的妈妈,让她们在拉萨开了一家酒馆,以便使自己可以长期饮用。每当夜晚来临,仓央嘉措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后门偷偷溜出布达拉宫,化名宕桑汪波,来到拉萨街头,走进藏雄酒馆开怀畅饮,和美丽的拉萨姑娘们调笑玩耍(甚至酿酒少女后来也成了他的情人)。当第二天黎明曙光出现时,他才悄悄返回布达拉宫。是藏雄酒帮助仓央嘉措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体力,同时又激发了他的激情。
据说,仓央嘉措饮用的藏雄酒经过了专门的配制,他又加入了许多神秘的药物,从而更增强了藏雄酒壮阳健身的功能,从而让使用者可以在不丧失自己体能和精力的情况下保持性爱时间和效果。而且,这种改造过的藏雄养生酒还具有另一种功能,它可以使人练就类似道家房中术一样的法术,即采阴补阳。
这段文字是一家保健酒厂家做的广告文案,这个故事让人直接将仓央嘉措想象成一个又酗酒又采花的活佛。反过来,这不恰恰也说明了关于仓央嘉措生活放荡的故事,大多数是无耻的演绎吗?
以上四项内容——《列隆吉仲日记》的记载、拉藏汗的一面之辞、五世班禅的自传、仓央嘉措诗歌的附会,看起来都不可靠。但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关于仓央嘉措生活放荡的说法,曾经有一个“实物证据”——一缕女人的青丝。
“青丝”这个细节记载在仓央嘉措诗歌的另一个汉译大家、中央民族大学庄晶教授的一篇文章中。该文提到,我国北方民族史专家贾敬颜(1924~1990年)先生早年在阿拉善旗考察时,曾亲眼见到过它。据说,在当地仓央嘉措留下了很多遗物,除了宗教器物之外,确实有这样一缕头发。它现在还在阿拉善的南寺、也就是广宗寺里供奉。早些年,还曾在当地宗教展览中展出过——当然,这个“物证”产生的前提是1706年仓央嘉措没“死”,后来辗转云游到阿拉善旗终老。
那么,这条头发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是仓央嘉措情人的吗?难道仓央嘉措至死都在怀里揣着当年情人的头发,并带到了棺材里?
有意思的是,庄晶就是《仓央嘉措秘传》的汉译者。如果仔细阅读该书第三章,就会看到如下记载:阿拉善王的女儿道格公主曾“将自己的发丝积攒起来,做成一只精美的顶髻……与此相配的还有五佛冠,上下衣裳等全套服饰”,“全部贡献”给仓央嘉措。
贾敬颜先生看到的头发,很有可能就是它。
这个事件,估计很多人还会浮想联翩地附会一下:是不是那个公主对仓央嘉措有什么朦胧的意思?在汉族地区,女子赠发给男人,可一直是表示情爱的。如果按照汉族地区民间习俗来揣测,可就是大错特错了,用头发编髻供养,可完全是藏传佛教里的宗教事务。
举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藏传佛教中开创活佛转世制度的是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黑帽”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真实的历史是,1256年噶玛拔西却吉受到元朝宪宗皇帝赏赐的黑色僧帽一顶,并钦定其为前辈大师都松钦巴转世。由此,拔希却吉追认都松钦巴为第一世活佛,称自己是第二世,于是开创了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形成了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
但在藏传佛教的传说中却不这么记载,它说的是都松钦巴剃度时,智慧空行母和上乐诸神给他戴上了一顶黑帽;这帽子就是十万俱胝空行母用头发编成的。
显然,道格公主用自己的头发做供养,就是遵照这个传说而来的,是一桩非常严肃的藏传佛教宗教行为。这缕头发,绝非仓央嘉措早年情人的定情之物,也绝非后来公主的示爱之物。所谓的“物证”,其实也很不可靠。
既然四种书面证据和一项物证都不可靠,那么,仓央嘉措的真实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可以将仓央嘉措的生活时间分为两段,分割点就是1697年、1698年。也就是他被正式册封为第六世达赖喇嘛前后。在此之前,是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有一定的史料记载;在此之后,是他的达赖喇嘛时期,私生活方面几乎没有正史记载。
仓央嘉措童年、青少年时期,在民间的传说中是在家乡过的,而且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友,这女友后来跟随他到了拉萨成为他的情人——这些传言基本上都不可能。
1683年,仓央嘉措出生在西藏门隅邬坚林寺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关于他属于什么民族,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藏族;但于乃昌先生在《仓央嘉措生平疏议》中认为属于门巴族。这个观点,其价值在于有助于确定仓央嘉措的家庭信仰背景,因为门隅地区的门巴族人很有可能是信奉宁玛教义的。
信奉宁玛教义跟生活有什么联系吗?首先,宁玛派是可以娶妻生子的,它的早期传承方式就是父子相传,这与早期宁玛派没有寺庙组织、走家串户宣扬教义的传播方式有关;其次,宁玛派对密法修持比较重视,而早期又受到印度左道性力派的一些影响。所以,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宁玛派的主要修持方法就是所谓的“双身”、“双修”。
如果仓央嘉措的家庭信仰是宁玛派,他的一系列放荡的生活就有了所谓的“理论根据”。
另外,于乃昌和一些国外研究者还认为,五世达赖喇嘛和桑杰嘉措也是信奉宁玛派的,他们想要恢复古老的宁玛密法传统,于是大力培养一个信奉宁玛派的仓央嘉措。这种观点有一些根据,比如五世达赖喇嘛在世时大力建造了多吉札寺和敏珠寺等宁玛寺院,从此宁玛派改变了没有中心寺院、信徒组织比较分散的教派形式。
可这就能说明仓央嘉措成天搞“双修”吗?
以五世达赖喇嘛那样的高僧大德,维护各教派之间的平衡、吸取其他教派的优点,就意味着他反对格鲁派教义吗?显然不能这么说。同样,仓央嘉措确实学习过一些宁玛派的经典。可纵观历史,几乎所有有成就的藏传佛教高僧都学过,难道所有大师都有生活问题吗?既然答案都是否定的,为什么偏偏要给仓央嘉措“扣帽子”呢?事实上,就算宁玛派允许所谓的密法。也绝不意味着允许放荡,历史上更没有哪个宁玛大师在这方面的负面记载。
关于仓央嘉措的族属和早期信仰是可以研究的,但以此为证据得出仓央嘉措生活放荡的结论,显然是过于草率。
而事实上,仓央嘉措很小就开始接受格鲁派的教育了,就算他家信宁玛派,他也没怎么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