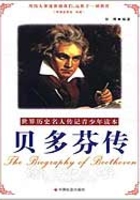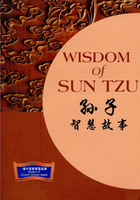1.入定修观法眼开,祈求三宝降灵台。观中诸圣何曾见,不请情人却自来。
2.入定观修上师尊,心中偏偏不显现。不曾意想爱人脸,清清楚楚现在前。
这两首诗实际上是一首两译,写的都是观想的时候,“诸圣”和“上师尊”,也就是佛菩萨的影像还没有浮现在眼前,却看到了情人;而且是“不请情人却自来”。
这首诗于道泉先生是这样翻译的:
我默想喇嘛的脸儿,心中却不能显现;我不想爱人的脸儿,心中却清楚地看见。
可以看出,于道泉的版本是字面直译的,而曾缄的版本是体现出一些含义的。
这些含义,还得靠佛家的观想方法来说明:观修练到一定层次,不是看到佛菩萨,而是佛菩萨与自己合二为一。所以,“不请情人却自来”可以说是仓央嘉措修持观想的一个心得,也记录了他修持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层次——此时的仓央嘉措,也许不用眼观的办法,而是可以在心里很快地进入观想的层次了,这就是“不请却自来”、“不曾意想”表达的境界。
至于是“心中”重要,还是“眼前”重要,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佛教界的人士解答吧。但无论答案是什么,即使仓央嘉措此时的修行层次在佛家看来还不高,也只能说明这首诗记载了当时的他的修行心得。就像某位作家的早期作品,虽然不成熟,但却记录了他当时的水平。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于道泉先生的译本:
若以这样的“精诚”,用在无上的佛法,即在今生今世,便可肉身成佛。
这首诗在曾缄翻译的时候,加了很多“文采”,又将“情人”这样的字眼儿给弄出来了:
静时修止动修观,历历情人挂眼前。肯把此心移学道,即生成佛有何难。
按照于道泉先生字面直译的翻译风格,恐怕原诗里是没有“少女”这样的词的,但曾缄还是大胆地保持自己的“统一风格”,于是民间又会将这首诗当成情歌了。
为什么会当成情歌呢?原因有二:一、诗里有“情人”的字样;二、错误的阅读逻辑。
因为仓央嘉措原诗恐怕是没有“少女”字样的,所以我们搞不懂曾缄译本中的“情人”指的是女人,还是佛。不过,这都不要紧,无论它指的是什么,我们都能从阅读逻辑角度分析出它不是情歌。
按普遍的阅读逻辑,“静时修止动修观,历历情人挂眼前”是个时间上的承接关系,翻译过来就是:观想的时候,情人却浮现在眼前。这样理解起来,前半句是后半句的时间状语。意思很明显,仓央嘉措不好好修持,表面上在那儿装样子,心里想的还是情人。
而如果我们用另一种句法解释,就可以得出完全迥异的结论,这个办法就是将后半句当做前半句的补语,翻译过来应该是——“静时修止动修观”,就好像“历历情人挂眼前”。
这说明了什么?恰恰说明仓央嘉措将修持时刻放在心头,时刻惦念不忘。
这样的解释,秘密隐藏在上半句中,“动”,说的是不仅仅打坐的时候要修持,行动的时候也要时刻不忘、时刻精进,就好像谈恋爱的人时刻把情人挂念在心头一样,这样才可能有大成就。所以下一句就说,要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即身成佛了。这里需要指出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的一个区别,汉地佛教一般来说,主张的是修持多少劫、多少世才可以成佛;而藏传佛教追求的是今生今世就能成佛,也就是即身成佛。
调整了阅读逻辑,我们发现,哪怕“情人”指的就是个女人,也说明仓央嘉措此诗是佛法诗,焉知他不是在劝导世人:求成佛和世间谈恋爱异曲同工啊,都要念念不忘、魂牵梦萦才能成功呢。
如果“情人”指的不是女人,是佛呢?那么我们就又有新的发现了。
此时,前一句上下半句之间,就不应该考虑定语和补语的问题,而应该成为并列关系了。“静时修止动修观”在古汉语里不是“静该怎样”、“动该怎样”两件事,而是将“动静”和“止观”拆开写了,这在古汉语中是常见的结构方法。因为我们实在无法单独地分析“止”和“观”,它们应该是一门功课——“止观”,这是一切禅定的精华,佛家的必修功课,观想便是其中的要义。
那么,整句翻译过来就是:无论是行动还是打坐都要修持止观,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佛菩萨挂在心头,这样精诚用心的话,即身成佛是可行的。
通过这样的解读,我们发现,以上列举的三首仓央嘉措的诗,都是佛法诗,和爱情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所有诗作中出现的“情人”字样,如果理解为“佛”,含义就完全变化了。
那么,理解为“佛”是否可行呢,这是强词夺理,还是原意如此呢?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曾缄译本诗作中有这样一首:
意外娉婷忽见知,结成鸳侣慰相思。此身似历茫茫海,一颗骊珠乍得时。
按照世俗化的理解,这是一首“情歌”,表达的是与意中人心心相印的渴望和惊喜,情义两心知就好像在大海中捞到珍宝一样令人心动,这里当然也有难得、幸运的含义。
需要注意的是“娉婷”这个词,在这首诗里怎么看都是“情人”的意思,但是,如果仔细翻阅曾缄本的其余译作,我们还能发现一首:
为竖幡幢诵梵经,欲凭道力感娉婷。琼筵果奉佳人召,知是前朝礼佛灵。
这里同样用了“娉婷”这个词,而这个词在这首诗里,指的就是佛。
曾缄先生没词可用了吗?为什么两首诗出现同一个词呢?难道不可能是他有意为之吗?既然后一首诗里“娉婷”指的是佛,那么,前一首诗里为什么就不能是呢?这首诗怎么就不能表达仓央嘉措对佛法求之不易的感叹呢?而“娉婷”是佛,“少女”、“佳人”、“情人”怎么就不能是佛呢?
如果说上面几首诗,内容本身和用词上都涉及了佛法,其义一见就明,如此解释也容易让人接受;那么,有没有那种“公认”的爱情诗,在原本里没有出现宗教字眼的诗,其实一直被我们误读呢?
仓央嘉措的“情歌”中,流传最广的是这一首:
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第三最好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第四最好不相惜,如此便可不相忆。
第五最好不相爱,如此便可不相弃。第六最好不相对,如此便可不相会。
第七最好不相误,如此便可不相负。第八最好不相许,如此便可不相续。
第九最好不相依,如此便可不相偎。第十最好不相遇,如此便可不相聚。
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安得与君相诀绝,免教生死作相思。
不知道这个版本是从何而来,在于道泉先生的译本中,只有前面两句:
第一最好是不相见,如此便可不至相恋;
第二最好是不相识,如此便可不用相思。
这两句诗曾缄先生的译本是这样的:
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安得与君相诀绝,免教生死作相思。
无论怎么看,这两句诗都是写爱情内容的,无论古体版本还是自由体版本,在翻译上保持惊人地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于道泉在此诗之后,还有行注文,说,“这一节据藏族学者说应该放在29节以后”。他所说的第29节是:
宝贝在手里的时候,不拿它当宝贝看;宝贝丢了的时候,却又急的心气上涌。
这段诗曾缄翻译为:
明知宝物得来难,在手何曾作宝看。直到一朝遗失后,每思奇痛彻心肝。
如此说来,最好不“相见、相知、相思”的,是一个“宝贝”或“宝物”,那么,这是指情人,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呢?
即使没有第29节的前提,“相见、相知、相思”的就一定是一个女人吗?
于是有人通过对照藏文原文,直译如下:
第一最好不发现,免得不由迷上它;第二最好不谙习,免得以后受煎熬。
这样一来,这个“宝贝”,就很有可能指的是佛法,或者是一种我们搞不清楚的藏传佛教的修持法门,它抒发的是仓央嘉措痴迷佛法、欲罢不能的感觉。
实际上,可以进行类似解读的诗作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还原仓央嘉措的真实历史形象,对这些诗作的理解就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只不过,他的民间形象太深入人心,以至于在翻译这些诗作的时候,译者也只好按照情诗来定“基调”。
比如曾缄,在发表他的七言绝句体汉译本的同时,还创作了一首《布达拉宫辞》。这首长诗轰动海内外,成为当时的普通百姓了解风流活佛、街谈巷议他的浪子行为的最佳版本。在这首长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秘戏宫中乐事稠”。任谁都知道,在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学作品中,这样的字眼,只能烘托出一个贪淫好色、秽乱后宫的昏君形象,民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隋炀帝,但是,有谁正面评价过他那些光辉的历史功绩呢?
同样的道理,这样的词汇用在仓央嘉措身上,人们心目中也就自然将他想象成风流浪子,但又有谁想过,他很可能是一位有政治雄心并且精研佛法的活佛呢?
这就是由一个文学形象塑造、流传出来后转变为民间形象的典型事例。而根据这样的民间形象,便有好事文人继续创作出尺度更大胆的文学形象,如此流传下来,仓央嘉措在民间便逐渐被定格为一位浪子活佛;他的诗,也自然成为表达相思之情的爱情诗了。
事实上,有专家曾指出,仓央嘉措的诗歌是在表达自己对修行的理解,他的诗歌从密宗角度出发,全能做出宗教上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仓央嘉措情歌》原文的题目是“仓央嘉措古鲁”,而并非“仓央嘉措杂鲁”。在藏语里,“杂鲁”是有规范的,“杂”是名符其实的“情”;而“古鲁”的含义是“道歌”。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仓央嘉措情歌”,在作者的原意中,或许是有劝诫意义的宗教道歌,学术著作中一直坚持翻译为“仓央嘉措诗歌”,是比较严肃和客观的译法。
既然他的诗歌不是情歌,那么,他谈恋爱、有情人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呢?他还是不是那个民间形象中风流倜傥的浪子活佛呢?